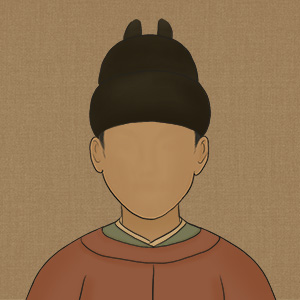《将进酒》原是汉乐府短箫铙歌的曲调,标题的意思为“劝酒歌”,内容多是咏唱喝酒放歌之事。这首诗是诗人当时和友人岑勋在嵩山另一老友元丹丘的颍阳山居作客,作者正值仕途遇挫之际,所以借酒兴诗,来了一次酣畅淋漓的抒发。在这首诗里,李白“借题发挥”,借酒消愁,感叹人生易老,抒发了自己怀才不遇的心情。
这首诗十分形象的体现了李白桀骜不驯的性格:对自己充满自信、孤高自傲、热情豪放,“天生我材必有用”、“人生得意须尽欢”。全诗气势豪迈,感情豪放,言语流畅,具有极强的感染力。李白咏酒的诗歌非常能体现他的个性,思想内容深沉,艺术表现成熟。《将进酒》即为其代表作。
诗歌发端是两组整齐的长句,如挟天风海雨向读者迎面扑来。“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颍阳去黄河不远,登高纵目,故借以起兴。黄河源远流长,落差极大,如从天而降,一泻千里,东走大海。如此波澜壮阔的现象,必定不是肉眼能够看到的,作者是幻想的,言语带有夸张。上句写大河之来,势不可挡;下句写大河之去,势不可回。一涨一消,构成舒卷往复的咏叹味,是短促的单句(如“黄河落天走东海”)所没有的。紧接着,“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恰似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如果说前二句为空间范畴的夸张,这二句则是时间范畴的夸张。悲叹人生苦短,而又不直言,却说“高堂明镜悲白发”,一种搔首顾影、徒呼奈何的神态宛如画出。将人生由青春到老的全过程说成“朝”“暮”之事,把原本就短暂的说得更为短暂,与前两句把原本壮阔的说得更为壮阔,是“反向”的夸张。开篇“以河之水一去不复返喻人生易逝”,“以黄河的伟大永恒形出生命的渺小脆弱”。这个开端可谓悲感至极,却又不堕纤弱,可以说是巨人式的感伤,具有惊心动魄的艺术力量,同时也是由长句排比开篇的气势感造成的。这种开篇的方法作者经常用,比如“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宣城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沈德潜说:“此种格调,太白从心化出”,可见其颇具创造性。此诗两作“君不见”的呼告(一般乐府诗只是篇首或篇末偶尔用),又使诗句感情色彩大增。所谓大开大阖者,此可谓大开。
“人生得意须尽欢”,这似乎是宣扬及时行乐的思想,然而只不过是现象而已。诗人“得意”过没有?“凤凰初下紫泥诏,谒帝称觞登御筵”(《玉壶吟》)似乎得意过;然而那不过是一场幻影。“弹剑作歌奏苦声,曳裾王门不称情”(《行路难三首·其二》)又似乎并没有得意,有的是失望与愤慨,但并不就此消沉。诗人于是用乐观好强的口吻肯定人生,肯定自我:“天生我材必有用”,这是一个令人鼓掌赞叹的好句子。“有用”而且“必”,非常的自信,简直像是人的价值宣言,而这个人“我”是需要大写的。于是,从貌似消极的现象中透露出了深藏其内的一种怀才不遇而又渴望入世的积极的态度。正是“长风破浪会有时”,应为这样的未来痛饮高歌,破费又算得了什么!
“千金散尽还复来!”这又是一个高度自信的惊人之句,能驱使金钱而不为金钱所使,这足以令所有凡夫俗子们咋舌。诗如其人,想诗人“曩昔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馀万”(《上安州裴长史书》),是何等的豪举。所以此句是深蕴在骨子里的豪情,绝非装腔作势者可以得其万分之一。与此气派相当,作者描绘了一场盛筵,那决不是“菜要一碟乎,两碟乎?酒要一壶乎,两壶乎?”而是整头整头地“烹羊宰牛”,不喝上“三百杯”决不罢休。多痛快的筵宴,又是多么豪壮的诗句!至此,狂放之情趋于高潮,诗的旋律加快。“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几个短句忽然加入,不但使诗歌节奏富于变化, 而且使我们似乎听到了诗人在席上频频地劝酒。既是生逢知己,又是酒逢对手,不但“忘形到尔汝”,诗人甚至忘了是在写诗,笔下之诗似乎还原为生活,他还要“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以下八句就是诗中之歌了,这纯粹是神来之笔。
“钟鼓馔玉”即富贵生活(富贵人家吃饭时鸣钟列鼎,食物精美如玉),可诗人却认为这“不足贵”,并放言“但愿长醉不复醒”。诗情至此,便分明由狂放转而为愤激。这里不仅是酒后吐狂言,而且是酒后吐真言了。以“我”天生有用之才,本当位极卿相,飞黄腾达,然而“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三首·其二》)。说富贵“不足贵”,乃是出于愤慨。以下“古来圣贤皆寂寞”二句亦属愤语。诗人曾喟叹“自言管葛竟谁许”,说古人“寂寞”,其实也表现出了自己的“寂寞”,所以才愿长醉不醒了。这里,诗人是用古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说到“唯有饮者留其名”,便举出“陈王”曹植作代表。并化用其《名都篇》“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之句。古来酒徒很多,而为何偏举“陈王”,这又与李白一向自命不凡分不开,他心目中树为榜样的都是谢安这些高级人物,而这类人物当中,“陈王”曹植与酒联系得比较多。这样写便有了气派,与前文极度自信的口吻一贯。再者,“陈王”曹植于曹丕、曹睿两朝备受猜忌,有志难展,也激起诗人的同情。一提“古来圣贤”,二提“陈王”曹植,满满的不平之气。此诗开始似乎只涉及人生感慨,而不染指政治色彩,其实全篇饱含了一种深广的忧愤和对自我的信念。诗情之所以悲而不伤,悲而能壮,即根源在此。
刚露一点深衷,又说回酒了,而且看起来酒兴更高了。以下诗情再入狂放,而且愈来愈狂。“主人何为言少钱”,既照应“千金散尽”句,又故作跌宕,引出最后一番豪言壮语:即便千金散尽,也不惜将名贵宝物“五花马”(毛色作五花纹的良马)、“千金裘”(昂贵的皮衣)用来换美酒,图个一醉方休。这结尾之妙,不仅在于“呼儿”“与尔”,口气甚大;而且具有一种作者一时可能觉察不到的将宾作主的任诞情态。须知诗人不过是被友招饮的客人,此刻他却高踞一席,气使颐指,提议典裘当马,令人不知谁是“主人”,浪漫色彩极浓。快人快语,非不拘形迹的豪迈知交断不能出此。诗情至此狂放至极,令人嗟叹咏歌,直欲“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情犹未已,诗已告终,突然又迸出一句“与尔同销万古愁”,与开篇之“悲”关合,而“万古愁”的含义更其深沉。这“白云从空,随风变灭”的结尾,显见诗人奔涌跌宕的感情激流。通观全篇,真是大起大落,非如椽巨笔不办。
《将进酒》篇幅不算长,却五音繁会,气象不凡。它笔酣墨饱,情极悲愤而作狂放,语极豪纵而又沉着。全篇具有震动古今的气势与力量,这诚然与夸张手法不无关系,比如诗中屡用巨额数字(“千金”、“三百杯”、“斗酒十千”、“千金裘”、“万古愁”等等)表现豪迈诗情,同时,又不给人空洞浮夸感,其根源就在于它那充实深厚的内在感情,那潜在酒话底下如波涛汹涌的郁怒情绪。此外,全篇大起大落,诗情忽翕忽张,由悲转乐、转狂放、转愤激、再转狂放、最后结穴于“万古愁”,回应篇首,如大河奔流,有气势,亦有曲折,纵横捭阖,力能扛鼎。其歌中有歌的包孕写法,又有鬼斧神工、“绝去笔墨畦径”之妙,既非鑱刻能学,又非率尔可到。通篇以七言为主,而又以三、五言句“破”之,极参差错综之致;诗句以散行为主,又以短小的对仗语点染(如“岑夫子,丹丘生”,“五花马,千金裘”),节奏疾徐尽变,奔放而不流易。《唐诗别裁》谓“读李诗者于雄快之中,得其深远宕逸之神,才是谪仙人面目”,此篇足以当之。
南宋淳熙十一年(1184年),稼轩以“凭陵上司,缔结同类”的罪名,罢居上饶已经将近三年了。所以词中处处把李之入任,与己之罢闲,双双对照写来,一喜一忧,缠绵悱恻,寄意遥深,感人心肺。
起两句,“蜀道登天,一杯送绣衣行客”。点出李之入蜀与己之送行,双双入题,显得情亲意挚,依依难舍。“登天”虽借用李白诗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其实却暗含此行之艰难;虽是王命,何尝又不是小人的挟嫌排挤,有如远谪?所以他这阕词写的极其沉郁,这开头无异已定下了全词的基调。“一杯”,何其简慢;看似淡语,然而却是至情的无间;流露出君子之交,一杯薄酒足矣。没有华筵歌妓,也没有清客的捧场;只有两个知心的朋友一杯相对,则这“一杯”二字,不仅写出了友情之深,亦且写尽了世态之薄。笔墨之力量如此,则这“一杯”也就不少了。
“绣衣”,是对“提刑”的美称。汉武帝时,派使者衣绣衣巡视天下,操有生杀之大权,称为绣衣直指。李正之提点刑狱公事,也负有司法和监察的任务,所以稼轩也借以称他为“绣衣使者”。
三、四句:“还自叹、中年多病,不堪离别。”点出“中年”,是时稼轩45岁,正是“不惑之年”,大有作为的时候。然而“多病”,这一“病”字,包含就多了,更何况“多病”。稼轩正当中年,而一放就是三年。又正是祖国被侵占的时候,自己又有才能去驱除外侮,却非要闲置如此,内忧外患,不能不“病”。所以他才用“还自叹”三字领起下面两种难堪:已是自己闲置生愁,怎当堪用的同志又遭远调,离开了中央,这一来抗战派淘汰将尽矣。所以这种离别,不止友情,更关系国家的命运,才是最大的痛楚。
五、六两句,按词律要求,是要用律句的对仗格式。他巧妙地安上了诸葛亮的《出师表》和司马相如的《喻巴蜀檄》,都是关于蜀的故事。切题已难,而寓意得妙更难。他却举重若轻,正是有一肚子的学问。“还北看惊”者,是还北方的大好河山,沦入异族之手,正应当像诸葛亮请求出师那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着一“惊”字,有三层意思:惊山河之破碎;惊投降派的阻挠;以至惭愧得都怕(惊)读诸葛亮的《出师表》了。然而却反其“道”而行之,让李正之去西南的巴蜀“更草相如檄”。据《史记·司马相如传》载:“唐蒙使路通夜郎西僰中,发巴蜀吏卒……万余人,用兴法诛其渠帅,巴蜀民大惊恐。上闻之,乃使相如责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这里着一“更”字,透露出了不出师还北之恨未已,而又要被强迫到西南去镇压人民。恨上加恨,这个“更”字把一个南宋小朝廷的那种对敌和,对己狠的心态暴露无遗。下字非常生动而有力。
七、八两句,“把功名收拾付君侯,如椽笔”。正是双方的小结。自己废置无聊,而李又任非其所。而“把功名收拾付君侯”的,是因为他毕竟还是有土有责的,和稼轩自己只能耕种以自适的“稼轩居士”不同,终究还是可以期望以“功名”的。然而稼轩之所以期望于李的功名,不是铁马金戈,不是临刑的鬼头刀,而是如椽之笔!因为李正之是提刑,他那红笔一勾,是要人命的,虽不能法外开恩,也要慎之又慎。所谓“况钟之笔,三起三落”。在这六年前,稼轩也曾有过“按察之权”,而他当时却向皇帝上过《论盗贼札子》,他就曾非常精辟地说过剿“贼”之害。他说:“民者国之根本,而贪浊之吏迫使为盗,今年剿除,明年扫荡,譬之木焉,日刻月削,不损则折,臣不胜忧国之心,实有私忧过计者。欲望陛下深思致盗之由,讲求弭盗之术,无恃其有平盗之兵也。”用笔,即亦“无恃其有平盗之兵”。能如此,那于国于民也就算是功名了。言来令人欲泪。
过拍起首四句:“儿女泪,君休滴。荆楚路,吾能说”。“儿女泪”是用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诗末二句:“无为在岐路,儿女共沾巾”之意。“能”,这里读去声,宁可的意思。这里是说:与其有作儿女哭泣的时间,倒不如听我说一说你要去的荆楚这一路的风光吧?以此换头,过度到下阕,一荡上阕愁闷的情绪。用“要新诗准备”贯串“庐山色”、“赤壁浪”、“铜堤月”。不过这看似闲情逸趣,何等潇洒。其实这正是上阕的“表”与“檄”的内含。下阕怜南,也正是上阕的思北。“荆楚路”这一带是没有被敌人占领的,如此美景,宜爱宜惜。爱,就要珍重它;惜,就要保护它。特别作为北方的游子,当提到这些南方的美景时,不能不有一些思乡的酸楚夹杂于胸中。总之,只因是一个分为两片的祖国横亘在胸中,所谓“新诗”,当也是长歌之恸。以此相勉,是轻松的调侃,其实正是痛心的变异。以此寄人,不仅见趣,亦且见志。多么委宛而深厚有致。
最后点明时间。李正之是十一月入蜀的,所以他说“正梅花万里雪深时,须相忆!”是彼此双方的互勉,仍以双双作结。
这一段看似白描,似乎没有多少深意。其实如果联系历史背景,是仍然可以感到话外之音的。“正梅花万里雪深”,“梅花”是他们,又是传递消息的暗示。所谓“折梅逢驿使,送与陇头人”。“万里雪深”是写彼此的间隔,也是彼此的处境。所以是地理的,也是心理的。但不论地理的或心理的,造成可以间隔而寂寞的,终归是政治的原因。是投降派对于他们的打击。那么,在这样个废弃与远戍的道路上,他形象地即情即景,用“万里雪深”,彼此的一切,俱足以包之了。而要相互勉励莫相忘并不断传递消息的,那当然是人,所以“须相忆”是彼此的。既是人,又是事。而这人事,正是他们“志”的结集,所“须相忆”者,仍是祖国恢复之大业。因此,这是一场特殊的斗争,即抗战派在被迫流离失所时,仍在呼喊着团结。甚至可以说,通篇都是在告诫着不要忘了抗战的事业。这样分析是有心理依据的。在共同斗争中因失利而不得不分手的战友,临岐执手勉励莫相忘时,他们思想里起作用的第一要素应是斗争失利的耻辱与磨砺以须的豪情。
战友在一起当然比分散开好。他知道,投降派又何尝不知道。以是他们之间的“离别”就成为“不堪”的了。“不堪”二字,伤心之至:已不成军,不堪遣散。通篇都是对于抗战事业的悼念与惋惜。甚至连那一滴儿女泪,也要他收起,这样的心肠,要以江山为念,真正是情深意厚。
这是一首歌咏宫廷生活而有所托讽的诗。
“珠箔轻明拂玉墀,披香新殿斗腰支。”一两句描绘宫廷中的歌舞场面,正点题目。汉代未央宫有披香殿是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歌舞过的地方。唐代庆善宫中也有披香殿,“新殿”或取义于此。但此处主要是借这个色彩香艳而又容易唤起历史联想的殿名来渲染宫廷歌舞特有的气氛。对于披香殿前的歌舞,诗人并未作多少具体的铺叙,而是着重描绘了“珠箔轻明拂玉墀”的景象。珠箔即珠帘;玉墀指宫殿前台阶上的白石地面。轻巧透明的珠帘轻轻地拂着洁白的玉墀,这景象在华美中透出轻柔流动的意致,特别适合于表现一种轻歌曼舞的气氛,使人感到它和那些“斗腰支”的宫妓融为一个和谐的整体。“斗腰支”三字,简洁传神,不仅刻画出宫妓翩跹起舞的柔媚之态,而且传出她们竞媚斗妍、邀宠取悦的心理状态。同时,它还和下两句中的“鱼龙戏”、“偃师”,在竞奇斗巧这一点上构成意念上的关联。不妨说,它是贯通前后幅,暗示全诗主旨的一个诗眼。
“不须看尽鱼龙戏,终遣君王怒偃师。”三、四两句突转,集中托讽寓慨。“鱼龙戏”,本指古代百戏中由人装扮成珍异动物进行种种奇幻的表演。《汉书·西域传赞》颜师古注云:“鱼龙者,为舍利之兽,先戏于庭极;毕,乃入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鱼,跳跃漱水,作雾障日;毕,化成黄龙八丈,出水敖戏于庭,炫耀日光。”可见这是一种变幻莫测、引人注目的精彩表演。不过,从题目“宫妓”着眼,这里的“鱼龙戏”恐非实指作为杂技百戏的鱼龙之戏,而是借喻宫妓新颖变幻的舞姿。末句的“怒偃师”用了《列子·汤问》的一则故事;传说周穆王西巡途中,遇到一位名叫偃师的能工巧匠。偃师献上一个会歌舞表演的“假倡”(实际上是古代的机器人),“钡(抑)其颐则歌合律,捧其手则舞应节,千变万化,惟意所适。”穆王以为是真人,和宠姬盛姬一起观赏它的表演。歌舞快结束时,假倡“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穆王生气,要杀偃师,吓得偃师立即剖解假倡,露出革木胶漆等制造假倡的原料,终于免祸。三、四两句是说,等不到看完宫妓们那出神入化的精彩表演,君王就要对善于机巧的“偃师”怒气冲冲。
原故事中的偃师是一个善弄机巧的人物,但他却差一点因为弄巧而送命。这种机关算尽、反自招祸患的现象具有典型意义。诗人用偃师故事,着眼点正在于此。诗中的宫妓和“偃师”的关系,相当于原故事中倡者和偃师的关系;而诗中所描绘的“斗腰支”、“鱼龙戏”,又正相当于原故事中倡者的歌舞,所突出的正是偃师的机巧。那么,透过“不须”、“终遣”这两个含意比较明显的词语,可以看出,诗中所强调的正是善弄机巧的偃师到头来终不免触怒君王,自取其祸。如果把这首诗和《梦泽》、《宫辞》等歌咏宫廷生活而有所托讽的诗联系起来考察,便很容易发现“未知歌舞能多少,虚减宫厨为细腰”,“莫向樽前奏《花落》,凉风只在殿西头”和“不须看尽鱼龙戏,终遣君王怒偃师”之间有着十分神似的弦外之音。宫廷歌舞原是政治生活的一种隐喻;而迎合邀宠、红粉自埋的宫女,一时得宠、不管将来的嫔妃,和玩弄机巧、终自召祸的偃师,则正是畸形政治生活的畸形产物。在诗人看来,他们统统是好景不常的。
这首诗第一句写养蚕的辛勤劳苦。诗人在这里没有过多地描写养蚕的过程,只是用“辛勤”与“得茧不盈筐”互相对照,突出了蚕事的艰辛。人们心中充满了怨恨,因此诗人在下句说这些养蚕人“灯下缥丝恨更长”。这句诗用茧丝来比喻蚕农的恨,既形象又贴切。劳动人民每天深夜都要抽丝织布,每一缕丝都是蚕农辛酸的记录,但是他们享受不到自己劳动的果实。劳动果实被统治者白白拿去,所以在他们心中充满了怨恨,那每一声织机的声响都是劳动人民的叹息,都是劳动人民的诉说。
第三句诗锋一转,写穿绫罗绸缎的贵人。他们穿着华美的衣服,然而他们哪里知道蚕农和织妇的辛酸,他们只知贪爱绣在绸缎上的鸳鸯图案。这样,这首诗的中心思想就更为明显,更清楚地点明封建社会贫富的对立,写出劳动人民对那些不劳而获的寄生虫的愤恨和鄙视,诗的社会意义就更深刻,社会作用更广泛了。
全诗语言通俗,明白如话,前两句同后两句构成对比,使诗意更加鲜明,加强了诗的表现力,使诗的主题揭示得更加深刻。
《鱼藻》,《诗经·小雅·鱼藻之什》的一篇。为先秦时代华夏族诗歌。全诗三章,每章四句。这首诗赞颂武岂饮酒的平和安乐,有颂古讽今之意。《毛诗序》以为“刺幽岂也。言万物失其性,岂居镐京,将不能以自乐,故君子思古之武岂焉”,显然是以用为意,于诗本文无稽。
诵读诗文,朴实中寓新奇,无论是语言技巧还是结构方式甚或是总体风格都与民谣相近,陈子展以为“全篇以问答为之,自问自答,口讲指画,颇似民谣风格”(《诗经直解》),可谓贴切之论。以此反观诗原文,那种根植于民间的新鲜活泼和摇曳多姿的诗风在雅诗中独显风韵。
全诗共分三章,每章四句。每章前两句以“鱼在在藻”起兴,出语奇崛。一句四字而“在”字两见,颇具特点,对它的理解是正确诠释全诗的关键。若以冬烘之论视之,以为是凑足音节之举,不但在用法上显得笨拙,而且不合《诗经》语体。吴闿生《诗义会通》将“鱼在在藻”释为“鱼何在,在乎藻”,这样两个“在”字实为自问自答,全诗节奏以此为基调,欢快跳跃,收放有致。
三章中每章第二句对鱼的形态描写,酷似现代电影中的特写镜头,“依于其蒲”则是鱼在藻中摇头摆尾,得其所需的全景式展示。三章并提,由特写至全景,构成了一组极具情节性和象征意味的鱼藻情趣图。而诗的每章后两句则是写岂,“岂在在镐”、“饮酒乐岂”,形式上只是语序颠倒,实则暗含活动顺序和因果。春秋时代,酒是富足后的奢侈品,因而也是欢乐的象征。若无“岂乐”的心绪则不会去“饮酒”。而在酒过三巡之后,那欢乐的气氛在酒香弥漫中显得更为浓烈。宴饮之景、欢乐之情跃然纸上。第三章的“有那其居”既是对大岂居所的无限赞叹,也是对前两章因果关系上的照应。从视觉效果上看,也正是点和面、局部和全景的关系,与观鱼的空间转换一致,这样整首诗比兴和铺排和谐无间,浑然一体。
通观全诗,“鱼”和“岂”,“藻”和“镐”在意象和结构上严格对应,起兴之意昭然。但若止于此,则了无新意。先贤以为此诗“以在藻依蒲为鱼之得所,兴武岂之时民亦得所”(郑笺)。虽然武岂之说无以确证,但此说为读者揭示了鱼藻的另一层映射关系。诗人歌咏鱼得其所之乐,实则借喻百姓安居乐业的和谐气氛。正是有了这一层借喻关系,全诗在欢快热烈的语言中充分展现了君民同乐的主题。因此,从形式和内容结合的完美程度来考察,这首诗在雅诗中是较优秀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