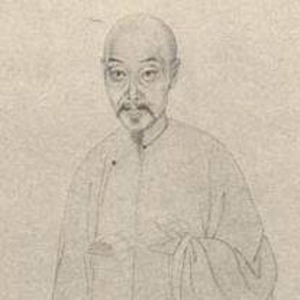这首诗的首联“楼观云开倚碧空,上阳日落半城红。”写出盛世帝京的壮丽景象。阴云散去,天空一碧。楼观巍峨,耸向碧空。落日辉映着华丽的宫殿,半座城池一片通红。但以“上阳”代指清宫,使人想到己经湮没的唐代上阳宫,接以“日落”,含有逐见衰落、好景不长之意。景象于壮丽中带衰飒。
颔联“新声北里回车远,爽气西山拄笏通。”写诗人对社会现实的态度。“北里”正在演唱新曲,管弦呕哑,轻歌曼舞,飘荡着靡靡之音,诗人转身回避,离得远远的。郊外西山,远离尘嚣,气氛清新爽朗,那里才是诗人想去的地方。北里:《史记·殷本纪》:“于是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阮籍《咏怀诗》:“北里多奇舞,濮上有微音。”后来唐代长安平康里,因在城北,也称北里,其地为妓院所在。后世称妓院所在地为北里,爽气:晋代王徽之为桓冲骑兵参军,冲尝谓徽之曰:“卿在府日久,比当相料理。”徽之初不酬答,直高视以手版拄颊云:“西山朝来致有爽气。”苏轼诗:“朝来拄笏见西山。”后世多以此喻指清高人物及其风度。此联用典,表示诗人对庸俗腐朽生活的厌弃,对清高脱俗生活的向往。
颈联“闷倚宫墙拈短笛,闲经坊曲避豪骢。”写诗人郁郁不得志,烦闷无聊,便倚着宫墙,拈出短笛来吹奏,用音乐消愁解闷。他闲暇时途经“坊曲”(小街曲巷),也不愿见到“豪骢””(骑着高头大马的豪门贵族),总是远远避开,免得见到后激起心海波澜,产生更多的愤怒和不平。一“闷”字表明内心状态。一“闲”字反映其无事可干,无所作为。他的“闲”,不是心闲、意闲、清闲、安闲,“闲”是由“闷”而来。
尾联“帝京欲赋惭才思,自掩萧斋著《恼公》。”将诗意推进一层,表明自己不依附统治者的态度。本是不欲献赋作诗,描绘帝都盛况,赞颂繁华,粉饰太平,却说“惭才思”(为自己没有才华感到惭愧)。“惭才思”三字,表面谦逊,实是不愿把才思贡献出来。它柔中带刚,绵里藏针。清高自傲、抗尘绝俗的结果,当然无法施展才华,实现抱负,无可奈何,只好自我排遣,自找乐趣。一个穷书生能找到什么乐趣呢?只能坐在萧条寂寞的陋室寒斋中玩弄笔墨,写出象《恼公》之类的诗歌。《恼公》是李贺的一首诗情浓丽、逞才斗奇的游戏之作。
这首诗,可说是诗人消极反抗的表示,也是无可奈何的自我宽解。
这首诗的首联“楼观云开倚碧空,上阳日落半城红。”写出盛世帝京的壮丽景象。阴云散去,天空一碧。楼观巍峨,耸向碧空。落日辉映着华丽的宫殿,半座城池一片通红。但以“上阳”代指清宫,使人想到己经湮没的唐代上阳宫,接以“日落”,含有逐见衰落、好景不长之意。景象于壮丽中带衰飒。
颔联“新声北里回车远,爽气西山拄笏通。”写诗人对社会现实的态度。“北里”正在演唱新曲,管弦呕哑,轻歌曼舞,飘荡着靡靡之音,诗人转身回避,离得远远的。郊外西山,远离尘嚣,气氛清新爽朗,那里才是诗人想去的地方。北里:《史记·殷本纪》:“于是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阮籍《咏怀诗》:“北里多奇舞,濮上有微音。”后来唐代长安平康里,因在城北,也称北里,其地为妓院所在。后世称妓院所在地为北里,爽气:晋代王徽之为桓冲骑兵参军,冲尝谓徽之曰:“卿在府日久,比当相料理。”徽之初不酬答,直高视以手版拄颊云:“西山朝来致有爽气。”苏轼诗:“朝来拄笏见西山。”后世多以此喻指清高人物及其风度。此联用典,表示诗人对庸俗腐朽生活的厌弃,对清高脱俗生活的向往。
颈联“闷倚宫墙拈短笛,闲经坊曲避豪骢。”写诗人郁郁不得志,烦闷无聊,便倚着宫墙,拈出短笛来吹奏,用音乐消愁解闷。他闲暇时途经“坊曲”(小街曲巷),也不愿见到“豪骢””(骑着高头大马的豪门贵族),总是远远避开,免得见到后激起心海波澜,产生更多的愤怒和不平。一“闷”字表明内心状态。一“闲”字反映其无事可干,无所作为。他的“闲”,不是心闲、意闲、清闲、安闲,“闲”是由“闷”而来。
尾联“帝京欲赋惭才思,自掩萧斋著《恼公》。”将诗意推进一层,表明自己不依附统治者的态度。本是不欲献赋作诗,描绘帝都盛况,赞颂繁华,粉饰太平,却说“惭才思”(为自己没有才华感到惭愧)。“惭才思”三字,表面谦逊,实是不愿把才思贡献出来。它柔中带刚,绵里藏针。清高自傲、抗尘绝俗的结果,当然无法施展才华,实现抱负,无可奈何,只好自我排遣,自找乐趣。一个穷书生能找到什么乐趣呢?只能坐在萧条寂寞的陋室寒斋中玩弄笔墨,写出象《恼公》之类的诗歌。《恼公》是李贺的一首诗情浓丽、逞才斗奇的游戏之作。
这首诗,可说是诗人消极反抗的表示,也是无可奈何的自我宽解。
这首诗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诉说了自己的不幸遭遇,抒发怀才不遇的愤慨心情。
诗共十二句。开头四句,紧扣“不遇”题旨,连用四个“不”字,反复叙写自己困顿失意的情形。北阙,指朝廷。首句是说自己,向朝廷上书,陈述自己的政见,表达用世的要求,但没有得到任何答复。次句化用汉代杨恽《拊缶歌》:“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的句子,意思是说自己退隐躬耕,因为天时不顺,没有获得好收成,衣食无着。第三句反用晋伏滔参加孝武帝召集的百人高会,受到孝武帝垂青的故事(《世说新语·宠礼》),借指自己不能挂名朝籍的不幸遭遇。五侯,用汉成帝同日封其舅王谭等五人为侯的典故(《汉书·元后传》),此处泛指权贵。第四句意思是:阿谀奉承权贵,可以获得利禄,但自己的性格刚正不阿,不愿这样做,只能沉沦困顿。
接着的四句,描写主人公不遇失意后漂泊困窘的生活。河朔,。茂陵,。主人公落魄以后,远游河朔,投靠一位朋友为生。但滞留他乡,依附他人的生活,使他心中产生了深沉的乡思。家人住在京城,风尘阻隔,音信全无,他们都平安无事吧?还是暂且留在北地,登山临水,流连赏玩吧。即使春天已经来到人间,和风吹拂,杨柳依依,最能惹起人的旅思,也全然不管。既思乡怀人,却又宁愿继续漂泊他乡,主人公这一矛盾的心理,极深刻地反映了他失意以后凄楚、哀伤悲愤的心情。
最后四句,主人公向友人陈述他对世俗的态度和自己的人生理想。他说:今天世上的人,只为自己着想,自私自利,我对这种现象大为不悦,内心十分鄙视。这一点,你是应当了解的。我希望先济世致用,然后功成身退,去过闲适的隐逸生活,岂肯一辈子庸庸碌碌,毫无成就,枉做一个男子汉大丈夫。主人公在失意潦倒、栖迟零落的境遇下,仍然说出如此高亢激昂的誓言,表现出他仍然有强烈的用世要求。
这首诗每四句一转韵,诗意亦随之而转换,是七古体裁中典型的“初唐体”,说明了王维的诗歌创作受初唐的影响很深。但诗中所表现的虽失意不遇,仍然昂扬奋发的进取精神,则是盛唐封建知识分子普遍的精神风貌和人生态度。
上片首三句“艅艎东下,望西江千里,苍茫烟水。”突兀而来,描写临别时的环境氛围,景象苍茫寥廓,颇有气势。“试问襄州何处是?雉堞连云天际。”这二句自问自答,展开了对襄阳的描写,将遥远的襄阳用变焦镜头拉扯到了读者眼前,空间距离因为抒情的需要在一瞬间缩短了。“叔子残碑,卧龙陈迹,遗恨斜阳里。”这三句写襄阳遗迹,暗点出两位古代英杰理想未竟而终的遗恨,为歇拍一句称赞友人作势。“后来人物,如君瑰伟能几?”歇拍一句盛赞张明之才能的卓绝,并希望他能以前贤自勉,负重自强,完成历史使命,消除先人的遗恨。
下片“其肯为我来耶?河阳下士,差足强人意。”用韩愈《送石处士序》一文成句,是词人对京西南路安抚使上书辟张明之为幕僚一事的评论,赞扬了他礼贤下士的作风,同时,亦暗示张明之此去定会得到重用。“勿谓平无事也,便以言兵为讳。”南宋统治集团实行投降政策,禁止朝野议论出师北伐之事。这二句是词人对张明之的告诫与勉励,希望他能恪尽职守,加强战备。同时也是对当权者置中原大好河山于不顾的投降政策的严正谴责。“眼底河山,楼头鼓角,都是英雄泪。”眼下河山沦丧,城楼鼓角震天,这些都足以让有志之士为痛苦流涕。这三句转入抒情,同时也点明了当前危难的局势,苍凉悲壮,体现了诗人对国事的关心,极富鼓动性。 “功名机会,要须闲暇先备。”国家多事之秋,正是为国效力,一展抱负、博得功名的机会,闲暇时千万不可麻痹大意,要常备不懈。末二句再次勉励张明之抓住机会,建功立业。这一而再,再而三的以国事、功业相勉励,顿现出送别之人与被送之人的亲密关系,送人之情意亦愈见真挚和亲切。
全词语言朴实,亲切自然,切合挚友送别之口吻。虽为送别词,却不作儿女之语,慷慨激昂,一派豪气,壮人行色,鲜明地表达了词人的爱国精神和对友人的深情厚意。
诗以清奇多姿的景语开笔,表现诗人远听太白轻雷、近看紫阁流云的归山逸趣;中间续以久滞宦途的兴叹,折为“钓竿不复把,野碓无人舂”的失意和惆怅;最后复出之以景语,留袅袅钟音于诗外。诗以山中雷鸣雨落、云烟变幻的奇观为启端,抒发了诗人对心居微官的愧悔和向往自由闲适生活的情怀。全诗语调慷慨豪迈调,绘景雄奇瑰丽,境界淡远,写得气魄非凡。
开始四句写雷雨景象,第一、二句写远景。诗人在白阁峰西面自己的草堂中,极目远眺,只听见轰然的雷声突然从终南山那面传来,震耳欲聋。“雷声傍太白”一句,起势突兀,巨响自天而降,震撼人心,具有先声夺人的咄咄气势。接着,闪逝雷煞,大雨滂沱,笼罩着莽莽苍苍的终南山诸峰。这铺天盖地的大雨,在惊雷的衬托下,更加气势夺人。第三、四句渐次而近:终南山的雷雨正向草堂汹涌逼来,东面白阁峰上的乌云,如万马奔驰,涌向那紫阁峰上的十万长松中,乌云与松林连成一片,激起满山的虎啸龙吟。开始这四句,雷鸣、雨下、云涌,写得层次分明,又错综交织,并且与终南山和白阁、紫阁诸峰相连,造成一种雄阔无比、笼罩宇宙的恢宏气势。
接着,诗人却就此陡顿,转换笔锋。“胜概纷满目,衡门趣弥浓”。是这首诗前后过渡的关键。前一句是对风雨雷电交织而成的雄壮景色的赞叹,而后一句于赞叹之中,更蕴含着丰富的内容,它表面是在进一步渲染草堂景色之胜,而实际上,是用“衡门”与帝都长安以及右内率府兵曹参军的衙署相比,京城和衙署尽管那般堂皇,但生活却是平庸枯燥的,比不上这简陋的草堂中瞬息万变、应接不暇的景色,和那游目骋怀、无拘无束的浓郁的情趣。这里已经委婉流露出了诗人追求新鲜活泼、自由无碍的生活的思想。
由这关键性的两句,引出了诗人的深深感慨。从“幸有数亩田”到末尾,以夹叙夹议的手法,抒发了自己对区区微官的不满和向往自由闲适生活的情怀。自己本有几亩薄田,可以像二仲那样过隐居的生活;也听过“达士”规劝之语,正与诗人心相通。却错误地做了个于世无补、于己不利的区区小官,现在因假而还归草堂,看到自己满身尘俗之气,无地自容啊。如今,钓竿疏远了,舂米的碓也无人操作,想起来惆怅不已,望着那日暮时渐尽的飞鸟,只听见南溪几声悠扬的疏钟。最后两句,诗人将无限怅惘之情,融进自然景物之中,结语微妙。白天四处觅食的鸟儿,随着暮色的降临,渐渐各自找到了归宿之所,而自己还滞留宦途,在异乡飘泊。那静夜里悠扬的钟声,是警醒诗人的“暮鼓晨钟”,好像是对诗人的召唤,但同时又像是轻轻的叹息。诗人用象征、映衬手法,将不尽之意隐含在最后两句。
不仅如此,这首诗的开头和结尾还形成了一种对比,隐含着诗人的深意。开始四句极写雷雨风云来势之猛,一派动荡之势,草堂似乎难以避免暴风雨的冲涮。接着,诗人虽然没有再交待风雨,但从最后两句“惆怅飞鸟尽,南溪闻夜钟”的暗示中可以看出,显然风雨往别处去了,并没有降临草堂。诗人这种章法,动荡与宁静的强烈对比,无疑地隐含着对人生变幻无常的感慨,与“早闻达士语,偶然心相通。误徇一微官,还山愧尘容”的出处无定的伤喟,正是统一的,两者交相映发,将这种迷惘而又感伤的情怀,表现得更为婉曲而又深沉。
统观欧阳词,如一人而有二面。其艳情词艳得近于淫靡,轻佻俳狎,几乎难以卒读。然如《南乡子》八首,却换了一副笔墨,一洗绮罗香泽,转为写景纪俗之词,全写广南百越少数民族地区风物。读其词,如夏日清风、久雨新晴,心神为之一爽。
这是八首之二,写景如画,写情传神,将广南少女的真率、羞涩,质朴的情状活脱脱显于纸上。词的开头两句,宛如一幅南国水乡图,而且是静物素描,不加渲染,不事润色。炎炎长夏,船儿不动,桨儿不摇,近处是以木槿花为篱(木槿为广南常见之物,夏秋间开花,红白相间,当地人常以为篱)的茅舍,远处是依稀可见的横江竹桥,静极了,也天然极了。而“画舸”与“槿花”两相辉映,又使恬静素淡之中平添了几分艳雅,也为痴男情女的出场作了引信。
下片写男女初聚之情。“水上游人”指远方来客,即“画舸”中的男子;“沙上女”与“水上游人”相对为文,即以槿花为篱的茅舍的主人,立于沙头的一位少女。至此,词人又为读者在南国水乡图上叠印了一幅仕女图,尽管这幅仕女图似乎也是静的,不过已经呼之欲出,跃跃欲动了。男子,总是主动的,勇敢的,他伫立良久,便上前问话了,问女子姓甚名谁,年庚几许,家在何处。不过,这些作者都没有写,是画外之音,是省文,但却不是凭空结想。且看,这位情窦初开的少女,欲答,又羞于答,她转身走了。走了,又不甘心,却又回头顾盼,“笑指芭蕉林里住”。这“芭蕉林”,或者就是“槿花篱”的旁景,或者竟是这女子撒了一个谎:“家可远哩,在芭蕉深处。”结句的答话,将全词的静景一下子点活了。原来“画舸”之所以要“停桡”,是因为男子被女子所吸引;槿篱竹桥,也几等于北方的“桑间濮上”;水上沙上,跃动着初恋者的倩影。
李白有《陌上赠美人》诗云:“骏马骄行踏落花,垂鞭直拂五云车。美人一笑褰珠箔,遥指红楼是妾家。”正与此词相近。然一指红楼,一指蕉林,各是自家身分。李清照《点绛唇》有句曰:“和羞走,依门回首,却把青梅嗅。”与此词的写“回顾”同一笔意。盖“回顾”这一动作最能传女子的娇羞之态,故诗人每每写及。然彼一回顾而依门嗅梅,此一回顾而笑答客问,北国千金与水乡村姑的腔范就判然分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