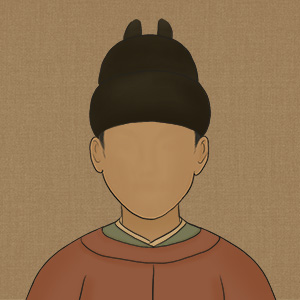此首为思妇之词。开头两句,通摄全词,点明由春色引起春恨。上片主要写春色,下片主要写春恨。上下片仿佛两个相连的画面,全词情景交融。
开始两句十二字,内蕴丰富。“深闺”暗示抒情主人公是少妇,面对恼人春色,不禁情思绵绵。一个“劳”字透露出她那“为君憔悴尽,百花时”的隐痛。由“劳”瘁而怨“恨”,可见其爱之深切。“恨共春芜长”,佳在“春芜”一词含义双重面使全句意味隽永。以春草喻离别,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远如“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楚辞·招隐士》),又如“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李煜《清平乐》)。以上“春草”都是本义,没有引申之意。而“恨共春芜长”的“春芜”,除春草本义外,还隐寓行人之意,也就是说此句不仅有闺中人的怨恨随着春草不断增长之意,还含有“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的人越远、恨越长之意。这就深化了诗意,即前人所谓得“句外意”之妙。下面三句写景,以具体意象补充首句“春色”,选取深闺“琐窗前”的视角写思妇所见所闻。“黄鹂娇啭泥芳妍,杏枝如画倚轻烟”两句宛如五代花鸟画,用笔工细,着色鲜艳。前一句声色并茂,以声为主,富有动势。黄鹂的婉啭娇鸣,似与满园春色而共语。后一句写杏枝倚立于淡淡烟霭中,恬静如画。这春色以黄鹂、红杏为主,缀以群芳的姹紫嫣红,一片暖色,再加上黄鹂悦耳的娇啼,真是“红杏枝头春意闹”不足喻其美。少妇透过琐窗听见以上春光,当比“忽见陌头杨柳色”感触更为深婉了。上片如从思维顺序出发,触景而生情,则开头两句亦可算是逆笔。
从上结至过片,时空转换为另一个画面。张炎云:“最是过片,不要断了曲意。”(《词源·制曲》)“凭阑”句既自成画面,又未断意脉。原来闺中人被春色所吸引,不满足于隔窗观花,她轻移莲步,款款伫立于阑干旁,含愁凝眸。“双娥细”,以秀眉的细长以形容其青春貌美。“‘柳影斜摇砌”,是思妇凭阑所见,也是下片唯一景语,寥寥五字,一波三折,确是词的当行本色语。表层意思是柳条之影因风吹斜而摇曳于台阶,但其中还隐含摇落了杨花、杨花飘落于“砌”两层意思。这三层意思浓缩于五字句中,写得极密。五字中没有“杨花”字样,而于下文显现,是诗人匠心所在。下文思妇的内心独白,由上片的蓄势,直至此句才引发出来。从杨花的摇落,联想自己红颜将凋零,所以她痛苦地唱出了全词的最强音:“玉郎还是不还家,教人魂梦逐杨花,绕天涯。”和开头暗相呼应。她终日盼不回丈夫,怅恨之情悠然而生,于是嗔问道:“你倒是回来不回来?叫人家成天价象在梦魂中一看,跟着那漫天的柳絮,绕世界去神游寻觅!”这种奇思遐想,意味深长,倾吐出少妇的无限离愁和情思。“魂梦逐杨花”为思妇词开创了新的意境,对后代有所影响,如晏几道名句:“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鹧鸪天》)似受此词启发,又如章楶的《水龙吟·杨花》以及苏轼的和词,咏杨花而和思妇情怀相联,也似乎受到此词的影响。
《花间》词温庭筠多丽藻,韦庄多质朴语。顾敻成就不及温、韦,此词却能熔丽藻与质朴于一炉,使之疏密相间,恰到好处。
上片首二句本自陶渊明《桃花源记》的开篇 :“醉漾轻舟,信流引到花深处。”这个“花深处”,就是指桃源。在郴州,词人为了排忧遣恨,不得不借酒解愁。醉眼朦胧之中,词人受潜意识的支配,仿佛觉得自己划起了小舟,正轻松自如地随着溪流浮泛,朝桃花源进发。路上,“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桃花源记》)。词人十分欣喜,他左顾右盼,不知不觉中,已“林尽水源”,来到了“花深处”。阅读这两句,关键是要抓住“醉”这个核心词语。醉入梦乡,本是常事,所以说这两句是写梦境幻象。“尘缘相误,无计花间住。”是词人神志清爽后的抱恨之言。佛教认为色、声、香、味、触、法六尘是污染人心、使生嗜欲的根源。秦观在这儿是借“尘缘”指世俗之事,如名利一类,自是相对灵境而言的。假如自己不出来求仕为宦,就不至于有此时的迁谪之祸,这就是“尘缘相误”。在写法上,只说“尘缘相误”,隐去尘缘的具体内容,便产生空灵蕴藉,词情摇曳生姿的效果。此刻自己身受官府羁绊,即使想找一个类似于“桃花源”的远僻之地平安度日也不可得——这就是“无计花间住”。
过片二句,勾勒出一幅“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满庭芳·山抹微云》)一般的黄昏景象。“尘尘”“千里”尤给人天涯飘泊之感。紧接一句“山无数 ”,与“烟水尘尘”呼应,构成“山重水复疑无路”(陆游《游山西村》)的境界,这就与上片“尘缘相误”二句有了内在的联络,上下片意脉不断。下片开头四句,乃是词人有意识地择取人世间的四种凄凉景象,来影射他黯淡、感伤的心境。“烟水尘尘”,则前途渺遥可知;“千里斜阳暮”,暗示着词人的处境将每况愈下;“山无数”,正是阻力重重、难回朝廷的象征;“乱红如雨”,就是说美好事物正在横遭摧折。这四种景象并集一起,凝现出巨大的艺术感染力。词人虽无片言只语关涉愁苦,而愁苦、失望之情已溢满纸面。结句“不记来时路”,源于《桃花源记》。陶渊明说,武陵渔人出桃花源后,在返家的路上处处作了标志,“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这个结句正暗应了题目和开头,道出了词人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的窘境和苦况,表达了他“抽身退步悔已迟”和“世外桃源不可得”的愁怛心绪。
这首词所反映的思想,是作者由于无端遭受打击,导致了他对现实的不满,并由此产生了对世外桃源的向往。但有的评论者认为句句都有暗寓,这只能是一种猜测。此词所表现出的那种迷离恍忽的境界,只是秦观在艺术上喜欢朦胧美的一种手法而已。
此文的开头,欲擒故纵,引出论题。六国“以五倍之地,十倍之众”的绝对优势,却相继为秦所灭,乃是决策者目光短浅,“不知天下之势”之故。随之,从当时的“天下之势”展开论述。
文中反复论证秦与六国争天下,关键就在韩、魏之郊野。因为对秦来说,韩、魏首当其冲,若韩、魏不附,乃是其腹心之疾;对山东之各诸侯国来说,韩、魏是他们理想的屏障。所以在七雄相斗的形势下,韩、魏的地位就显得特别重要。这就是当时起决定作用的“天下之势”。
形势摆出之后,接着从正反两方面引例作证。以秦来说,范雎受秦重用,立即助秦昭王收韩;商鞅受秦重用,则助秦孝公收魏。当韩、魏未附秦之时,昭王出兵攻齐,范堆忧之。由此证明秦欲争得天下,必先收韩、魏而后可。当秦军越韩过魏而攻燕赵,这本身是件冒险之举,若燕赵正面迎战,韩、魏再乘机击之于后,那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秦人远攻燕赵,却毫无韩、魏之忧,那是因为韩、魏屈于秦之淫威而已归附它的原故。文章写到这里,再作收束,归结到“天下之势”。如此说来,韩、魏附秦是不识天下之势了;进而又为其开脱:韩、魏本身势孤力弱,面对虎狼之秦,又怎能自保而不归附于秦呢?其中自含山东各诸侯国“不知天下之势”而不助韩、魏杭秦之意。正由于六国都不能正视天下之势,以致秦人得以东指而“天下追受其祸”。
末段再从各诸侯国着笔,阐明作者为其构想的“自安之计”。当时的天下之势,一方面韩、魏不能单独抗拒强秦,另一方面,山东各诸侯国又要借助韩、魏以巴秦。那最好的办法就是山东诸国应不惜代价去“厚韩亲魏以摒秦”。这样,就会出现另一种局面:秦人不敢越过韩、魏的土地远攻齐、楚、燕、赵;而齐、楚、燕、赵也就能安居后方。一旦齐、楚、燕、赵能与韩、魏通力合作,相互支援,那秦国就不能有所作为。这确是当时拯救六国危亡的良方。末尾笔锋一转,回到冷酷的历史现实:即六国决策者目光短浅,不识“天下之势”,彼此“背盟致约,以自相屠灭”,以致“秦兵未出而天下诸侯已自困突”,从而自食恶果,相继灭亡。文章截然而止,含不尽感慨。
全文紧扣“天下之势”,纵论六国与秦争天下中的成致得失,层层解剖,鞭辟入里,说透“自安之计”。而笔又一气流注,曲折尽意。
杜甫、王维、岑参三首和《早朝大明宫》,其艺术成就都超过了贾至的原作。在诸和诗之中,杜甫的和诗以其格律谨严而著称,王维的和诗以其气象阔大而驰名,至于岑参的这首和诗,则以其押韵奇险、属对精工与用语之典丽而深获历代论者之盛誉。
诗一开头,先由作者在早、朝途中的所见所闻写起。这两句是说,诗人早朝上路之时,听见雄鸡正在报晓,看到东方刚微露曙光,觉得天气仍有些凉意;时值暮春三月,流莺百啭,在这京都之内不时可闻其鸣。首句写“鸡鸣”、“曙光”,交待早朝上路的时间,点题巧妙而又自然。在时间概念上也比贾至原诗首句“银烛朝天紫陌长”的笼统交待显得确切。次句写“莺啭”、“春色”,描绘京城暮春时节清晨的景色,呼应贾至原诗第二句“禁城春色晓苍苍”的写景。两相比较,贾诗所写之春景比较模糊,形象不鲜明,“春色晓苍苍”,艺术感染力实际上并很不强。究其原因,即在于拂晓之时天色尚暗,描写此时景物仅仅诉诸于视觉印象,其难度较大。岑参深谙其中奥秘,故其诗首联写景时,既写其所见之“曙光”、“春色”,又写其所闻之“鸡鸣”、“莺啭”,甚至写到其身心所感觉之“寒”,准确地抓住了暮春时节清晨之时景物和气候的特点,从视觉、听觉、感觉等不同角度进行描写,艺术感染力自然就强了不少。
“金阙晓钟开万户,玉春仙仗拥千官”,与王维和诗的颔联一样,岑诗颔联联写的也是早朝时的场面:伴随着金銮殿里传出的朝钟声,一扇扇宫门依次而开;在汉自玉台春两侧排列着皇家的仪仗,文武百官们按部而朝见皇帝。“金阙”、“玉春”,其辞藻富丽堂皇,正适合表现皇宫的金璧辉煌和雕栏玉砌。以“金”对“玉”,以“万”,对“千”,其对仗典雅精工,又与早朝时庄严整肃之朝仪相谐。因此若论气象之阔大,岑诗此联诚逊于王诗,若沦辞藻之富丽与对仗之精工,则岑诗又在王诗之上。
岑诗的颈联颇得后世论者之青睐,南宋著名诗人杨万里在其著《诚斋诗话》中论及贾至等人的这组早朝大明宫唱和诗时曾说:“和此诗者,岑诗云‘花迎剑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干’,最佳。”在杜甫、王维均参与唱和的情况下,岑诗此联能获得如此高的评价,是不容易的。此联的佳处即在于它既写了早朝的场面又抓住了时间早这一特点,既呼应贾至的原作又表现出岑诗的语言特色:鲜花迎接饰有佩剑的官员,柳条轻拂仪仗的旗帜,此时晓星方落,露犹未干。作为一首早朝诗,应处理好“早”与“朝”之关系,即在空问上应围绕朝见之场面来写,在时间上又要体现出一个“早”字。贾、杜、王三人的唱和诗,均以首联写早朝之时间,以中二联写一早朝之场面,唯岑诗此联能将“花迎剑佩”、“柳拂族旗”之场面与“星初落”、“露未干”之时辰融为一体,以一联表现了他人需两联才能交待清楚的内容。作为一首和诗,岑诗此联的景物描写又与贾至原诗互为呼应,进一步充实了对春色的描写。不过贾至的原作中,写景与朝见结合得不紧密,结果出现了首二联写景,颈联写朝见,尾联倡和的格局,对于一首早朝诗来说,其中心不突出,显得本末倒置。因此,王维在和其诗时,以中二联写朝见场面,突出了重点。但王诗也有不足,即忽视了贾至原作中的春色描写,与之呼应不紧。观王诗,竟通篇于春色未着一字,反倒用了不少笔墨不厌其详地一再写君臣之服饰,首联已云“翠云裘”,颈联又写“衮龙”,颔联则先写“衣冠”,又继以“冕旒”,语意颇嫌重复,而不腾出笔墨来呼应一下贾诗中之春色。前人对此有“衣冠冕旒,句中字面复见”之讥(《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五)。虽说王诗成就很高,此等不足毕竟是瑕不掩瑜,但相比之下,总是不如岑诗之唱和得体、一呼应紧密而又能避免其中心不突出之缺陷。最后,此联之语言亦颇能体现岑诗之特色。纵观贾、杜、王三诗之颈联,均有御炉香烟等字样,可见在早朝诗中写香烟之类已成司空见惯之例。岑参显然不满足于此等俗套,故全诗无一语道及御炉香烟而于此联写出了“剑”、“旗”、“星”、“露”等较之其他三作显得很新奇的景语。所谓边塞诗人与宫廷诗人之别,于此大概亦可略见一斑。
“独有凤凰池上客,阳春一曲和皆难。”诗的结尾,响应贾至的倡议:唯有身居凤池的中书省贾舍人,你这一曲高雅的阳春自雪和起来实在困难。说和诗难,倒不仅仅是出于对贾至的恭维,或是表现自己的谦逊,这“难”字确实流露出岑参内心的真实感受。一同和诗的王维、杜甫,都是久负盛名的大诗人,与之同和一诗确实不易。王维久任朝官,写起宫廷唱和诗来简直是轻车熟路;杜甫做诗刻苦,语不惊人死不休,又尤长于律诗。诗友在某种意义上又是诗敌,同和一诗实寓有一较短长之意,因此在这场高水平的竞赛中若无高超的手段是根本不可能争先的。后人在评价这组唱和诗时多以岑参此诗为最佳,其致胜之诀不外乎下列三点:
其一曰“押韵奇险”。写宫廷诗,古人多以富丽之辞藻充做韵脚,如贾诗之“御炉香”、“侍君王”、杜诗之“醉仙桃”、“有凤毛”、王诗之“拜冕旒”、“衮龙浮”等,均是其例。岑参不排斥富丽之辞藻,但更偏爱奇丽之辞藻,体现在此诗之韵脚上,便是“曙光寒”、“春色阑”、“和皆难”、“露未干”等出乎人们意料的辞藻与奇特的押韵。在宫廷诗中,“寒”、“阑”、“干’、“难”等韵脚是不大有人问津的,更不用说以之作为早朝诗的韵脚了,这些词汇,通常是用以表现衰残之景的,将它们写入早朝诗中而不减损富丽堂皇之气,需要有高超的写作技巧。稍一不慎,便成败笔,在前人看来这简直是在走独木桥,故称这些韵脚为险韵。正是在这种他人通常不敢尝试之处,岑参成功地进行了尝试,收到了后世公认的奇特的艺术效果。具体说来,“寒”通常会引起人们的蜷曲畏缩之感,但岑诗的“鸡鸣紫陌曙光寒”给人的感觉便全然不同,雄鸡一唱天下白,黑暗即将让位于光明,那鸡鸣令人振奋,那曙光令人憧憬,那暮春清晨的微寒令人惬意。奇妙的艺术效果的取得就在于诗人在以“寒”为韵脚时恰当地进行了搭配,这一点在“阑”、“干”、“难”等韵脚上同样得到了体现。“阑”本用于几写残景,但诗人配之以“春色”、配之以“莺啭”,效果便截然相反。春阑不同于秋阑,花虽疏而叶更茂,红虽瘦而绿益肥,加之以流莺百咐,越发显得生机勃勃。其他如,’干”、“难”等韵脚,均各有妙用。在美学领域中,也处处存在着辨证法。岑诗中这几个韵脚,押得虽险而丽,虽丽又奇,颇能体现岑诗尚奇丽之特点。
其二曰“对仗精工”。对于律诗来讲,中二联对仗即已足矣,岑诗多用一联对仗,意在与早朝时那种左右分班、文武对列的朝仪相协调一致,以诗歌形式上的工整表现诗歌内容即早朝场面的严整。另外前人已经指出,此诗首联以“紫”对“皇”,极为典丽,岑参此诗对仗之精于此亦可见一斑。在这四首唱和诗中,论对仗之精工典丽,唯杜诗可与岑参此诗相敌。
其三曰“辞藻典丽堂皇”。岑参虽尚奇丽,但并不排斥典丽堂皇之语。在岑参此诗中,虽然有若于奇险之韵脚,但也有不少典丽堂皇之造语,其例如“紫陌”、“皇州”、“金阙”、“玉春”等,绝不亚于其他三诗。早朝诗毕竟要写宫廷气象,若一味追求奇险就有可能破坏诗中画面的和谐。岑诗虽押险韵而未过份,又用了若干典丽堂皇之辞藻表现宫廷气象,恰到好处地取得了平衡。其诗虽奇而又未离格,达到了奇不离正,正中有奇,得心应手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