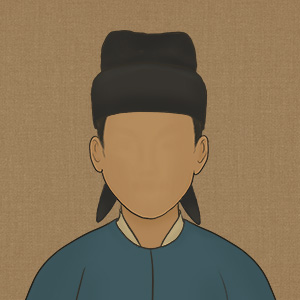关于孔子作《曳杖歌》前后的情况,在《礼记·檀弓上》、《孔子家语·终记解》以及《史记·孔子世家》等书中都有大体相同的记载。兹引《礼记·檀弓上》中的相关文字如下:
孔子蚤作,负手曳杖,消摇于门,歌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当户而坐。子贡闻之,曰:“泰山其颓,则吾将安仰?梁木其坏,哲人其萎,则吾将安放?夫子殆将病也。”遂趋而入。夫子曰:“赐,尔来何迟也!……予畴昔之夜,梦坐奠于两楹之间。夫明王不兴,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将死也。”盖寝疾七日而没。
东汉郑玄在上述引文之末注解说:“明圣人知命。”所谓“知命”,字面意思是了解自己的命运;比较科学的解释,也就是依据已知的情况对未来作出较为近是的预测。孔子唱这首歌时,只是一种预感,接着病倒了,七天后去世,正应验了他预感的正确。活着,活得清醒;快去世时,也不糊涂。大概这就是孔子之所以为孔子,也是这首《曳杖歌》所要昭示世人的这一层意思吧。
从《礼记》的记载中可以知道,孔子在吟唱这首《曳杖歌》之前,心灵上正经历着微妙的深刻的变化:夜里他做了一个不祥的梦,梦见正坐在两个廊柱之间被人祭奠;他早早地起了床(“蚤作”),或许梦醒后就一直未曾睡着吧;他反背着手,拖着手杖,孔颖达解释“负手曳杖”说:“杖以扶身,恒在前面用。今乃反手却后以曳其杖,示不复杖也。”(《礼记正义》)所谓“示不复杖”,意思是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不会再用手杖了;他还“消摇于门”,从屋内走到门口,显出一副放松随便的样子。“消摇”,即“逍遥”,安闲放松的样子。孔颖达说:“夫子礼度自守,貌恒矜庄。今乃消摇放荡以自宽纵……示不能以礼自持。”又说“负手曳杖”与“消摇于门”二句,“并将死之意状”(引书同上)。正是在这样一种特殊的心态支配之下,孔子这位在二十多年前已早知“天命”的哲人,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也不能不长歌当哭,动情地唱出这首留恋人生、爱惜生命、无奈地直面死亡的悲歌。
《曳杖歌》全文只三句。前两句用比拟,以物比人,以“泰山”、“梁木”拟“哲人”。“泰山”是众山所仰的高山,现在泰山快要崩塌,众山就无可瞻仰了。“梁木”是放置檩条、椽子的地方,现在梁木快要折断,檩条、椽子就无可依托了。紧接着这两个比喻的句子,末句直接说到自身。“哲人”,乃夫子自道;“萎”,原指草木枯死,引申为病危。上述做梦等种种潜意识的以及行为上的异常情况,令孔子自感已经病入膏肓,将不久于人世了。孔子的高足子贡,这天早上刚好来看望老师,听了这首歌,由“泰山”、“梁木”的比喻,他想到了“哲人其萎”的后果将是十分严重的。他所说的“则吾将安放”,意思是他们这些学生就将永远失去孔子这位诲人不倦、可敬可亲的好老师了,不觉心情黯然。
全诗三个句子,虽有前两句的比喻与后一句的直陈两个层次,但因感情真挚,比喻贴切而又形象,且句式整齐,每句的第三字都用表示“大概”或“将要”的副词“其”字,故仍不失一气呵成、流利紧凑的即兴吟成的本色。
这是一首触景写情之作.细腻动人。前半首写室外勾画了一幅凄清的场景。后半首转入室内,掩紧屏风熏炉中的香早已燃成灰烬,不见一丝温暖。这一切,无不透着凄冷之意。而看花之人此时无言胜有言,是对柔弱之花被摧折的叹息,是对自身命运不能由自己掌握的悲哀。
这首小词结构层次分明,井井有条地描摹出了一幅画面。先写室外,再写室内,最后点到愁怨之人。本篇虽短小精悍,但却层层深入,极见情味。纳兰长于小令,由此篇亦可见一斑。一开始便发问:何时下起了这么大的雨?把屋檐下的花儿都淋湿了。那个惜花之人默默地看着那些被风雨摧残的。
此词或可视为纳兰对自身处境的一个婉曲表达,从中可见词人内心的悲凉。
首句点题,说明自己行程。“烟瘴”二字,切岭南气候,暗示自己因为避乱到连州,过着很艰苦的生活。次句具体写流亡生活对自己身体的摧残,连用“疾病”、“衰颓”、“不堪”三词,突出环境的恶劣,也隐隐将自己对国事的忧愁略加表露,语意低沉深挚。历来诗人都喜欢把情感寄托在对风物的吟咏之中,这两句诗切定“烟瘴”,从而直述种种不堪,也是采用这一手法。
三、四句笔锋忽转,不再写自己,转说小儿女不知道是逃难,坚持说眼前的景物比江南还好。这两句看似平常,实际上颇见构思之苦。诗以“避地”二字为主脑。眼前的风光,未必不如江南,关键是诗人此番是逃难而来,他又是江南人,见惯江南景色,如今颠沛流离,心情不佳,遥望故乡,战火不息,他怎会对眼前的景色赞赏呢?他又怎么会有心情欣赏眼前的秀丽景色呢?反过来,儿女年幼,没有大人那样的忧愁,自然感觉不同,说眼前的景色胜过江南。诗人这样写,正是通过小儿女的不解事,反衬自己的忧思,所以用“强言”二字为小儿女定位,道出心中无限凄楚。苏轼《纵笔》“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酒红”,将心中的感慨借小儿的误会诉出,寓庄于谐,兴味无穷;杜甫《月夜》“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直接说小儿女无知,表示自己悲伤。吕本中这首诗也通过小儿女的不懂事来表达自己的感情,尽管取径不同,仍然很有可能是受了前人的启发。
诗前两句从正面直说,写得很凝重压抑;后两句从侧面衬托,表面上作轻描淡写,实际上将原本的痛苦渲染得更加深沉。吕本中诗自附于江西诗派,讲究“悟入”、“活法”,这首诗写得沉浑老成,就是从杜甫诗入径,而加上了自己的变化。
这是一首广泛传颂的名作,诗情画意,十分动人。
此诗首句刻画了人物形象,第二句概括自己数十年间、千万里路的遭遇与心情,再接以“此身合是诗人未”自问,最后结以充满诗情画意的“细雨骑驴入剑门”,形象逼真,耐人寻味。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全诗别出心裁,构思新颖,含蓄地表达作者报国无门、衷情难诉的情怀。
作者先写“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销魂”。陆游晚年说过:“三十年间行万里,不论南北怯登楼”(《秋晚思梁益旧游》)。梁即南郑,益即成都。实际上以前的奔走,也在“万里”“远游”之内。这样长期奔走,自然衣上沾满尘土;而“国仇未报”,壮志难酬,“兴来买尽市桥酒……如钜野受黄河顿”(《长歌行》),故“衣上征尘”之外,又杂有“酒痕”。“征尘杂酒痕”是壮志未酬,处处伤心(“无处不销魂”)的结果,也是“志士凄凉闲处老”的写照。“远游无处不销魂”的“无处不”(即“处处”),既包括过去所历各地,也包括写这首诗时所过的剑门,甚至更侧重于剑门。这就是说:他“远游”而“过剑门”时,“衣上征尘杂酒痕”,心中又一次黯然“销魂”。
引起“销魂”的,还是由于秋冬之际,“细雨”蒙蒙,不是“铁马渡河”(《雪中忽起从戎之兴戏作》),而是骑驴回蜀。就“亘古男儿一放翁”(梁启超《读陆放翁集》)来说,他不能不感到伤心。当然,骑驴本是诗人的雅兴。李贺骑驴带小童出外寻诗,就是一个佳话。李白、杜甫、贾岛、郑棨都有“骑驴”的诗句或故事,而李白是蜀人,杜甫、高适、岑参、韦庄都曾入蜀,晚唐诗僧贯休从杭州骑驴入蜀,写下了“千水千山得得来”的名句,更为人们所熟知。所以骑驴与入蜀,自然容易想到“诗人”。于是,作者自问:“我难道只该(合)是一个诗人吗?为什么在微雨中骑着驴子走入剑门关,而不是过那‘铁马秋风大散关’的战地生活呢?”不图个人的安逸,不恋都市的繁华,他只是“百无聊赖以诗鸣”(梁启超语),自不甘心以诗人终老,这才是陆游之所以为陆游。这首诗只能这样进行解释;也只有这样解释,才合于陆游的思想实际,才能讲清这首诗的深刻内涵。
这就是说,作者因“无处不销魂”而黯然神伤,是和他一贯的追求和当时的处境有关。他生于金兵入侵的南宋初年,自幼志在恢复中原,写诗只是他抒写怀抱的一种方式。然而报国无门,年近半百才得以奔赴陕西前线,过上一段“铁马秋风”的军旅生活,旋即又要去后方充任闲职,重做纸上谈兵的诗人了。这使作者很难甘心。所以,“此身合是诗人未”,并非这位爱国志士的欣然自得,而是他无可奈何的自嘲、自叹。如果不是故作诙谐,他也不会把骑驴饮酒认真看作诗人的标志。作者怀才不遇,报国无门,衷情难诉,壮志难酬,因此在抑郁中自嘲,在沉痛中调侃自己。
一般地说,这首诗的诗句顺序应该是:“细雨”一句为第一句,接以“衣上”句,但这样一来,便平弱而无味了。诗人把“衣上”句写在开头,突出了人物形象,接以第二句,把数十年间、千万里路的遭遇与心情,概括于七字之中,而且毫不费力地写了出来。再接以“此身合是诗人未”,既自问,也引起读者思索,再结以充满诗情画意的“细雨骑驴入剑门”,形象逼真,耐人寻味,正如前人所言,“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但真正的“功夫”仍在“诗外”(《示子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