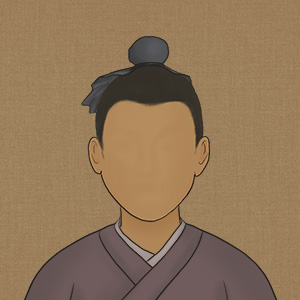这首诗从题目看,该诗似乎是由读《封建论》引发诗兴的,然而诗中的主要观点交锋,则是聚焦在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中论列的儒家、法家及法家代表人物秦始皇的是非问题上。诗首联即明确涉及秦始皇及其“焚书坑儒”举动。郭沫若之“骂”,简而言之,既包括非议、斥责、抨击其“苛政”及其“苛政”中的“焚坑”之举,也包括过分否定秦始皇的历史功绩。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认为,秦始皇是不顺应向“封建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的,是“站在奴隶主的立场”搞奴隶制暴政的人物,而“焚书坑儒”即其暴政中的暴行之一。
“焚坑”是“过”是“罪”,还是非“过”非“罪”,对此历来众说不一,或将之作为“苛政暴政”之证据,或视之为对付和打击“奴隶制复辟势力”的有力措施。毛泽东在诗句中是选用褒义词“事业”来状写它的,在毛泽东的观念里,“焚坑”是服从维护秦始皇开创的“大一统”之“事业”的,是与其“统一中原”的伟业相关的,是维护其“统一基业”“统一大业”的一种措施和手段。既然连“焚坑”都无须过分责备,那么不言而喻,秦始皇的其他政治举措就更无须责备了。因此毛泽东既诚恳又严肃地奉劝郭沫若:对秦始皇应当“少骂”,你对“焚坑”所持的“暴行说”是需要“商量”的。换言之,即对秦始皇的历史功业应多肯定,少否定,多否定甚至根本否定的观点是不对的。诗题特意用了“呈郭老”三字,接着首联又用了“劝”字、“君”字和“商量”二字,使这首“论战”诗一起笔就带有彼此商榷和探讨有关中国历史人物的看法之和睦融洽的氛围,有助于消解对方的心理压力和自危心态。
该诗的首联着意于历史性、肯定性地评价秦始皇及其下令实行的“焚书坑儒”举动有利于维护秦王朝“统一大业”的合理性;颔联则着意于在特定的历史范围内及相互对比中,肯定秦始皇创立“大一统”的秦朝的历史功绩远胜于只讲“空话”而无政治实践成果的孔丘。颔联出句是与颔联对句的“孔学”强烈对比着的。毛泽东在这里是认为,被学界一部分人评价得过高的“孔学”,其实如同无多大价值的“秕糠”一样。看战国时代的历史实践检验的结果:秦始皇以统一战争消灭了割据的诸侯国而破天荒第一次建立了“大一统”的秦王朝,可孔丘的那些学说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变革”“历史飞跃”的政治实践中却无法实施、几无所用,这岂非如同无多大价值的“秕糠”。毛诗领联该是主要置于“战国时代”的特定历史范围之内而言的,因而“秕糠”之说该是有其真实性及合理性的。
如果说,颔联是从特定的“战国时代”的视角来评说,那么颈联则主要是从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的视角来评说,它进一步把秦始皇和秦王朝置于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予以肯定性评价。郭沫若学识渊博,才华横溢,其书对先秦社会历史及当时诸流派的诸多人物等,做了研究和评说,当年曾被学界誉为“颇多创见”之著述。毛泽东对郭沫若的诸多学术成果历来是十分赞赏的,如郭沫若于1944年发表的总结明末李自成起义军最终失败的历史经验教训的《甲申三百年祭》,就曾得到毛泽东的赞赏和使用;又如郭沫若在《奴隶制时代》等著作中提出的中国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的分期在春秋、战国之交的论断,毛也表示赞成。而对“十批”,为何毛则笼统地断言“不是好文章”。就毛泽东历来就不赞成“崇儒反法”的观点以及此诗之主旨而言,主要是因为“十批”否定秦始皇、肯定孔丘学说的崇儒抑法的基本观点,与毛泽东的观点相悖。毛泽东认为:“十批”中批判“秦王政”,可是“百代都行秦政法”。总之,颈联着意于肯定秦始皇开创的中央集权的行政统治体制的重要历史进步作用及其深远的历史影响,并认为与此相悖的观点是不对的。由于“十批”只“骂”(否定)秦始皇而未充分肯定秦始皇的历史功绩,因此是不能称为“好文章”的。
尾联“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在前三联的历史性和肯定性评价秦始皇的基础上,尾联着意指出:对秦始皇的历史功业,远在唐代的柳宗元早就肯定过,今人千万别不及柳子厚而持历史倒退观点。柳子厚论说文代表作之一是尖锐抨击苛政的《捕蛇者说》,毛泽东则特别看重他的《封建论》,并且奉劝郭沫若要“熟读”(反复阅读、深思、领会)柳宗元的《封建论》,因为毛泽东认为,此政论文涉及的废“分封”、削“藩镇”、实行和加强中央集权与统一的“郡县制”的行政体制的主张和本质精神是对的。“莫从子厚返文王”,意译之即:不要从柳子厚否定“分封制”和主张废“分封”的观点,又退回到肯定搞“分封”的周文王时代的观点上去。所谓“分封制”,即君王把土地分封给宗室和功臣,让他们分别在分封的土地上建立由君主统辖的“诸侯国”,其结果往往是形成诸侯割据的四分五裂的局面。毛泽东在这里是认为,连唐人柳宗元都不否定秦始皇首废“封建制”(分封制)和首立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的历史功绩,都反对“分封制”而主张顺应历史发展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难道今人尚不及古人。其实质是认定:历史是不会走回头路的;同时奉劝郭沫若也要熟知和接受此番道理和此种观点,不要持“历史倒退”的观点。
此诗写的是历史题材,涉及中国古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及人物,可属咏史诗。虽然不能断定此诗与毛泽东在当年特殊背景下的“政治运动”思维毫无关联,但从诗句本身来看,如何评判秦始皇的历史功业,应是它的主旨所在。此诗内含丰富,无渊博、扎实的史学功底,难以创作出如此之诗,应视为造就、构成毛诗的“史诗性”的重要诗作。
这首诗首联写自己长久客居外地,终于可以回到桐庐。颔联从时间着笔,写傍晚舟中所见。颈联从经过的山水着笔,写归途景物。尾联写自己只听见雁声而未见雁鸟,与“岁暮”相呼应。这首诗明暗相衬,动静结合,绘声绘色,给人以清晰的立体状的画面感。
这首诗首联是说:长久客居外地,不觉已经出现花白的头发了。此刻从桐庐乘着扁舟独自归来,表现出思归之情非常殷切。
颔联:“新月无朗照,落日有余晖。”从时间着笔,示傍晚舟中所见。这两句自然清颖,富于理趣,表面上信手拈来,实由洗练而出。时当上弦,新月已上,在落日余晖的映衬下,天空中浮起了一弯眉月,而此时天边霞彩,却显得绚丽可爱。澄江如练,余霞成绮。虽然新月还未能朗照,却也带着些淡淡的晴彩了。东天的如眉初月,西天的夕阳在山,人在舟中,俯仰成趣。
颈联是从经过的山水着笔,写归途景物。时近黄昏,晚风渐紧,渔浦边上已聚集了渔舟,暮潮也随着兴起。江岸那边的龙山一带,升上了阵阵些微的炊烟,远方也见到星星的灯火。天空渐渐呈现了暮色,作者所乘的船儿,也便停泊了下来。
尾联:“时闻沙上雁,一一皆南飞。”在泊舟之后,听到沙洲上已有落雁的声音。在草木黄落的深秋,鸿雁是惯于南飞的。现在一行行南飞的归雁,已在寻求它们歇宿的地方了。作者于凝静中看到“平沙落雁”的情景,而所见之景、所闻之声,却都是动态,这些景象,使作者更生思归之情。这两句和诗的起笔相应,显示出“物犹如此,人何以堪”的意味。全诗作意,正在于一个“归”字。
这首五律描绘了一幅江南水乡冬季独具特色的暮江晚景。最后一联用“闻”字写人惊雁飞,使整个图景延伸出无限幽思,静僻处顿添神采,犹如雁高飞而留馀响,渺远飘逸。这首诗,思致清远,刘攽《中山诗话》说:“潘阆诗有唐人风格,仆谓此诗,不减刘长卿。”刘长卿在唐代被称为五言长城,其诗句如“离人正惆怅,断月愁婵娟”、“石横晚濑急,水落寒沙广”,皆与此诗相近。
此词为思妇闺怨之作。上片写别后离愁。望长天灰云漫漫,一行大雁正如自家一样唳声哀哀地飞向远方的空茫。“湿云粘雁影”中的“湿”、“粘”二字用得十分绝妙。云湿,意味着将要落雨,它能将雁影“粘”住,表明雁飞得无力而缓慢,其实这都是词人眺望云空雁阵时的一种主观的感觉,这种感觉是独特的、准确的,因而当他用一个千锤百炼后的“粘”字将这种感觉贴切地表现出来时读者就觉得非常新颖、触目,立刻就和自身曾经有过体验发生共鸣,不禁击节叫绝。仰望云天之后,词人便放眼前瞻,前面长路漫漫,征尘迷濛,“愁远”之情自然又涌上心来。家乡是一步比一步离得远了,亲人的面影,昔日的温馨纷乱如丝地在自己的心头缠绕着,剪不断,理还乱,又怎能整出个头绪来呢?
以下词人继续抒写旅途的辛劳和感怀。“疏钟催晓,乱鸦啼暝”二句写出他晓行夜宿的情状,清晨晓钟催他出发,黄昏乱鸦迎他寄宿。一个“催”字点出千金难买的光阴之倏忽不停;一个“啼”字点出在昼逝夜来的匆促行旅中心情之哀伤如乱鸦的悲鸣。其实“疏钟”也无所谓“催晓”,“乱鸦”也无所谓“啼暝”,这“催”与“啼”不过是诗人.的一种感觉,一种内心情绪的外化,是诗人.主观情绪对客观外界景物的渗透。“花悰暗省”以下数句是诗人.在行旅的寂寞中对昔日欢情追忆与眷恋,诗人.与新欢的相逢只能在梦中恍惚的瞬间;而音书的久杳则更增添了心中的幽怨与怅恨。
下阕进一步抒写词人客居异乡的情怀。“孤迥”二字是一个总的概括,“迥”者,深远也。孤寂因离家愈远而愈深,真乃“离恨恰如芳草,更行更远还生”者也。“盟鸾心在”数句表明词人盟誓之心不变,但毕竟不能如仙人似地跨鹤出世,在茫茫红尘之中前程尚难逆料,情丝还是趁早斩断为好;然而正待剪时,反而惹得旧情更浓,怀恨更炽。这样就把词人对恋情欲罢不能的矛盾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怕天教何处”三句是一个诗意的象征和哲理性的感喟,从字面上说,诗人.是吟叹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有双飞的燕子,就难免衔落花染蕊粉;实际上是指人,都难于逃脱男女之爱,而一旦为爱所持,便难于摆脱相思之苦,这是古往今来人类注定的宿命。因此接下来词人便在想象中遥对他的所思者说:“咱们都对着菱花镜瞧瞧吧,看谁在相思中瘦得最厉害?在外飘泊的我一点都不比你少瘦呵!”看来词人陆叡实在是位情种,他的痴心并不比他闺中的所爱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