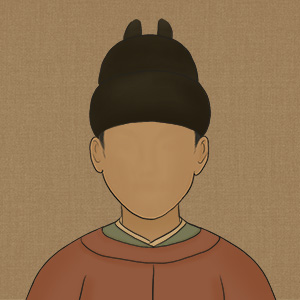这首词上片首三句明写荷花,实写美人,以“碧玉堂深”点出美人所居之地;以“水”兼写“小芙蓉”及美人所在玉堂的清姜环境。后三句连用“闭”、“掩”、“倚”、“拖”四个有独特含意的动词,把女主人公如痴如醉如怨的情状淋漓写出。
下片“迟迟”二句以乐景写愁情,以鸳鸯兴相思。结尾二句,是女主人公对上二句“凝望”后的瞬间表情,如梦如幻,以笑写愁,笑得愈沉醉,愁情也愈酸楚。
唐诗中写景通常不离抒情,而且多为抒情而设。即使纯乎写景,也渗透作者主观感情,写景即其心境的反光和折射;或者借用比兴,别有寄托。而这首写景诗不同于一般唐诗。它是咏夏天的暴雨,既不能从中觅得何种寓意,又不能视为作者心境的写照。因为他实在是为写雨而写雨。从一种自然现象的观察玩味中发现某种奇特情致,乃是宋人在诗歌“小结裹”方面的许多发明之一,南宋杨诚斋(万里)最擅此。而《溪上遇雨二首》就是早于诚斋二三百年的“诚斋体”。
再从诗的艺术手法看,它既不符合唐诗通常的含蓄蕴藉的表现手法,也无通常写景虚实相生较简炼笔法。它的写法可用八个字概尽:穷形尽相,快心露骨。
夏雨的特点是来速疾,来势猛,雨脚不定。这几点都被诗人准确抓住,表现于笔下。急雨才在前山,忽焉已至溪上,叫人避之不及,其来极快。以“坐看”从容起,而用“忽惊”、“却是”作跌宕转折,写出夏雨的疾速。而一“衔”一“喷”,不但把黑云拟人化了(它像在撒泼、顽皮),形象生动,而且写出了雨的力度,具有一种猛烈倾注感。写云曰“黑”,写雨曰“猛”,均穷极形容。一忽儿东边日头西边雨,一忽儿西边日头东边雨,又写出由于雨脚转移迅速造成的一种自然奇景。这还不够,诗人还通过“遇雨”者表情的变化,先是“坐看”,继而“忽惊”,侧面烘托出夏雨的瞬息变化难以预料。通篇思路敏捷灵活,用笔新鲜活跳,措语尖新,可喜可愕,深得夏雨之趣。
就情景的近似而论,它更易使人联想到苏轼《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中的一首:“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比较一下倒能见出此诗结构上的一个特点。苏诗虽一样写出夏雨的快速、有力、多变,可谓尽态极妍,但它是只就一处(“望湖楼”外)落墨,写出景色在不同时间里的变化。而此诗则从两处(“前山”与“溪上”)着眼,双管齐下,既有景物在不同时间的变化,又有空间的对比。如就诗的情韵而言,苏诗较胜;如论结构的新奇,此诗则不宜多让。
可见,诗分唐宋是大体的区分,不能绝对看待。王渔洋曾列举宋绝句风调类唐人者数十首,是宋中有唐;另一方面,宋诗的不少倾向往往可以追根溯源到中晚唐,是唐中有宋。大抵唐诗经过两度繁荣,晚唐诗人已感难乎为继,从选材到手法便开始有所标新立异了。这个唐宋诗交替的消息,从崔道融《溪上遇雨二首》诗中是略可窥到一些的。
这首词的上片重在写景,通过写 景来抒情说理,寓理于景,寓情于景。景、情、理浑融一体。“秦望山头,看乱云急雨,倒立江湖。不知云者为雨,雨者云江?”开篇直截了当,写登高望远所见。“秦望山”,因秦始皇南巡时曾登此山观大海,祭大禹,故名。“乱云急雨,倒立江湖。不知云者为雨,雨者云江?”乌云翻滚,暴雨如注,给人翻江倒海一样的感觉。一时烟雨茫茫一片,分不清哪个是云,哪个是雨。“乱”“急”“倒立”“不知”等词语写出了狂风暴雨的骇人气势和壮观景象。“不知云者为雨,雨者云江”,语出《庄子·天运》:“云者为雨江?雨者为云江?”庄子的意思是云兴雨至乃自然之理,没有什么意志和力量的驱使。作者引用此语除了突出狂风暴雨的凶猛气势外,也有狂风暴雨是自然现象这个意思。但是,老子说过“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这不,刚才还是狂风暴雨,现在天气就变成了“长空万里,被西风变灭须臾。”这句承上,仍是作者所看到的景象,表意急转,作者的情绪也急转直下。刹那间西风便把云雨吹散,露出了万里晴空。“回首听月明天籁,人间万窍号呼。“天籁”,自然界的音响,这里指风。在明亮的月光下,回头听见,西风在天空中呼啸而过,大地上无数的洞穴发出了尖厉的声音。这句从视觉写到听觉,表现了自然现象的复杂多变。纵观上片,好像作者只是为了表现狂风暴雨这种自然现象,但联系当时的社会形势来看,不难发现作者有更深的用意在。作者借暴风骤雨到云散雨收,月明风起这种自然现象的变化,暗示着抗金之路虽然看似曲折,但前途一片光明,广大民众的抗敌呼声如同夜空刮过的西风,将会变成巨大的积极力量影响着时局朝着乐观方向发展。下片引用典故,以古喻今,影射现实,告诫当局不要重蹈覆辙,应奋发有为。“谁向若耶溪上,倩美人西去,麇鹿姑苏?至今故国人望,一舸归欤。”这里用的是春秋时吴越争霸的故事。作者在这里用这个故事,强调的是吴国国王因为不图长远之计,耽于安乐而亡国。意在告诫当朝统治者应该引以为戒,不要重蹈吴国的覆辙,应该奋发作为,一雪国耻。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登高怀古,占据他心灵的不是秦皇、大禹,也不是越王勾践,而竟是范蠡。这是因为范蠡忠贞不二,具有文韬武略,曾提出许多报仇雪耻之策,同作者的思想感情息息相通。辛弃疾和范蠡,条件相当,但境遇悬殊,范蠡功成名就,而自己壮志难酬,两相比较,作者不由伤感痛心,情绪低落,引出下句“岁云暮矣,问何不鼓瑟吹竽?”作为答句,引出最后一句“君不见、王亭谢馆,冷烟寒树啼乌!”难道你没有看见,像王亭谢馆那些当年的行乐之地,现在已是一片萧条冷落,烟雾笼罩着秋天的树木,乌鸦在悲凉地叫着!作者的无奈伤感之情溢于言表。
这是一首登临览景而咏史怀古之词。上片写登蓬莱阁所见壮丽雨景,极具变化倏忽之致。下片怀想西施旧事,对此作者流露出同情敬仰之意。“岁云暮矣”以下,表达作者对世事沧桑所采取的及时行乐的思想。全词情调统一于自然与人事的变幻,使人产生无常之感。特别多引用庄子玄妙之句,使这一特点显得更为突出。
全诗三章,每章四句。为先秦时代陈地汉族民歌。是一首歌月怀人的诗。这诗描写一个月光下的美丽女子。每章第一句以月起兴,第二句写她的容色之美,第三句写行动姿态之美,末句写诗人自己因爱慕彼人而慅然心动,不能自宁的感觉。《诗经》是汉族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对后代诗歌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月出皎兮”,天上一轮圆月洒着皎洁的银辉,这夜色显得格外的美丽。这是写景,也是写情。这句交待了诗人活动的背景是在一个月光明丽的夜晚,这本身就富有很大的魅力和诱惑力,容易使人对景生情,发出许多美好的联想。同时,结合下句,这句又有着比兴的作用,以月光的美来比喻所爱人的美,是很恰贴的。
“佼人僚兮”反映出这时在诗人的眼前,出现了一个娇美的女子,引起他无限的爱慕和情思。天上有着皎洁的月光,地上有着娇美的女子,此时此刻,此情此景,花好月圆,天惬人意。
“劳窈纠兮”一句写诗人仔细端详女子时的感觉。在月光下,她不但显得容貌皎好,而且身材那么苗条、秀美,真让人神颠魄荡;而更吸引人的,是她还有一种气质美,她举止劳缓,雍容大方,性情安静,而这气比外表更富有魅力。“劳心悄兮”,此句是诗人自言其心情的烦闷。月光美,人更美,那窈窕的身姿象那雍容的举止,使得诗人一见钟情,而又无从表白,因而生发出无限的忧愁和感慨。
这首诗的景色描写很有特色,“月出皎兮”,“月出皓兮”,“月出照兮”,柔美的月光本身就有无限的情意,而让它作为背景来衬托,则女子的倩影愈发显得秀美。同时,月光朦胧下,一个线条优美的女子在缓缓起步,更增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有一种朦胧美的韵味。所以,这一景色很富有画意,而画意又渗透了无限的诗情。
《月出》的意境是迷离的。诗人思念他的情人,是从看到冉冉升起的皎月开始的。也许因为月儿总是孤独地悬在无垠的夜空,也许因为它普照一切,笼盖一切,所谓“隔千里兮共明月”(谢庄《月赋》),月下怀人的作品总给人以旷远的感觉。作者的心上人,此刻也许就近在咫尺,但在这朦胧的月光下,又似乎离得很远很远,真是“美人如花隔云端”(李白《长相思》)。诗人“虚想”着她此刻姣好的容颜,她月下踟躅的婀娜倩影,时而分明,时而迷茫,如梦似幻。
《月出》的情调是惆怅的。全诗三章中,如果说各章前三句都是从对方设想,末后一句的“劳心悄兮”、“劳心慅兮”、“劳心惨兮”,则是直抒其情。这忧思,这愁肠,这纷乱如麻的方寸,都是在前三句的基础上产生,都由“佼人”月下的倩影诱发,充满可思而不可见的怅恨。其实这怅恨也已蕴含在前三句中:在这静谧的永夜,“佼人”月下独自地长久地徘徊,一任夜风拂面,一任夕露沾衣,她也是在苦苦地思念着自己。这真是“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张若虚《春江花月夜》)。
《月出》的语言是柔婉缠绵的。通篇各句皆以感叹词“兮”收尾,这在《诗经》中并不多见。“兮”的声调柔婉、平和,连续运用,正与无边的月色、无尽的愁思相协调,使人觉得一唱三叹,余味无穷。另外,形容月色的“皎”、“皓”、“照”,形容容貌的“僚”、“懰”、“燎”,形容体态的“窈纠”、“懮受”、“夭绍”,形容心情的“悄”、“慅”、“惨”,可谓一韵到底,犹如通篇的月色一样和谐。其中“窈纠”、“懮受”、“夭绍”俱为叠韵词,尤显缠绵婉约。
望月怀人的迷离意境和伤感情调一经《月出》开端,后世的同类之作便源源不断,李白《送祝八》“若见天涯思故人,浣溪石上窥明月”,杜甫《梦太白》“落月满屋梁,犹疑见颜色”,常建《宿王昌龄隐处》“松际露微月,清光犹为君”,王昌龄《送冯六元二》“山月出华阴,开此河渚雾,清光比故人,豁然展心悟”,此类甚多,大抵出自《陈风》。不管它们如何变换着视角,变换着形式,变换着语言,但似乎都只是一种意境,一种情调,即迷离的意境,怅惘的情调。这种意境与情调,最早也可以追溯到《月出》。这些滥觞于《月出》的望月怀人诗赋作品,总能使人受到感动与共鸣,这也正如月亮本身,终古常见,而光景常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