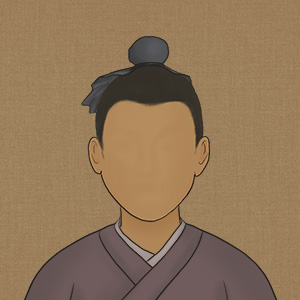“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两句是远景,一句写物景,一句写人景。据此,我们不妨这样想,诗人在清明节这一天来祭扫,未到坟茔聚集之地,即以目睹此景,因墓地往往在深处,怕妨路径,故一眼必是望到远景。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场景呢?“南北山头多墓田”,“南北”当是虚指,意即四面八方。是不是就可以解成“四面八方的山头上有很多墓田”了呢?难道我们竟没有体会出诗人说这句话时无限悲凉的口吻吗:“(你看啊!)四面八方的山头上竟然有这么多的墓田,(那些可都是死去的人啊!)”这样解就丰满得多了。下面人景也就很是顺理成章了,墓地多,自然来祭扫的人也就多了:“清明祭扫各纷然”。可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各”指每家祭扫每家的毫不相干,“纷然”则指人数众多。那么既然人数众多,何以“各人自扫门前雪”呢?难道不会出现相互帮助、相互劝慰的场景吗?须知道,人们一般只有在什么情况下才会互不搭腔,就是已经痛苦难过到了极致,以致习惯成自然,各自心知肚明,无需多言。
“纸灰飞作白蝴蝶,泪各染成红杜鹃。”两句,诗人走上前去,镜头拉近,细节刻画物景与人景:“纸灰飞作白蝴蝶,泪各染成红杜鹃。”字面上很好说,就是说冥纸成灰,灰飞漫天,好似白色的蝴蝶;相思成泪,泪滴成各,仿佛红色的杜鹃。可为什么要以纸灰作蝴蝶,泪各作杜鹃,而不是旁的什么?我们都知道中国古代美丽的神话中有庄周化蝶、杜鹃啼各的范式。那么就清楚了:原来蝴蝶是沟通阴阳二界的使者啊,冥纸当然就是起到这样的作用;同样的,相思要怎么样来表达才最恳切,总不至于老是“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已时”一类的吧,这样就浅薄了。“我”要告诉阴间的人,“我们”想你想得都把眼泪哭干了,现在啼出来的是各啊!这种震撼力,实在是难以言表的。
“日落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灯前。”承接上句,依照时间发展续写诗人的所见所想:“日落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灯前。”出句当然是虚景,哪里会有这么巧让诗人碰到狐狸在冢穴里面睡觉呢!不过是说,一天的祭扫结束了,日薄西山,人人各自归家,但“我”知道,只有一种动物是不会离开的,那便是狐狸。你凭什么这么说?虽然“我”没有看见,但“我”竟连“狐死必首丘”的道理也不懂吗?你们这些人,祭扫之时哭哭啼啼,平日里哪里见到你们有丝毫的伤心难过?狐狸却不同,它们始终对同伴、对“家庭”忠诚无二,即使死了,也要将头对准丘穴的方向!真是“狐犹如此,人何以堪”啊!这一层强烈的反差不经仔细的推敲是得不到的。可是哪里知道反差更强烈的还在后头:晚上回到家来,看到孩子们在灯前玩闹嬉戏,他们怎么会知道“我”的心酸,怎么会知道生离死别的痛苦?这于我们来说,又是一个极大的冲击。可是还不止如此,我们再挖掘下去就发现:这些孩子都还那样弱小,是那么天真无邪,可是终归要长大,终归要衰老,终归也要死去,这是天命所在,是多么得令人遗憾,令人神伤。你看,这里正好与首联我们提到的诗人厌倦死亡的思想相照应了。是不是吃了一惊,短短十四个字,居然内涵多至如斯境地,且皆为感人心魄,发人深省之语。
“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九泉。”诗人要总结了,也算是表达自己的态度:“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九泉。”应当说这是比较易见的文人士大夫的心理常态,就是及时行乐。我们读到这里,定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古诗十九首》里那么成系统地高唱“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或者会更直接想到“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但果真如此简单吗?我认为关于这一点我们存在一种认识上的误区:即并未区分与判断抒发及时行乐思想究竟是已臻化境,心本开阔,还是无奈愁极,故作旷达,这一点是极重要的问题,是可以作为专题来研究的。就高翥这首诗而言,显然是故作旷达无疑。你看,诗人尚在阳间,就已经想到死后别人祭祀他的酒他一滴也尝不到了,可见他对这个世界是何其留恋!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由此可见欲望能使人丧失本我,渐成依赖。
原本下面该是艺术手法的分析,因又要涉及理论,与我想要表达鉴赏的最初的心理流变旨趣不合,故略去。高翥是南宋后期江湖诗派的重要作家,且为宁波人,可以说,无论从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与我近来研究的楼钥有偶合之处。
这是一首以春雨为背景来写闺怨的歌词,风格颇似北宋前期的晏殊欧阳修。
词的开头两句“一曲歌成酒一杯,困人天气好亭台。”显然袭用了晏殊《浣溪沙》开头之“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晏殊“一曲新词”之“新”,是与后句中之“去年”及“旧”字相照应的,为下阕抒情“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作了很好的铺垫。这里中白所写题材与大晏相同,画面背景也有相似之处。以“歌成”取代“新词”,未见佳妙;但后句“困人”二字则显然紧扣“春雨”的背景,并为写闺怨的主题作好准备,妙在信手拈来,不露痕迹。
“沉沉春昼斜飞雨,寂寂闲亭乱点苔”二句,即是承“困人”二字展开来说的。天气何以“困人”?只缘“沉沉春昼斜飞雨”,春天白昼较长,“沉沉”此处有“漫漫”、“漫长”之意。“斜飞”二字,写春风颠狂,又与下句“乱点”二字相照应。由于春昼漫长,风雨不断,所以闺亭终日紧闭。一“闲”字是与“寂寂”二字相呼应的,骤雨终日,自然不会有客来访,因而显得“寂寂”,只有台下的青苔,在春雨润湿下,任意蔓延滋长。两句有声有色的写景,为下片写闺怨提供了一个典型环境。
换头三句写春雨之中百花纷谢。“花几簇,锦千堆”二句,极写春日繁花处处可见,或一丛丛,一簇簇,或万紫千红,锦绣成堆。然而经过春雨摧残,终于“落红成阵”。帘内的思妇,眼见众花零落,映照香腮,极易产生美人迟暮之感。“映香腮”二字亦人亦花,亦花亦人,“花面交相映”,含不尽之意。思妇不忍看这众芳凋零的景象,“不如却下帘儿坐,自看同心七宝钗。”钗为女性首饰,“七宝”指多用宝物装饰。“同心”二字有二义;一是钗本身是由两股合成,如夫妇同心;二是暗示此钗乃其所爱者所赠。因百花凋零而有美人迟暮之惧,美人迟暮又有为所欢抛弃之惧。怎样才能避免这一后果,消释眼前愁闷呢?关键在于所欢对自己始终不渝的爱,故结尾两句,以看同心钗来自我慰藉,生动地传达了她此时的心态。
这首词颇似温庭筠的《菩萨蛮》组词,作者虽是常州派的后劲,但看不出这首词有何深沉的寄托。从艺术上看,此词除开头两句袭用晏殊词句外,还在于较注重意境的刻划。“沉沉”二句形象生动地从形和声两方面写出春雨的神态。而“落红成阵映香腮”,则以暮春的落花飞雨,烘托闺中人的寂寞无聊,而又于百无聊赖中透露一丝相思的恋情。人总是既生活在现实中,又生活在希望中的,没有希望就没有生活。全词即在这向往中收住,留下耐人寻味的余地。
这是一首题画词,词题叫《题君善祝发图》。君善,生平不详。明长乐人敖继公字君善,官至信州教授;是否其人,不详。祝发,断发; 即削发受戒为僧人。此等题目很少有人在诗词中道及,沈氏却于此落墨,才识诚不同寻常。词的上片入手擒题,“闷怀难表。西风弄,愁人踪迹颠倒。”发语即从一“闷”字写起。削发之人,大都因人事磨难,际遇坎坷,对现世人生灰心失望,看破红尘,遂起遁入空门之念。所以说满怀愁怨苦闷,难以表达。加之秋风惹弄,搅得人心神错乱。“笑拼华发付凄凉,露泣芙蓉老。”揽镜自照,但见白雪满头,华发萧骚;凄然一笑中,饱含了无限辛酸之情。接着以秋江上衰老芙蓉捧露如泪的描写,来烘托画面上主人公的冷落心境。“梦破柳烟蝴蝶晓”句,用庄周梦为蝴蝶的典故。《庄子·逍遥游》:“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遽遽然周也。”这里借以表达一种人生如梦、虚幻非真之意。“沈吟掷镜寒云扫”,“沈吟”二字颇有份量,表明祝发并非易事,是有过痛苦的思想斗争的; 而 “掷镜”则表明经过斗争,最终毅然割断尘缘的决绝态度。“寒云”,比喻衰白的头发。“寒云扫”指抛却一切尘念,将华发削净,就像风扫残云一般。于是万事皆休,一无所有,一无所求,一无所得。“但倩取幽窗月影,夜半留照”,幽窗残月,独伴愁人; 万籁俱寂,万念皆灭。
下片首三句系接“世事总休休”而来,向画里祝发者指出狂与醉都是憔悴的原因,因为心动处无非易致狂态,而愁来时每易借酒浇愁。接下来去谈求静与消愁之妙谛。“绕崖黄叶正纷纷,好共哀猿啸。”黄叶纷纷,哀猿长啸; 景象萧瑟,气氛悲凉。接下来又深入一层,写 “落蕊楚江君莫恼,芳洲处处悲秋草。”这两句既是景语,又是情语。是词人劝慰画中祝发人不要为花落楚江而懊恼,君不见,秋风里,芳洲处处悲秋草。这组意象具有明显的暗示性,暗示着人生无处不苦辛,人生无时无烦恼;而遁入空门,反倒怡然自得、悠然自适、恬淡清闲。“自有闲云飞伴,松月山空,桂丛烟渺。”结句显得飘逸空灵,柔和美好。闲云自在,松月清幽,空山寂寂,桂香袅袅。置身其中,自然令人忘怀尘世得失,不知今夕何夕了。
这首词意境清冷,色彩幽暗。据词人之弟沈自徵于词人去世后所作《鹂吹集序》云: “(姐)赋性多愁,洞明禅理,不能自解免。虽一生境遇,坎壈为多, 亦良由禀情特甚, 山花开落,陇月盈亏,光阴往来,荣瘁互代;而台前镜里,偏多踯躅之怀,绿水芳丛,恒如摇落之感;……触绪兴思,动成悲惋; 香笺盈泪,彩笔余辛。”可见女词人平生多愁善感,故其作亦如“怨鹤空山,离鸿朝引”(同上) 。这首词的基调也是如此。因词人“洞明禅理”,受佛老思想影响,所以对祝发弃世之事,并无微词;相反,流露出一种神往之情。其艺术上的特色: 一是将画里和画外的描写有机结合起来。题画词既以画面为主,从画面生发开来; 又能不为画面所囿,写出了词人和画里人的感情共鸣。二是情景交融。词中所描写的西风、幽窗、黄叶、落蕊等一组凋残、萧瑟之景,与画里画外人所抒发的闷、愁、悲、哀之情,和谐一致,有水乳交融之妙。三是结构井然,文思如剥蕉见心,运笔如盘中走珠,极回环跌宕之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