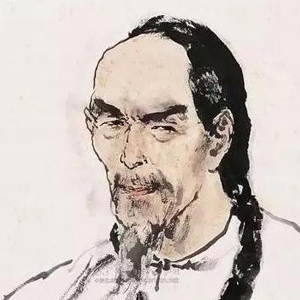这是一首咏物诗,咏物中尤多寄托,具有浓郁的象征性。句句写的是蝉的形体、习性和声音,而句句又暗示着诗人高洁清远的品行志趣,物我互释,咏物的深层意义是咏人。诗的关键是把握住了蝉的某些别有意味的具体特征,从中找到了艺术上的契合点。
首句“垂緌饮清露”,“緌”是古人结在颔下的帽带下垂部分,蝉的头部有伸出的触须,形状好像下垂的冠缨,故说“垂緌”。古人认为蝉生性高洁,栖高饮露,故说“饮清露”。这一句表面上是写蝉的形状与食性,实际上处处含比兴象征。“垂緌”暗示显宦身份(古代常以“冠缨”指代贵宦)。这显贵的身份地位在一般人心目中,是和“清”有矛盾甚至不相容的,但在作者笔下,却把它们统一在“垂緌饮清露”的形象中了。这“贵”与“清”的统一,正是为三四两句的“清”无须藉“贵”作反铺垫,笔意颇为巧妙。
次句“流响出疏桐”写蝉声之远传。梧桐是高树,着一“疏”字,更见其枝干的高挺清拔,且与末句“秋风”相应。“流响”状蝉声的长鸣不已,悦耳动听,着一“出”字,把蝉声传送的意态形象化了,仿佛使人感受到蝉声的响度与力度。这一句虽只写声,但读者从中却可想见人格化了的蝉那种清华隽朗的高标逸韵。有了这一句对蝉声远传的生动描写,三四两句的发挥才字字有根。
“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这是全篇比兴寄托的点睛之笔。它是在上两句的基础上引发出来的诗的议论。蝉声远传,一般人往往以为是藉助于秋风的传送,诗人却别有会心,强调这是由于“居高”而自能致远。这种独特的感受蕴含一个真理:立身品格高洁的人,并不需要某种外在的凭藉(例如权势地位、有力者的帮助),自能声名远播,正像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说的那样,“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这里所突出强调的是人格的美,人格的力量。两句中的“自”字、“非”字,一正一反,相互呼应,表达出对人的内在品格的热情赞美和高度自信,表现出一种雍容不迫的风度气韵。唐太宗曾经屡次称赏虞世南的“五绝”(德行、忠直、博学、文词、书翰),诗人笔下的人格化的“蝉”,可能带有自况的意味吧。沈德潜说:“咏蝉者每咏其声,此独尊其品格。”(《唐诗别裁》)这确是一语破的之论。
清施补华《岘佣说诗正像曹丕在》云:“三百篇比兴为多,唐人犹得此意。同一咏蝉,虞世南‘居高声自远,端不藉秋风’,是清华人语;骆宾王‘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是患难人语;李商隐‘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是牢骚人语。比兴不同如此。”这三首诗都是唐代托咏蝉以寄意的名作,由于作者地位、遭际、气质的不同,虽同样工于比兴寄托,却呈现出殊异的面貌,构成富有个性特征的艺术形象,本诗与骆宾王的《在狱咏蝉》,李商隐的《蝉》成为唐代文坛“咏蝉”诗的三绝。
实际上,咏蝉这首诗包含着诗人虞世南的夫子自道。他作为唐贞观年间画像悬挂在凌烟阁的二十四勋臣之一,名声在于博学多能,高洁耿介,与唐太宗谈论历代帝王为政得失,能够直言善谏,为贞观之治作出独特贡献。为此,唐太宗称他有“五绝”(德行、忠直、博学、文辞、书翰),并赞叹:“群臣皆如虞世南,天下何忧不理!”从他不是以鲲鹏鹰虎,而是以一只不甚起眼的蝉来自况,也可见其老成谨慎,以及有自知之明。
这首诗的首联从反面切入,写聚会,偏从离别的象征物杨柳写起,构思奇特,然后次句以“未拟还”拉回,又以谢朓比谢榛,切姓,又切身份;颔联由上“未拟还”生出,把他不归说成不得归,暗中达到颂扬的目的;颈联在谢榛布衣的身份上做文章,说他不屑仕进,而交游遍天下;尾联收缴全篇,说他终将与妻子高隐;尾联一纵一收,收放自如,巧妙地化用典故,为谢榛转圜,把他高人诗客与出入京华富贵之家的形象组织在一起,处处为他占身份,虽是颂扬,但颂扬得十分得体。
京城送走了严冬,又迎来了春天,路边的杨柳抽出了长长的嫩条,正好供行人攀折话别,而谢榛却游宴歌咏于京师,还没有回乡的意思。古人有折杨柳送别的风俗,《三辅黄图》云:“灞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后诗词中多引为赠别语,如唐王之涣《送别》云:“杨柳东门树,青青夹御河。近来攀折苦,应为离别多。”这首诗写的是聚会,却偏从离别的象征物杨柳写起,构思奇特,非才力大于凡人者难以做到。对句以谢朓比谢榛,即切合其姓,又符合他诗人的身份。而西园又是达官贵人府第的代称,并以文人游宴赋诗而著名,谢榛在京城与当朝大佬过从甚密,诗用西园典,与他的行事密切吻合。李攀龙论诗与“前七子”遥相呼应,力主“诗必盛唐”,特别心醉杜甫。杜甫的赠人诗以用典切合人的姓氏身份著称,如《送翰林张司马南海勒碑》“不知沧海上,天遣几时回”,用张骞泛槎事切其姓。又如《敬简王明府》:“叶县郎官宰,周南太史公。”以汉叶县令王乔比王明府,切其姓与身份。李攀龙此句正是他学杜甫的经意之作。
古时提倡清高,对隐逸之士往往推许褒扬,对曳裾侯门者往往多微词。所以首联说了谢榛滞留京师不归,出人权贵之门后,颔联立即拉回弥补。诗说谢榛年事已长,由于苦吟和久居他乡,暗换了青青发,每逢春天到来,魂梦不由得萦绕着故乡的青山。这就把谢榛不归说成了不得归,他出入朱门也就非其所愿。而是由于权贵们仰慕他的诗名。这样对谢榛出入人海的行止作解释,便达到了颂扬的目的。
颈联在谢榛的身份上大作文章,说他生当清明盛世,正是可以出仕为帝室效力的时候,他却托病不起,甘以布衣终其身,虽然无官无禄,清寒贫苦,却结交遍天下,声名籍籍。尾联则进一步说谢榛虽然目前游走京师,最终仍然要像隐士庞德公一样,偕妻子高隐故乡。这两联仍然是一纵一收,处处为谢榛转圜,把他描绘成高人与诗客的结合体,为他占尽身份。虽是颂扬,而颂扬得非常得体,不露谀媚之态,无论是受者、旁观者都能坦然接受。
读古诗时总感觉到写赠答诗犹如送礼,措手颇费斟酌,且碍于情面,很难写得实事求是,恰如其分,更难表达真实感情。李攀龙这首诗巧妙地化用典故,收放自如,以精湛的技巧弥补了感情的不足。
这首诗是作于李攀龙与谢榛刚刚缔交时,诗竭力加以捧扬赞美。后来李攀龙论诗与谢榛发生龃龉,王世贞等人站在李攀龙一边,干脆把谢榛排斥在七子之外,自己做起领袖来。明代的世风,到了嘉靖年间已日现颓势,反映到诗人中,便同类相引,异己相斥,互相攻讦,忽离忽散。“后七子”后来一遭公安派的轰炸,马上溃不成军,未尝不是这种世风下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