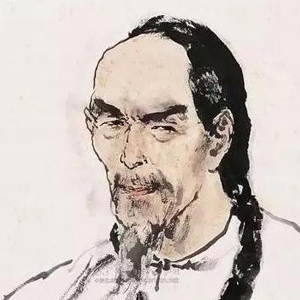这篇散文开篇先交待名号“五斗先生”的来源,然后介绍自己嗜酒的原因,最后他批评为养生而著论的嵇康、为途穷而哭返的阮籍,表明自己远离生世之扰,摆脱万物之累的决心。这篇散文属于自传性小品,短小精悍,字字珠玑。
鲁迅先生曾感叹:“批评一个人的言行实在难”(《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就以王绩的《五斗先生传》来说,如果说这是他自己为自己写的“传”,无庸置疑,王绩就是一位“绝思虑,寡言语,不知天下有仁义厚薄””万物不能萦心”,只知醉酒的糊涂先生。如果能这样论定,而且其结论又可靠,是很容易,可是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首先,这自号“五斗先生”的王绩本非如此,他对自己的一生曾经作过比较全面的回顾:“弱龄慕奇调,无事不兼修……明经思待召,学剑觅封侯。弃绢频北上,怀刺几西游”(《晚年叙志示翟处士》)。可见他本与一般出身世家的青年一样,深受儒学教养,满怀建功立业的壮志,而且也颇有才气,“君性好学,博闻强记……阴阳历数之木,无不洞晓”(吕才《东皋子集》序)。可生活给予他的只是“才高位下”,失意的情怀,简放的个性,仕途的险恶,加之隋末唐初的社会动乱,才使他萌发出退隐的念头,但排难解纷,有所作为的希望,也还未完全泯灭,这就是他所说的“中年逢丧乱,非复昔追求……解纷曾霸越,释难颇存周”(《晚年叙志示翟处士》)。真正绝意仕途,皈依自然,还是四十几岁以后的事情,所谓“晚岁聊长想,生涯太若浮。归来南亩上,更坐北溪头……自有居长乐,谁知身世忧”(同上)。于是乎释、道,尤其是道家思想,便成了他观照世界和人生的哲学。然而生活毕竟是现实的,那种“绝思虑,寡言语”,“万物不能萦心”等等,总是很难办到的。他在“一饮五斗”之外,也要考虑到家庭的生计、子女的婚嫁,这就如他在《独坐》中写的:“问君樽酒外,独坐更何须?有客谈名理;无人索地租。三男婚令族,五女嫁贤夫……”。他还说过“物外知何事,山中无所有。风鸣静夜琴,月照芳春酒。直置百年内,谁论千载后。张奉娉贤妻,老莱藉嘉偶。孟光倘未嫁,梁鸿正须妇”(《山中叙志》)。有琴有酒,尚嫌不足,还想娶一位贤淑的妻子共同偕隐。除了这些之外,他还要写诗作文,这都是很现实的。但是,正是这种现实才给他带来了另外一面,那就是失意的苦闷,与解脱苦闷的思考。“古来才命两相妨”,如今的境遇证明了个人的命运是无法把握的。不过就算是帝王将相,君不见有汉一代曾经是“何其赫隆盛,自谓保灵长。历数有时尽,哀平嗟不昌。……金狄移灞岸,铜盘向洛阳。君王无处所,年代几荒凉”(《过汉故城》)。兴衰更易,沧海桑田,亦是“忽焉而去,倏然而来,其动也天,其静也地”。既然是来不可阻,去不可留,一切在“天”,在“地”,在自然,那么万物自然不必“萦心”,也没有什么苦闷可言。这就是他所见到的“天下”,以及他认为生活在这样的“天下”应持的态度。由此观之,嵇康大谈“养生”,阮籍途穷而哭,实在是多余的,因为性命非善求可得,途亦无所谓穷通,“盛衰自有时,圣贤未尝屑”(《古意六首》)。所以“圣人”就处于“昏昏默默”的境界,一切不知,一切不谈,委身自然。但是,并非人皆“圣贤”,王绩大概也不敢自封“圣贤”,那要进入“圣人所居”的境,就要回到原来的命题上,只有“以酒德游于人间”,做“五斗先生”,长醉不醒,才可以“昏昏默默”,“不知所如”了。那么自号“五斗先生”的王绩,是否完全进入了这个境界,前面已经说过——没有。因此,要说这传中的形象,就是王绩的真貌,恐怕不妥;要说与他无关,也不准确,因为他毕竟是一位“平生唯酒乐,作性不能无”(《田家三首》)的“斗酒先生”;比较客观地看,这里有他的一些“影子”,而更主要的是在于表现他晚年对老庄哲学的追求与向往。这追求与向往又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遁世伤时,保全自己,与苦闷愤懑,牢骚不平等等思想感情的复合体。
五斗先生是本文的传主,但不能就此认定是作者的小传,不过文中确有作者自己的影子。五斗先生绝尘脱俗,浑身道家风韵,一切顺其自然,物我皆忘,竟是在“醉乡”中寻觅到了快乐的活法。他期望“昏昏默默”的境界,然而又只有借助于酒,才能追求到这样的境界。这便是一个力图摆脱尘世烦恼者的幸与不幸。由此也可以看出本文的主旨不仅仅是宣扬饮酒的妙处。
这篇寓言讲述养猴子的人残酷剥削猴子,猴子觉醒后群起反抗的故事,揭示了靠权术奴役百姓而不讲法度的人迟早要遭到反抗并必然灭亡的道理。全文语言简练古朴,与主题相映生辉,耐人寻味。作为寓言,《楚人养狙》包括寓言故事和教训两个部分。
这篇寓言故事分三个层面。
第一层写狙公对猴子的剥削和压迫:“赋什一以自奉。”这是不劳而获,亦即剥削行为。“鞭箠”则是压迫。在这种情况下,猴子们都害怕狙公,虽以摘取果实为苦事,但不敢不依从。这是压迫的表面效果。
第二层交代故事的发展。这一层逻辑十分谨严,小猴子提出的第一、二两个问题可谓前提,第三个问题属于结论。前提和结论之间,有着合理而又深刻的同一性和必然性。作者故意让小猴子提出问题,一方面寄寓着老猴子麻木不仁、因循保守,小猴子思维敏捷、无所顾忌的用意;另一方面,又暗含着对于残剥削和压迫,连入世不深的小猴子也认识得一清二楚的内涵。这两个方面,相反相成,互为补充。作者在这一层中,着重从揭露剥削的角度进行思辨和启迪,从而增加了故事内涵的深刻性。
第三层叙述故事的结果:众狙相携入山不返,狙公卒饿死。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刘基的笔下众狙不再盲从,并非愚昧,它们有了自己的思索与追求。作品的第一层交代的“弗敢违也”,实际上并不是压迫和剥削的必然后果,而是暂时现象。被剥削、被压迫者一旦觉醒,就必然会产生像第三层所叙述的反抗行动。
这则寓言给予统治者的教训是深刻的,它不是一般的哲学道理和道德理念,而是带有锋芒的政治主张。寓言的实质是刘基赋予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地位与价值,体现了刘基对人的尊重,对自我的尊重。作为元王朝残酷统治的目击者,刘基的这则寓言,带有极大的现实针对性。它实际上变成了元王朝覆灭的预言。
就形式而言,《楚人养狙》中的寓言故事有三个特点。
其一是通俗生动,新鲜活泼。寓言实际上是一种比喻,而寓言故事则是比喻中的喻体。因为蛮横无理地奴役百姓,势必激起反抗的道理比较抽象,直接陈说又很可能遭到封建统治者的镇压,所以作者引譬设喻,用拟人化的修辞手法,虚构了猴子造反的故事,给抽象的道理描绘了一幅形象的图画。
其二是故事简短紧凑,纯用作者的叙述和议论,不作细致的描绘,也没有直接的抒情。俄国寓言作家陀罗雪维支曾经说:“寓言是穿着外衣的真理。”真理犹如人体,作为外衣的故事必须合身。又因它旨在解剖和评判生活,所以并不需要对形象作细致描绘。
其三是作品紧紧抓住生活的特征,把它放大,进行艺术的夸张。生活中存在着压迫就有反抗的真理,作者就设计了一群受压迫的猴子,这些猴子有组织,会说话,能思考,甚至还会出谋划策,采取巧妙的报复行动。这是拟人的写法,艺术的夸张。但这样的夸张又完全符合现实人生的情理。
词上片是写离开苏州时饯别酒宴上的情景。“潇潇”两句:典出白居易《寄殷协律》诗:“吴娘暮雨潇潇曲,自别江南更不闻。”白居易自注:“江南吴二娘曲云:‘暮雨潇潇郎不归。’”白居易是感叹自从离开江南后,再也听不到吴娘婉转缠绵的歌声了。这首词变用其意。作者跳跃过“酒趁哀弦,灯照离席”的等待,跳跃过“执手相看泪眼”的留恋,把满腔悲苦都倾泻在对造成离别痛苦之原因的追究和检讨上。
词下片联语写罗、王交往关系,是这首小词的高潮,也是词中离别之悲的极致。昔人离别怨天怨命,怨雨怨风,而作者在这里却别出心裁,把离别的痛苦归罪于当初不该与对方建立了如此亲密的友谊。“既有今日,何必当初”两句乃是一种“反语”和“愤语”,是今日不得不轻易离别的悲痛竟导致了对当日相知相识之乐的否定。“忆平生”,其中自有深意,忆自己八年间,由于罗氏的赏识、扶持,才能在治学的道路上猛进。对罗氏的感激之情,只是含意未伸罢了。末句深化主题,由眼前别离之痛苦,升华至整个人生命运的慨叹。
这首小词完全是写离别之意,从一个离别的事件引向了《人间词》所追求的那种反映人生和反映哲理的层次。词中写梦醒之后的感觉,这往往有一种对人生的反省和了悟。
《驹支不屈于晋》在晋与诸侯“会于向”这一历史事件中,只不过是一段小插曲,然而它却有不同寻常的认识价值。这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上一段耐人寻味的故事。它不仅看到了当时少数民族在霸权制度下所受压迫的深重,也从驹支与范宣子的冲突与和解中看到了古代各民族既斗争又融合的复杂关系的缩影。通过个性化的语言表现人物性格是《驹支不屈于晋》的一大特点。
文章开头范宣子一上来就是:“来,姜戎氏!”像怒气冲冲的主人呼唤惹了祸的奴隶,凶神恶煞,怒目而视,语气咄咄逼人,态度粗鲁生硬。接着居高临下,夸示晋先君对诸戎的大德大恩,而后毫无根据地把“今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子者”的罪责一股脑推给驹支。“盖言语漏泄”,分明是推测、怀疑,“职女之由”,则是武断定罪,“与,将执女!”恐吓之声,令人不寒而栗!范宣子颐指气使、不可一世的神态纤毫毕见。
驹支面对气势汹汹的指斥,面对即将遭受拘捕的厄运,则临危不惧,据理力争。针对范宣子强加于己的不实之词,逐层辩驳,洗刷被泼在身上的污水,维护自己和部落的清白。从答话可以看出,驹支虽为戎族首领,但其语言艺术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他的语言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把握分寸,恰到好处。他对范宣子的无端指责,既针锋相对又没有过激言辞,既不掩惠公之德,也不蒙不白之冤。
其次是逻辑严密,形象生动。先感惠公之德,再表戎对晋之功,以事实为据,证明自己对晋“不侵不叛”,忠心“不贰”。最后以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的事实驳斥范宣子强加的罪名,环环相扣,天衣无缝。尤其是关于“捕鹿”的比喻,极为确切生动,且符合人物的身份。
最后是赋诗言志,颇具策略。《青蝇》所赋:“恺悌君子,无信谗言”,驹支将范宣子恶意相加的罪名解释为“听信谗言”,给了范宣子一个下台的台阶,把范宣子说成“恺悌君子”,也让这位盛气凌人的大人物感觉舒服。其实驹支似乎设了一个看不见的圈套:是“恺悌君子”就不要听信谗言,否则就不是“恺悌君子”。春秋时代,诸侯外交,讲究赋诗言志。范宣子没有赋诗言志,反不如驹支,说明驹支胜过范宣子,夷狄胜过华夏。这一点,恐怕不是《左传》作者的初衷吧。
《左传》除了对各国战争描述精彩之外,对一些谋臣说客的辞令艺术的记录,也极具艺术性,尤其是那些谋臣们在外交中实话实话,以真取胜的史实,令人叹为观止。《驹支不屈于晋》就是戎子驹支以事实说话,驳倒范宣子的责难的事:范宣子仗着晋国的强大,仗着自己的先君曾有恩于羌戎,对驹支气势汹汹,把晋国霸主地位的动摇归咎于驹支。戎子驹支则据理力争,逐层辩驳。首先说晋国所赏赐的土地是荒芜不毛之地,不足以称大恩大德。其次说羌戎帮助晋国在肴地全歼秦军,可以说已经报恩了,之后更是鞍前马后,毫无二心。最后暗示晋国所以众叛亲离,乃是其自己一手造成的,与羌戎无关。全部辩辞语气委婉而正气凛然,使范宣子不得不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