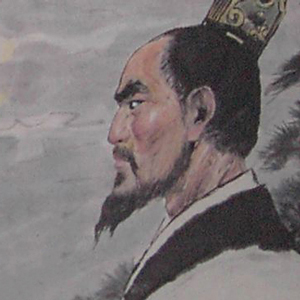译文及注释
译文
虽然我们都住在洛阳城,仅仅分在城东、城西,但每次分别都往往跨越季节。
当时离开的时候,漫天的雪花像盛开的白花;如今回来的时候,遍野的花朵像纷纷的白雪。
注释
昔:以前。
似:如同,犹如。
这首诗表达了对王、吴二人绘画艺术的观感及评价。
诗的发端四句,以错落的句法,点切诗题,交待王、吴二人画迹的所在,使人了然于普门、开元二寺俱有吴画,而王维的画则在开元寺的塔中。下面“吾观”二句,紧接着对二人的成就作概要的评断,肯定他们在画苑中并列的崇高地位。下面即分别描写二人的画象及是人所感受到的各自的艺术境界。
“道子实雄放”之下十句写吴道子画。“雄放”二字概括地道出吴画的艺术风格特点。“浩如海波翻”句以自然界的现象尽致地形容出雄放的气势。“当其”二句是诗人从画像中所感受到的吴道子运笔时的艺术气概。这种对吴道子创作过程的体会,也表达了诗人自己的艺术思想。后来诗人在其《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中曾说:“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么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即逝矣。”若能意在笔先,成竹在胸,才能“下手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这是艺术家的创作获得神妙境界的三昧所在,只有内具于自身,才能领会到他人获得这种成就的匠心所在。“亭亭双林间”以下六句写吴画的形象,极精要地勾勒出画的内容,生动地显现出释迦临终说法时听众的复杂情态,他们或感悟悲涕,或扪心自省,而那些“相排竞进”者的状貌,又表现得非常情急,这一切都栩栩如生。
“摩诘本诗老”以下十句写王维的画。“摩诘”从王维的身份提起,寓含王维画品的精神特质。即所谓“画中有诗”。“佩芷”句是对王维的人品和艺术的高度赞赏,即王维的人品和诗画艺术都是芳美的。“今观”二句照应前面“诗老”句,引用人所熟知的王维的诗的成就来喻其画风。“清且敦”意谓其画亦如其诗之形象清美而意味深厚。“祇园”以下六句写王维画的内容。前二句写画中人物情态,不似吴道子画表现的强烈,而意味颇蕴蓄。后四句写画中景物,为吴画所无,俨然是一幅竹画,再现了竹的茎叶动摇于清风中的神姿。纪昀说“交柯”句“七字妙契微茫”,王文诰说这四句即“公之画法”,这里面即寓有诗人画竹的艺法。这六句的画面,都具有“清且敦”的艺术风味。
诗末“吴生”六句,就对王、吴二人画的观感作总的评论,在尊重之中又对二人艺术造诣的境界,有所抑扬。对吴道子画评为“妙绝”,是对吴画中听众情态毕现形象的评价,而“妙绝”仅在迹象,只是画工的高艺。诗人认为王维画“得之于象外”,如神鸟离开樊笼,超脱于形迹之外,精神自然悠远,于是心中佩服,觉得无所不足。这里也体现了诗人美学理想的又一个方面。他在《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中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又说:“瘦竹如幽人,幽花如处女。”认为绘画不能但求形似,正如赋诗不能只停在所赋事物的表面,而要在形迹之外,使人在精神上得到启发,有所感受。瘦竹、幽花与幽人、处女,物类的质性迥异,而从瘦竹之感到幽人的韵致,从幽花如见处女的姿态,俱是摄取象外的精神,意味无穷。这种脱略形迹、追求象外意境的美学思想,长期支配中国文人画的创作,形成中国绘画艺术独具的风貌。
这首杂言诗以七言为主。七言古诗是盛唐诗人的一个胜场,李白、杜甫在这一诗体上是并峙的两座高峰。七古与五古同是在创作上极少拘束的,而七言长古更宜于纵情驰骋,在章法结构及气势节奏各方面更可变化无方,臻于奇妙之境。李、杜之后,中唐惟有韩愈能有不少佳作,再后就很寥落。苏轼的七言长古名篇迭出,成就之高,足与李、杜、韩相抗衡,这篇《王维吴道子画》即为其早年意气骏发之作。这首诗的章法很值得注意,整首诗的内容都在发挥诗题,而起结分合,条理清晰完密。诗的开始四句总提王维、吴道子,为全诗的纲领。“吾观”二句,又在分写王、吴画前先作总评。“道子实雄放”及“摩诘本诗老”两层,依次分写王、吴画面,为全诗的腹身。最后六句以评论收束,前四句分评吴、王,末二句于一致赞赏之余又稍有高低轻重,重申总评的精神。起和结的两节诗句于整齐中有参差,虽始终将王、吴二人并提,并极灵活而极错落之致。全诗章法如诗中所说:“交柯乱叶动无数,一一皆可寻其原。”
全诗的韵调具有优美的节奏感。开端四句闲闲而起,似话家常,语极从容。结尾六句,因评论而有所抑扬,语气于转折间呈矫健之势,而掉尾又觉余音袅袅,悠扬无尽。中间写吴道子一层,形象奇突,如峰峙涛涌,使人悚异;而写王维一层,景象清疏,如水流云在,使人意远。作为诗的中心的这两层,意象情调,迥然异趣。而全篇四节,波浪起伏,如曼音促节,递相转换,在大体上为七言句中适当间以五言,整体形成谐美的旋律,而气势仍自雄健。这是七言长古所必具的,也是不容易做到的。
此诗首联写月季花的季节特征;颔联重点描绘了月季花开放时的形态和色泽;颈联以桃李作比,透露出月季花的别有香味,以雪梅作比,又衬托着月季花的盎然英姿;尾联写诗人的独特感受,表露了诗人腊月前见月季的欣喜之情。全诗语言生动,新鲜活泼,且结构谨严,层层描绘,既有对月季花的精勾细摹,又有诗人的感情抒发,二者紧密结合起来,有较好的艺术效果。
此诗的标题是咏腊前月季,时候已是冬天,所以杨万里在诗里紧紧地抓住这两点来写。
首联“只道花无十日红,此花无日不春风。”很自然地入诗点题。第二句破题承起句“花无十日红”,本世人之常见,诗人加上“只道”二字,否定了世俗之见,出了新意,读来倍感新鲜。“无日不春风”是纲领,统领全诗诗人以满腔的热情,歌颂月季充满了青春的活力,生机勃勃,奋发有为。这二句概写,一句说百花,“花无十日红”,二句说月季,“无日不春风”。虽不是对月季的具体描绘,有些抽象,但并不难理解,且总领两句,已见月季特色。
颔联具体描绘。
“一尖已剥胭脂笔,四破犹包翡翠茸”,写月季花花蕾初绽的喜人情态。这句又同上句“无日不春风”相应。用胭脂笔”摹其含苞待放时的神情意志,一“剥”字表现月季绽开时顷刻间的动作,化静态的物象为动态美,又以“破”、“包”两词,状描花萼托蕊,傲然而开。见出诗人观察之细致,描写之逼真,堪称独步。
颈联写月季的浓香、风姿。
“别有香超桃李外,更同梅斗雪霜中”,“超”字与“斗”字仍是承首联中的“春”字,进一步刻画了月季的雪压霜欺花更艳的高尚气质。诗人在这里特别赞美了月季傲霜斗雪的可贵品格。不仅写了月季的香,而且写了月季的风姿。
尾联是写诗人的独特感受。
“折来喜作新年看,忘却今晨是季冬”。头句急转,提出新题,尾句作答即合,点明题旨,回应开头综观四时,月季“无日不春风”,即使在隆冬腊月,仍与梅花盛开雪圃“喜作”与“忘却”两词用得极妙,增添了诗句的活泼性,幽默性,诙谐性。
这首《腊前月季》,传为佳作。诗人为月季四季展浓艳,一年播芬芳,为人们生活增添乐趣的可贵品德所感,怀着深深的敬意,平平写来。对月季的爱悦,全部蕴含在浑融的诗歌意境中。玩索有味,体味有情。语言浅显,造境极佳,把月季写得神韵俱优。
这是一首小令,抒写的是作者游宴后邀朋乘舟晚归时的情景,是作者描写自然风光、表现闲适放逸生活情调的代表作。小令前五句写景,以浓墨重彩由远及近、由面及点、由实及虚地描绘了一幅色彩斑斓、境界恢宏的秋江晚霞图;最后两句是写人,通过作者与友人的对话表现其归隐生活的惬意。全曲语言通俗而不乏文采,笔调轻松而富于情韵。
首二句“铺水面辉辉晚霞,点船头细细芦花”,形象地写出了时间、地点。芦花在秋天开放,这是一个霞光明丽的秋天的傍晚。“水面”“船头”“芦花”三者组合在一起,表现了江南水乡的地方色彩。这二句字面没有写人,然而抒情主人公已在其中,他的目光由远而近,在船头停住,所以说:“铺水面辉辉晚霞,点船头细细芦花。”“辉辉”“细细”是仔细观察体会的结果,因为细,所以芦花下垂,所以会点着船头,他看得那么细,那么有味,可见其心绪之恬静悠逸。
次三句“缸中酒似绳,天外山如画,占秋江一片鸥沙”,再由近而远,描绘山水。这三句也没有写人,而又句句写人,——原来这位抒情主人公正坐在船中喝酒,所以有这时间、这心情去欣赏远近景物。“酒似渑”,极言酒之多,还够他慢慢喝的,他就由远及近、由近及远地观赏景物。他看了水面晚霞、船头芦花之后,便放目望去,远山隐约可见,在宽阔的江面上有一片栖息水鸥的沙渚。山水如此淡雅闲静,这是把抒情主人公的心态物化了。远近上下的景物全由“我”将其连缀组合成一个整体画面,并且是物“我”交融的。
最后二句“若问谁家是俺家,红树里柴门那搭”以自问自答作结。这“红树”“柴门”所在的地方,从抒情主人公的视线看,当是在鸥沙附近的秋江之畔,而且也只有这样画面才完整,色调浓淡相衬而又和谐,与首二句相应而圆合。真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至此才直写人物,自道府第,看来他也有点憋不住了,饶有趣味。
因陈铎作曲,化用前人的较多,故常被论家指斥,或谓其“曲多蹈袭(《曲苑·雨村曲话》),或说他“所为散套,既多抄袭,亦少才情”(何良俊《四友斋曲说》),而对他精通声韵协律合乐的制曲艺艺术却是一致公认的。即便批评他“多抄袭”的何良俊也不得不肯定他在声韵艺术方面的成就:“字句流丽,可入弦索。《三弄梅花》一阕,颇称作家。”(《四友斋曲说》)顾启元则更为概括地对此作了肯定:“陈铎为指挥,善词曲,又善谑。”(《客座曲话》)这二“善”当然仅是从制曲艺术而言的,并完全扣住了曲的特点和陈铎的独到之处。陈铎确实是善谑的,如上举诸曲,都具有程度不同的谑味,而在《滑稽余韵》集中更是比比皆是,真可谓竭尽揶揄调侃之能事。
总之,尽管陈铎有“蹈袭”之病,而作为讲究声韵必须合律的散曲艺术而言,人以“能手”“乐王”称之,适得其所,而广泛而又生动地反映明弘治正德间社会生活面貌的《滑稽余韵》集更属他人所无,前人都充分肯定了他所作出的贡献。汪廷讷曰:“曲虽小技乎,摹写人情,藻绘物采,实为有声之画……金元作者尚矣。于昭代,独北面陈大声氏。……其韵严,其响和,其节。词秀而易晰,音谐而易按。言言蒜酪,更复擅场,借使骚雅属耳,击节赏音。里人闻之,亦且心醉。”(《刻陈大声全集序》)曹学佺曰:“其所著有《梨云》《可雪》《月香》《纳锦郎》诸稿,而《滑稽余韵》……则又妙极俳谐,令人绝倒。大都流丽清圆,丰藻绵密,事尽而思不乏趣,言浅而情弥刺骨。”(《汪昌朝精订陈大声集序》)
《金菊对芙蓉》,这个词牌华美而清妍。题副是“上元”,由词题看是咏节序。此类诗词是比较难写的,南宋的张炎曾慨叹:“昔人咏节序,不唯不多,付之歌喉者,类是率俗。”后有刘永济在《词论》中言:“咏节序风物之作‘贵能直写我目、我心此时、此际所得。’”容若这篇则是以咏节为蓄,实乃怀人之想,予景于情,清朗自然,婉转流深,情深意切。
上元佳节,本是团圆欢聚的日子,这更让敏感多情的容若黯然神伤。容若思念着见阳,那个可以互诉衷肠把酒言欢的兄长知己,正身处战火纷飞之中。战地太过凶险,随时将有性命之忧,所以,他那细腻盛烈的心意中之深深牵念如何做的到独善其身呢?纵使再多书信,再多诗词,亦消融不了那一刻他心头凝结的悲凉愁绪。那,便是感人千古的义重如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