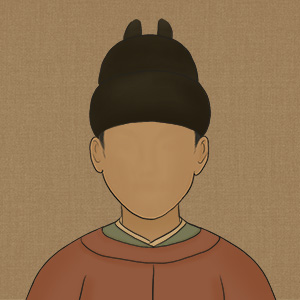杜甫的这首长篇叙事诗共有一百四十句,它像是用诗歌体裁来写的陈情表,是他这位在职的左拾遗向肃宗皇帝汇报他探亲路上及到家以后的见闻感想。它的结构自然而精当,笔调朴实而深沉,充满忧国忧民的情思,怀抱中兴国家的希望,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社会现实,表达了人民的情绪和愿望。
全诗分五大段,按照“北作”,即从朝廷所在的凤翔到杜甫家人所在的鄜州的历程,依次叙述了蒙恩放归探亲、辞别朝廷登程时的忧虑情怀;归途所见景象和引起的感慨;到家后与妻子儿女团聚的悲喜交集情景;在家中关切国家形势和提出如何借用回纥兵力的建议;最后回顾了朝廷在安禄山叛乱后的可喜变化和表达了他对国家前途的信心、对肃宗中兴的期望。这首诗像上表的奏章一样,写明年月日,谨称“臣甫”,恪守臣节,忠悃陈情,先说离职的不安,次叙作途的观感,再述家室的情形,更论国策的得失,而归结到歌功颂德。这一结构合乎礼数,尽其谏职,顺理成章,而见美刺。读者不难看到,诗人采用这样的陈情表的构思,是出于他“奉儒守官”的思想修养和“别裁伪体”的创作要求,更凝聚着他与国家、人民休戚与共的深厚感情。
“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痛心山河破碎,深忧民生涂炭,这是全诗反复咏叹的主题思想,也是诗人自我形象的主要特作。诗人深深懂得,当他在苍茫暮色中踏上归途时,国家正处危难,朝野都无闲暇,一个忠诚的谏官是不该离职的,与他的本心也是相违的。因而他忧虞不安,留恋恍惚。正由于满怀忧国忧民,他沿途穿过田野,翻越山冈,夜经战场,看见的是战争创伤和苦难现实,想到的是人生甘苦和身世浮沉,忧虑的是将帅失策和人民遭难。总之,满目疮痍,触处忧虞,遥望前途,作程艰难,他深切希望皇帝和朝廷了解这一切,汲取这教训。因此,回到家里,他虽然获得家室团聚的欢乐,却更体会到一个封建士大夫在战乱年代的辛酸苦涩,不能忘怀被叛军拘留长安的日子,而心里仍关切国家大事,考虑政策得失,急于为君拾遗。可见贯穿全诗的主题思想便是忧虑国家前途、人民生活,而体现出来的诗人形象主要是这样一位忠心耿耿、忧国忧民的封建士大夫。
“缅思桃源内,益叹身世拙。”诗人遥想桃源中人避乱世外,深叹自己身世遭遇艰难。这是全诗伴随着忧国忧民主题思想而交织起伏的个人感慨,也是诗人自我形象的重要特作。肃宗皇帝放他回家探亲,其实是厌弃他,冷落他。这是诗人心中有数的,但他无奈,有所怨望,而只能感慨。他痛心而苦涩地叙述、议论、描写这次皇恩放回的格外优遇:在国家危难、人民伤亡的时刻,他竟能有闲专程探亲,有兴观赏秋色,有幸全家团聚。这一切都违反他爱国的志节和爱民的情操,使他哭笑不得,尴尬难堪。因而在看到山间丛生的野果时,他不禁感慨天赐雨露相同,而果实苦甜各别;人生于世一样,而安危遭遇迥异;他自己却偏要选择艰难道路,自甘其苦。所以回到家中,诗人看到妻子儿女穷困的生活,饥瘦的身容,体会到老妻和爱子对他的体贴,天真幼女在父前的娇痴,回想到他自己舍家赴难以来的种种遭遇,不由得把一腔辛酸化为生聚的欣慰。这里,诗人的另一种处境和性格,一个艰难度日、爱怜家小的平民当家人的形象,便生动地显现出来。
“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坚信大唐国家的基础坚实,期望唐肃宗能够中兴。这是贯穿全诗的思想信念和衷心愿望,也是诗人的政治立场和出发点。因此他虽然正视国家战乱、人民伤亡的苦难现实,虽然受到厌弃冷落的待遇,虽然一家老小过着饥寒的生活,但是他并不因此而灰心失望,更不逃避现实,而是坚持大义,顾全大局。他受到形势好转的鼓舞,积极考虑决策的得失,并且语重心长地回顾了事变以后的历史发展,强调指出事变使奸佞荡析,热情赞美忠臣除奸的功绩,表达了人民爱国的意愿,歌颂了唐太宗奠定的国家基业,从而表明了对唐肃宗中兴国家的殷切期望。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诗人的社会理想不过是恢复唐太宗的业绩,对唐玄宗有所美化,对唐肃宗有所不言,然而应当承认,诗人的爱国主义思想情操是达到时代的高度、站在时代的前列的。
综上可见,这首长篇叙事诗,实则是政治抒情诗,是一位忠心耿耿、忧国忧民的封建士大夫履职的陈情,是一位艰难度日、爱怜家小的平民当家人忧生的感慨,是一位坚持大义、顾全大局的爱国志士仁人述怀的长歌。从艺术上说,它既要通过叙事来抒情达志,又要明确表达思想倾向,因而主要用赋的方法来写,是自然而恰当的。它也确像一篇陈情表,慷慨陈辞,长歌浩叹,然而谨严写实,指点有据。从开头到结尾,对所见所闻,一一道来,指事议论,即景抒情,充分发挥了赋的长处,具体表达了陈情表的内容。但是为了更形象地表达思想感情,也由于有的思想感情不宜直接道破,诗中又灵活地运用了各种比兴方法,即使叙事具有形象,意味深长,不致枯燥;又使语言精炼,结构紧密,避免行文拖沓。例如诗人登上山冈,描写了战士饮马的泉眼,鄜州郊野山水地形势态,以及那突如其来的“猛虎”、“苍崖”,含有感慨和寄托,读者自可意会。又如诗人用观察天象方式概括当时平叛形势,实际上也是一种比兴。天色好转,妖气消散,豁然开朗,是指叛军失败;而阴风飘来则暗示了诗人对回纥军的态度。诸如此类,倘使都用直陈,势必繁复而无诗味,那便和章表没有区别了。因而诗人采用以赋为主、有比有兴的方法,恰可适应于表现这首诗所包括的宏大的历史内容,也显示出诗人在诗歌艺术上的高度才能和浑熟技巧,足以得心应手、运用自如地用诗歌体裁来写出这样一篇“博大精深、沉郁顿挫”的陈情表。
这是一首写歌女弹筝的词,或有所寄托,或纯写眼中所见之人,耳中所闻之曲,不必深究。
开篇先点出乐曲的格调,首先,用的是筝,而筝声向来苍凉柔婉,适合表现哀怨、哀愁的情绪,而歌女所弹奏的也正是类似湘江故事的哀伤曲调。乐曲本是要靠耳听,而无法目见的,但词人却突然从听觉转向视觉,说“声声写尽湘波绿”。这种修辞手法叫作“通感”,也称“移觉”,即将不同感官所感受到的诸如听觉、视觉、触觉、嗅觉等感触沟通起来。因为文字最方便描写的是视觉,而对于听觉则相对难以描摹,所以用视觉来比拟听觉——澄碧的湘流。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说,确实易使人产生哀愁的情感.于是便以通感的手法来比喻筝曲。
上阕后两句点明了通感所表述的含义,并点出弹筝人的身份——女子,在以筝弹奏“幽恨”之曲。
下阕开篇也是视觉,重点从筝曲转换到弹筝之人,在宴会席间,沉静地弹筝,“秋水”也即澄澈的目光缓缓流转,表明弹筝的女子完全把整个身心都融合到所弹奏的筝曲中去了。而赏其弹奏者眼中所见既有澄澈目光,也有斜行的筝柱,也将筝和人合为一体,仿佛这乐声不是从筝上弹出,而是从弹筝女子心中涌出一般。正因如此,才能在筝声弹奏到最凄婉断肠的那一刻,女子缓缓垂下双眉,表情与乐声浑然一体,吐尽了胸中的哀伤和怨恨。
全词语辞清美婉丽,情感真挚凄哀,风格含蓄深沉,令人可观可叹。
第一首从回顾楚国兴起和发展的历史着笔,与其衰落败亡的结局以及今日遗址荒芜的景象,作强烈的对比。“远接商周祚最长,北盟齐晋势争强。”是说楚国远承商周二代的王业,国统由来久长,在发展鼎盛时期,曾和齐晋结盟,对抗强秦。楚原是商的属国,后至周,又被周成王正式封为诸侯国。因此可以说“是远接商周祚最长”了。“祚”,指王统。
第二联顺接上联意,写楚国最终由盛而衰,以至为秦所灭。“章华歌舞终萧瑟”,写的便是这种历史的结局。“章华”,即章华台,楚国离宫,旧址有几处,此当指沙市之豫章台。当年章华台上的歌舞,早已萧索寂寥了,但是,“云势风烟旧莽苍”:楚地著名的云势泽,气象依旧,风烟迷蒙,阔大苍茫。这里,诗人以章华歌舞之短暂映照云势风烟之永恒,产生强烈对比,抒发物是人非之感叹,揭示出历史发展之无情。
第三联由历史的回顾转为对眼前景象的描写:“草合故宫惟雁起,盗穿荒冢有狐藏。”当年郢都宫殿旧址,如今已野草滋蔓,唯见雁群时时飞起;早已被盗掘的荒坟野冢,如今成了狐兔藏身之所。这景象是多么凄凉败落,它既是诗人眼前所见之景,又是当年楚国衰亡的象征。而导致楚国衰亡的原因,正是屈原在《离骚》中所尖锐指出的,贵族蒙蔽君王,嫉贤还能,朋比为奸惑乱国政。这一历史的教训,使得千秋仁人志士莫不感到感慨万分,热泪沾裳。末联“离骚未尽灵均恨,志士千秋泪满裳。”是诗人对楚之衰亡所作的结论,也是全诗主旨之所在。“灵均”是屈原的字,“灵均恨”,既是屈原在《离骚》中所无法尽情宣泄的家国无穷之恨,也是陆游在这首诗中所要表达的与屈原共命之叹。
第一首以议论起笔,以抒情落笔,中间两联写景,情寓于景。第二首则首尾写景,中间抒情,情因景而发。第一联:“荆州十月早梅春,徂岁真同下阪轮。”“荆州”,即指郢都;“徂岁”,犹言过去的岁月;“下阪轮”,即下坡的车轮,这里用以形容流光迅速。此联是说荆州十月便是早梅初开的小阳春气候了,时光的流逝的感慨,这是一个胸怀大志、迫切要求报国效命的志士的感慨,是在对自然界客观规律的认识中包含着对人事代谢现象的探寻。第二联由对屈原的怀想而抒发对古往今来仁人志士壮志难酬的愤慨,这是伤古,又是悼今。“天地何心穷壮士?江湖自古著羁臣。”写得极为沉重。是啊,天行有常,何曾有导致壮士途穷困厄之心;自古以来,皆因人事之非,以致多少像屈原这样的贞臣节士去国离乡,放逐江湖。这一切怎不令人顿生怨愤,非淋漓痛饮焉能排遣,非慷慨悲歌何以发泄。诗的第三联“淋漓痛饮长亭暮,慷慨悲歌白发新。”正是表达这样一种感情。但是,诗人心中那报国无门的怨愤和苦闷是无法解脱的,所以“淋漓痛饮”于长亭薄暮之中,更显孤独;“慷慨悲歌”于白发初生之际,自增惆怅。这种心情只有泽畔行吟的屈原可以与之相通,美人迟暮悲今古,一瓣心香吊屈平。但眼前却是“欲吊章华无处问,废城霜露湿荆榛。”末联勾画出的这种荆榛满地、霜露侵入的惨淡景象,深深地印在诗人的心上,也引起读者的沉思。
陆游的优秀诗篇大都回荡着爱国激情。在这组诗中,诗人的一纸诗情,又是通过郢都古今盛衰的强烈对比来表现的,并且借屈原的千古遗恨来抒发自己的爱国之情。杨万里说陆游诗“尽拾灵均怨句新”(《跋陆务观剑诗稿》),正可概括这首诗的特色,读后,确如朱熹所云:“令人三叹不能自已。”(《答徐载叔赓》)公元年1178(淳熙五年)五月,陆游又写了《楚城》:“江上荒城猿鸟悲,隔江便是屈原祠。一千五百年间事,只有滩声似旧时。”皆抒发同一感慨。
据阮阅《诗话总龟》等书记载:“南唐卢绛病痁,梦白衣美女歌曰:‘玉京人去秋萧索’云云。”从此这首小词蒙上一层迷离恍惚的神秘色彩,被看作“鬼词”。其实,这只是一首倾诉闺情的篇章,它以笔致工巧,深婉动人,赢得了人们的喜爱,曾在北宋初年广为流传。从词中可知,抒情主人公是一位温柔多情、敏感娴静的女子。
“玉京人去秋萧索,画檐鹊起梧桐落。”在这萧索的秋天,心上的人儿远去京城,庭院画檐下喜鹊飞起,梧桐纷纷飘落。
玉京,本道教所谓天上宫阙,用作京城的代称。在一个秋日的黄昏,她凭栏凝视,沉浸在对远方亲人的怀念之中。起首两句描绘出一幅飒飒秋景,景中有情。前一句点出秋气而“人去”之意,是情与景双双写入之法。“萧索”二字是一篇眼目,后一句就此点染。喜鹊历来是吉祥之鸟,鹊起而不顾,暗示丈夫一去杳无音信,闺中的主人公怅然失望也已隐然可见,细微如梧桐落叶之声清晰可闻,庭院之阒寂,女子怀想之深也可以想见了。“人去”,令人记起往昔未去之时;“萧索”,烘衬出抒情者的悲凉意绪,连带说出便觉情景相生,这正是双入法的妙处,由此开篇,全词都笼罩着瑟瑟寒意了。基调也由此确定。
“攲枕悄无言,月和清梦圆。”这两句是说,倚靠着枕儿默然远想,月儿和梦境都是那么的圆美。
接下来时间由黄昏而入夜。如果说前面两句侧重渲染气氛的话,那么这两句着重刻画人物的动作。中心落在思念二字上。夜不安寐,倚枕无言,用动作表现心理,形象而又委曲。“无言”是静默之状,又含“脉脉此情谁诉”之意。唯其默然远想,才引出下一句的清梦来。不知过了多久,这位辗转反侧的女子渐渐进入梦乡。梦中见到了她久别的亲人。词人把这梦中团聚和中天月圆巧妙的交织在一句之中,“圆”字双关。梦境沐浴着月的清辉,而一轮圆月又在梦的幻影之中,境界惝恍迷离,清幽怡人。梦境与现实,月色与人事两相对照反衬,使主人公的情怀表现得愈婉愈深了。
“背灯唯暗泣,甚处砧声急。”这两句是倒装句,说,不知什么地方响起阵阵捣衣声,把她从睡梦中惊醒,眼前的冷寂,益发加深了感伤和怅惘,她怎能不柔肠寸断,哀泣不止呢?
“甚处”,说明砧声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是一种并不太响,而且时断时续的声音,也符合乍醒来时恍惚莫辨的情态。这种声响竟把人惊醒,可知夜之静谧了。这样看来,句中极醒目的“急”字恐怕侧重于表现人的内心感受,未必是实写砧声。“背灯暗泣”乃梦断神伤之状。“暗”字兼言情、景,思妇心境之黯然具体可感。从上文的“攲枕悄无言”到此刻的“背灯暗泣”,层层叠进,愈转愈悲了。
“眉黛远山攒,芭蕉生暮寒。”结末两句是说,室内女子黛色如远山的眉头紧攒,室外圆月清辉之下芭蕉也觉瑟瑟寒意。
给那攒蹙的秀眉一个特写镜头,把满怀的思念和哀怨全部凝聚在黛色如远山的眉间了。末句轻轻宕开,以景收束:“芭蕉生暮寒”。凄冷之意有真切,又朦胧,那寒气直沁入人的心里,却又不曾说破。词婉而情切,令人哀感无端,正是所谓已经结情的妙笔。
这首词在结构上,一句景,一句情,间或情景双写。在情与景的相映、相生、相融之中,女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婉曲而深切的袒露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