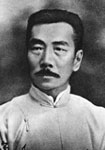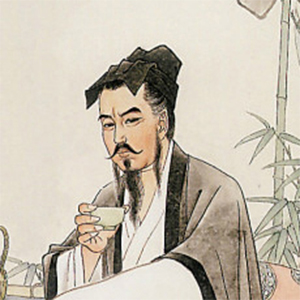这首诗的前两句“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坚实有力,具有不可辩驳的力量,是流传较广的名句。作者没有多用笔墨去铺叙事情的原委,一开始就用哲理性的诗句,雄辩地提出那种“无情”之辈未必是真正的豪杰,而“怜子”者倒完全可以是大丈夫。诗句有力地回击了那些抽象地玩弄“有情”、“无情”的论客,严正指出,以“无情”自嘘的人并不就是英雄,用攻击别人的“怜子”,以显示自己的“无情”更是卑鄙可笑。在鲁迅看来,是否英雄,不在于它是否怜子,而在于他对敌人是否无情。诗句,先用一个“未必”,否定了“无情”论者,又用一个“如何”,诘问攻击“怜子”者,使之无言以对。这两句诗,是对仗的写法,但不是情对,也不是景对,而是理对。它的哲理性很强。气势也很壮。鲁迅在当时的众矢飞射之下,理直气壮地热爱其子,并把这种感情泛而至于广大人民,并不失为丈夫本色,而那些标榜“无情”的人却跟豪杰一点也不沾边。诗人痛斥“无情”论者,没有回避“怜子”,相反地正以“怜子”来证明攻击者的卑鄙,这就完全取得了主动的地位。这两句诗语意深刻,对仗天成,有否定,有肯定,有判断,有诘问,毫不费力,轻而易举,使得讥讽者自讨没趣,本相毕露。
后两句“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把“怜于如何不丈夫”的句意,扩展开来,在生动的比喻中给攻击者以嘲笑和挖苦;把老虎虽猛也要怜子之意充分表现出来。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曾记述说:“海婴性格活泼,鲁迅曾对我说:这小孩非常淘气,有时弄得我头昏。他竟问我:爸爸可不可以吃的?我答:要吃也可以,自然是不吃的好。我听了一笑,说他正在幻想大盛的时期,而本性又是带神经质的。鲁迅颇首肯。后来他《答客诮》一诗,完全写出了这种爱怜的情绪。”
这首诗,作者鲁迅分别通过否定句、反问句、疑问句,完成了诗的“起”、“承”、“转”;诗的首句“无情未必真豪杰”采用了否定句,这在诗歌创作中并不常见,但直白易懂,起到了开宗明义的作用;第二句“怜子如何不丈夫”承接第一句,通过反问句式,在意思上更进一层,把“丈夫”与“怜子”联系起来。全诗的题旨更加具体显豁,范围由一般意义的“豪杰”缩小到有孩子的“丈夫”们;第三句干脆不再讲究委婉与周严,直接用“知否”打头,发出无可辩驳的质问——“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推出了最有说服力的证据,语气也更加坚定。“未必”、“如何不”、“知否”都有否定语,却使立论步步深入,也使感情越来越强烈,为最后一句的“合”做了充分的铺垫。
该文是王安石阐述自己文论观点的信。信虽主要针对书、序、原、说一类理论文的作意而言,但从中也可窥见王安石基本的文学观点。在对文章本质的认识上,王安石是个“政教论”者。
他开门见山,提出要义:“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即认为文章的实质应是反映礼教政治,并为它们服务。在《与祖择之书》中,他也重复过这个意思:“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圣人之于道也、盖心得之,作而为治教政令也”,“书诸策而传之人。”王安石认为,当初文章产生,就是因为古代圣贤对于治理世事有了个人的见解,于是写下来,传示当代及后人,这就是文章了。所以文章实际上就是礼教政治。以此为前提,该文集中阐释了“作文之本意”,即写文章到底为了什么。作者指出,作文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有补于世”,“适于实用”。从这个根本点出发,王安石重点讨论了文和辞的关系,即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文章的内容和形式应该是统一的,但二者又有主次之分。韩愈、柳宗元是作文章的行家里手,成就很高,可惜他们没有重视作文的目的,只告诉人们一些作文的形式技巧。孟子在《离娄下》中所说的一段话却不只是告诉人们如何作文章,还可借以比喻写文章的终极目的。孟子的本义是说,君子探求学问,目的在于自己要有真正的心得,有了自己的心得,就能专心研究下去;专心研究,就会掌握住深厚的道理;掌握的道理多了,运用起来就能左右逢源、头头是道。写文章也是如此,首先要有明确的实用目的,目的明确,你就会认真思考,获得自己的见解;见解深刻,内容充实,写起来就能得心应手,驱遣自然。所以写文章,目的、内容是根本。他拿器物作比,说明文章“以适用为本”的道理。以为言辞形式之美有如器物的外饰,虽不可完全废止,但总不能摆在首位。一件器物只要适用,不一定非要华丽巧妙不可,而不适于实用者,装饰再华巧,也失去了它作为器物的本来意义。
在北宋,对于“道”与“文”的关系,争论非常激烈,不少人执论偏颇,王安石认为“彼陋者”,“非流焉则泥,非过焉则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当后者反先之,无一焉不悖于极。”(《与祖择之书》)有的人虽夸谈“文以明道”,而其真心却只重文不重道。所以他特别指出在强调“作文之本意”方面,韩、柳也还作得不够。同时,他也看到了道学家矫枉过正,重道轻文的弊病,因此也不完全否认“巧且华”的修饰作用。于是,他明确提出自己的主张:“容亦未可少也,勿先之”,即要求把文章的思想内容放在首位,而表现形式放在其次。如果读者对此不作机械的理解,二者位置的摆法无疑是正确的。然而,王安石所讲的思想内容,仅仅指礼教政治,这种认识就过于拘狭。但是,在那个历史时期,王安石能从文章的社会功用出发探讨其内容和形式的相互关系,提出这样独到而较为深刻的见解,是非常可贵的。
从王安石的写作实践看,他确是“挟此说以自治”的,即如此文,所论虽关宏旨,说理却透辟而简洁,毫无巧饰刻画之痕。起手即明确道出自己对“文”的基本看法,语气斩钉截铁,显得理足气盛。紧接着一言论定孔子“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的本意并非倚重修辞,这就否定了某些人片面强调文饰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据。关于圣人作文的本意,作者引用孟子之言作了回答,指出作文必须“以适用为本”,以思想内容为主,并用比喻对此展开了充分而生动的论说。信从作文之本意提起,而最后落脚在如何处理“文”、“辞”关系上,几经推演,但却中心突出,观点鲜明,作者的思路表达得很清楚。文笔既简练劲峭,又不失华采生动,语言极富表现力。
由于王安石从礼教政治出发,过于强调实用精神,使得他的文学观念带上了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人们又往往把仅适用于理论文章的“适用为本”的观点赋予普遍的意义,推广于一切文学,等而下之,其末流就将文学和政治宣传等同了起来,轻视乃至否定了文学的审美价值和愉悦作用。这也许是王安石始料所不及的。
全诗紧扣“游”字,描写夏日暮晚时分的独特山景,表达了诗人热爱自然之情,抒发了追求闲适、高洁之志,也表达了诗人想摆脱官场束缚意欲退隐的心情。
这首诗首联点明题旨,总写月夜下游山。夕阳西沉,作者和夏少府利用公余之暇,到山间寻幽探幽。颔联写山里山路、花木的幽香,颈联写山中的寂静幽深,二、三联写景,描写十分细腻,对仗特别工致。落日的余晖仿佛是点点滴滴的黄金,玉佩散落在幽暗的兰径、槐庭之中,空山静谷,寂寞无声,只有深深的月色伴随着阵阵山径;前三联描绘游山所见所闻,“兰径”、“槐庭、“静谷”、“空山",加上“幽佩”、“暗金"、“径声”“月色”,组成了一幅傍晚山中纯静、空明、幽雅、清丽的图画。
面对这样悦人的山色,诗人于尾联卒章显志,情不自禁地抒发了挣脱樊笼,寄迹山林的情怀,显得贴切自然。“樊笼累”(陶渊明“久在樊笼里”)表明对官场、俗世的厌倦,“松桂心”(陶渊明“复得返自然”)表明对自然的喜好,对归隐生活的向往,揭示了“诗心”,主旨凸显。
由此,全诗在营造山中夜色空旷、幽静的奇特意境中,含蓄地表达了诗人远离“樊笼”(尘世束缚)、亲近“松桂”(美好自然)的心愿,其厌恶尘世、热爱自然、追求高洁之情志,了了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