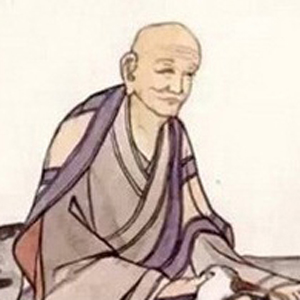此诗中“数骑”和“敢”字都是经过锻炼的字眼。只用三个字就表现了安禄山叛军的强壮和官军的怯弱。“青是烽烟白人骨”这一句,本来应该说“青是烽烟,白是人骨”。缩成七言句只好省略一个“是”字。《同谷歌》有一句“前飞鴐鹅后鹙鶬”,本来是“前飞鴐鹅,后飞鹙鶬”。省略了一个“飞”字。又《李潮八分小篆歌》有一句“秦有李斯汉蔡邕”,省略了一个“有”字。这种句法,仅见于七言古诗,五言诗中绝对不可能有。七言律诗中也少见。“青是烽烟白人骨”止是一个描写句,“白人骨”还属于夸张手法。阵亡士兵的尸体暴露在荒野里,至少要几个月才剩一堆白骨。杜甫此句,只表现“尸横遍野”的情景。他有一首《释闷》诗,其中有一联道:“豺狼塞路人断绝,烽火照夜尸纵横。”也是写战后的原野,它和“青是烽烟白人骨”是同一意境的两种写法。
此诗第二联写安禄山部队的强悍,第三联是其后果,所以写官军死亡之惨。而在叙述同一事件的另一首诗《悲陈陶》里,第二联写官军士气怯弱,无战斗力;第三联是其后果,所以写“群胡”的飞扬跋扈。可见杜甫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描写同一事件的艺术手法。第四联是写被困在长安城内的人民和作者自己的思想感情。陈陶斜一败之后,长安城中的人民在痛哭之馀,还希望官军马上再来反攻。可是在青坂再败之后,人民知道敌我兵力相差甚远,只得放弃“日夜更望官军至”的念头。杜甫在长安城中,听到唐军战败的消息,心中非常焦急。而只好设想托人带信给官军,希望他们好好整顿兵力,待明年再来反攻。这两首诗的结尾句深刻地表现了人民对一再成败的官军的思想感情的合于逻辑的转变。
《杜诗镜铨》引用了邵子湘的评语云:“日夜更望官军至,人情如此;忍待明年莫仓卒,军机如此。此杜之所以为诗史也。”这个评语,反映出邵子湘认为两个结句有矛盾,因此他把《悲陈陶》的结句说是人民的感情如此;把《悲青坂》的结句说是军事形势有这样的需要。他以为这样讲可以解释矛盾。其实是似是而非。要知道,“军机如此”,也同样是长安城中人民听到青坂之败以后的认识和感情。杜甫写的正是人民思想感情的转变,根本不能以为两首诗的结句有矛盾。
这是诗人访友不遇之作。全诗描写了隐士闲适清静的生活情趣。诗人选取一些平常而又典型的事物,如种养桑麻菊花,邀游山林等,刻画了一位生活悠闲的隐士形象。全诗有乘兴而来,兴尽而返的情趣,语言朴实自然,不加雕饰,流畅潇洒。
“移家虽带郭,野径入桑麻。”是说陆羽把家迁徙到了城郭一带,乡间的小路通向桑麻的地方。陆羽的新居离城不远,但已很幽静,沿着野外小径,直走到桑麻丛中才能见到。开始两句,颇有晋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而种车马喧”的隐士风格。
“近种篱边菊,秋来未著花。”点出诗人造访的时间是在清爽的秋天,自然平淡。陆羽住宅外的菊花,大概是迁来以后刚刚才种上的,所以虽然到了秋天,还未曾开花。这两句一为转折,一为承接;用陶诗之典,一为正用,一为反用,却都表现了环境的幽僻。至此,一个超尘绝俗的隐士形象已如在眼前,而诗人访友的兴致亦侧面点出。
“扣门种犬吠,欲去问西家。”说诗人又去敲陆羽的门,不但种人应答,连狗吠的声音都没有。此时的诗人也许有些茫然,立刻就回转去,似有些眷恋不舍,还是问一问西边的邻居吧。一般说来,写到“扣门种犬吠”,“不遇”之意已见,再加生发,易成蛇足。就像柳宗元的《渔翁》一诗:“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崖上种心云相逐。”前人每谓末二句“着相”,情思刻露,如苏轼、严羽、胡应麟、王士祯、沈德潜等都持是说。但皎然之写问讯于西家却正得其所。一方面,见出对陆羽的思慕,表明相访不遇之惆怅;另一方面,则借西家之口,衬托出陆羽高蹈尘外的形象,表明二人相契之根由。同时对诗中所描写的对象即陆羽,并未给予任何直接的刻画,但其品格却呼之欲出,这也正符合禅宗“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之旨。
“报道山中去,归时每日斜。”是邻人的回答:陆羽往山中去了,经常要到太阳西下的时候才回来。这两句和贾岛的《寻隐者不遇》的后两句“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恰为同趣。“每日斜”的“每”字,活脱脱地勾画出西邻说话时,对陆羽整天流连山水而迷惑不解和怪异的神态,这就从侧面烘托出陆羽不以尘事为念的高人逸士的襟怀和风度。
这首诗前半写陆羽隐居之地的景;后半写不遇的情况,似都不在陆羽身上着笔,而最终还是为了咏人。偏僻的住处,篱边未开的菊花,种犬吠的门户,西邻对陆羽行踪的叙述,都刻画出陆羽生性疏放不俗。全诗四十字,语言清空如话,不加雕饰,吐属自然,流畅潇洒,别有隽味。
东晋孝武帝太元八年(383年),北方的前秦苻坚率领百万大军南下,气焰嚣张,妄图消灭东晋,统一南北。东晋只有八万军队,不到苻坚的十分之一。而淝水一战,晋师大败苻坚,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保住了晋国的安全,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淝水之战。这对南宋有重大的历史借鉴意义。
上片首先在读者面前展开了一幅长江形势图,眼前只看到长江雪浪,滚滚滔滔,千里奔腾,一泻而下,阻隔南北。据传三国时魏国的曹丕在观望长江时,曾感叹地说:“此天之所以限南北也。”他两次伐吴,都未成功,长江阻隔,是其重要原因。如此天险,北方的金兵是难以逾越的。高宗如果稍有恢复中原之志,就应利用天险,加强设防,固守长江,以遏强虏。当然,天险难逾,并不等于绝对不可逾。三国时东吴孙皓,仅凭天险御敌,终于招致“一片降幡出石头”。所以李纲强调天险难逾,还必须加上“人谋克壮”,天险可凭,而又不可仅凭天险,重在人谋。有天险可凭,又加上人的深谋远略,北方索虏,岂敢吞噬我们的土地?索虏是南北朝时南方人对北方敌人的蔑称。这里既是指前秦,也是指金兵。这段描写兼论述为下文写晋师以少胜多提供了依据。下文很自然地转入到对淝水之战的记述。
苻坚率百万之众“倏忽长驱吾地”。倏忽,言其神速;长驱,言其势猛。这句极言秦兵强大,乃为后面秦兵失败作反衬。欲抑先扬,以突出晋军胜利其意义重大。
当苻坚南侵,大敌当前之时,谢安作为东晋宰相,其主要作用有二:一是决定大政方针:坚决抵抗,决不妥协;二是运筹帷幄,用人得当。他以谢石为征虏将军、征讨大都督,统率全军。以谢玄为前锋都督。还有辅国将军谢琰,西中郎将桓伊,龙骧将军胡彬等,协同作战。谢安深信他们的谋略将才,放手让他们发挥主动作用,自己不插手,不直接干预军事,指挥若定,镇静自如。《通鉴》载:“谢安得驿书,知秦军已败。时方与客围棋。摄书置床上,了无喜色,围棋如故。客问之,徐答曰:‘小儿辈遂已破贼’。”可见他胸有成竹,料事如神。故词中称赞:“破强敌,在谢公处画,从容颐指。”“颐指”,即指挥如意。
晋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确为历史奇迹,故换头以“奇伟”领起,对这次战争的胜利作了生动的铺叙。谢玄等以“八千戈甲,结阵当蛇豕。”戈甲,代指军队;蛇豕,封豕长蛇之简称。《左传·定公四年》:“吴为封(大)豕长蛇,以荐食上国。”封豕长蛇,比喻强大的贪暴残害者。此借指苻坚。“鞭弭周旋,旌旗麾动”,弭,弓之末梢,用骨质制成,用以助驾车者解开辔结。谢玄、谢琰、桓伊等指挥数千之众,直渡淝水,击退北军,使北军望风披靡。苻坚等登上寿阳城,望八公山上草木,皆以为晋军。在败逃路上,夜闻风声鹤唳,皆以为晋军追杀过来。弃甲曳兵,亡魂丧胆,惊慌失措,狼狈北逃。词以十分快意的笔调赞扬晋军出奇制胜、力挫强敌,保住了东晋的江山和人民,免遭“索虏”吞噬。其功业之伟大,虽“周雅”所歌颂的周宣王中兴也不得专美于前了。《诗·小雅》中的《六月》、《采芑》等诗记述周宣王任周尹吉甫、方叔等率军北伐 狁,南惩荆蛮,使西周得以中兴。淝水之捷,其功不亚于此。
全词从长江天险写起,指出既凭天险,又重人谋,何惧“索虏”!接着以主要篇幅描述了淝水之战晋胜秦败的过程及其值得借鉴的历史意义:强大的敌人并不可怕,是可以被打败的。只要弱小的一方敢于斗争,人谋克壮。词还突出了东晋宰相谢安“从容颐指”的作用。曾担任高宗宰相的李纲多么希望自己能起类似谢安那样的作用,可惜他没会机会。他写这首词,意在讽谕高宗以古为鉴,须知少可以胜多,弱可以胜强,强敌不足畏,全在“人谋克壮”。应痛下决心,北伐中原,收复失地,作者的用心是很明显的。
此词借写景以抒春愁,词之上片写离情相思,下片写久别盼归。
“梦怕愁时断,春从醉里回。”以对句起,点出“愁”字,开门见山,直抒愁怀。“梦”和“醉”二字,则说明这位愁人借以消愁解闷、自我麻醉的方法唯此二者。他害怕梦醒愁也醒,于是“终日昏昏醉梦间”,企图以此逃避愁闷的袭来;然而春天却从沉醉中悄悄地回来了。面对阳春烟景,他却发出酸楚的自问:“凄凉怀抱向谁开?”他感到满怀的凄凉况味,一时既诉说不尽,更找不到可以诉说的人。杜甫《奉待严大夫》诗:“身老时危思会面,一生襟抱向谁开?”虽然所指不同,但可以对之倾诉怀抱的人,一定是了解自己、关心自己的人。凄凉怀抱,无可告语,可见知心人不在身边,因而感到格外孤寂难堪。这一句暗示愁闷难解的原因在于怀人,则梦断酒醒的惆怅也自然可以理解了。这三句已定下全词的抒情基调,于是在词人眼中所见的“春景”,无不染上这种“凄凉”的色调。“些子清明时候被莺催。”清明前后,正是春光大好,踏青游春之时,词人却意兴萧索,无心赏玩春光。“些子清明时候”,在词人的感觉上,清明前后这春光的黄金季节,竟是如此短暂,匆匆即过。少许春光,并不曾给愁人带来丝毫欢乐;相反,在他听来,枝头的百啭黄莺,不是在为春天欢唱,却是唱着催春速去的挽歌。这两句把莺花三月,化作短暂的心理时间,染上凄凉的感情色彩;春天从醉梦里悄悄而来,又在莺声中匆匆而去,外在的春景如梦幻泡影。春去春来,愁情依旧。
如果说上片是词人直抒胸臆的痛苦告语,下片则推出了一组令人黯然销魂的景物镜头。词人隐身在景物之后,让这些无言的镜头说出他的心声。“柳外都成絮,栏边半是苔。”柳絮纷飞,意味着春将归去,很自然地令人想到上片结处“被莺催”的那个“催”字,意脉的过渡毫不着力。栏杆边的苔痕,则说明长久无人凭栏眺景了。春天对于愁人来说,似乎是可有可无的。然而有一件东西却深深地触动了词人:“多情帘燕独徘徊,依旧满身花雨又归来。”“多情”二字,含着热泪脱口呼出,有如见故人之感。燕子还记得当年帘幕中的欢乐情景,当它再度飞来时,却感到境地凄凉。气氛顿异,不禁迟疑起来。“独徘徊”三字,就传神地写出燕子归来的神态。“依旧”二字,则唤起对于当年燕子来时的回忆,同时也会很自然地触发这样的感慨:当年栖巢的燕子又归来了,当年欢聚的人儿呢?作者虽未曾点破,但整首词的着眼点却正在于此。作者巧妙地把要说的这句话,诱使读者替他说出来。这首词之所以耐人寻味,也正在于此。
此诗描写了冬至夜晚作者在邯郸驿舍的所思所感,表达了作者的孤寂之感和思家之情。全诗语言质朴无华而韵味含蓄,构思精巧别致,运用想象等手法,表现出淡淡的思乡之愁以及浓浓的怀亲之意。
“邯郸驿里逢冬至,抱膝灯前影伴身。”纪实,侧面写“思家”。第一句叙客中度节,已植“思家”之根。在唐代,冬至这个日子,人们本应在家中和亲人一起欢度。但是如今作者在邯郸客店里碰上这个节日,不知如何是好。第二句,就写作者在邯郸客栈里过节的情景。“抱膝”二字,活画出枯坐的神态。“灯前”二字,既烘染环境,又点出“夜”,托出“影”。一个“伴”字,把“身”与“影”联系起来,并赋予“影”以人的感情。只有抱膝枯坐的影子陪伴着抱膝枯坐的身子,作者的孤寂之感,思家之情,已溢于言表。
“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运用想象,正面写“思家”。后两句笔锋一转,来个曲笔,不直接写自己如何思家,而是想象家人冬至夜深时分,家人还围坐在灯前,谈论着自己这个远行之人,以此来表现“思家”,使这种思乡之情扩大化,真实感人。其感人之处是:他在思家之时想象出来的那幅情景,却是家里人如何想念自己。这个冬至佳节,由于自己离家远行,所以家里人一定也过得很不愉快。当自己抱膝灯前,想念家人,直想到深夜的时候,家里人大约同样还没有睡,坐在灯前,“说着远行人”。具体“说”了什么,作者并没有指明,这就给读者留下了驰骋想象的广阔天地。每一个享过天伦之乐的人,有过类似经历的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想得很多。作者没用华丽的词句,没有玩弄过多的艺术技巧,而用平实质朴的语言,却把思乡之情表现的淋漓尽致。
《邯郸冬至夜思家》没有精工华美的辞藻,没有奇特新颖的想象,只是用叙述的语气来描绘远客的怀亲之情。其佳处,一是以直率质朴的语言,道出了人们常有的一种生活体验,感情真挚动人。二是构思精巧别致:首先,诗中无一“思”字,只平平叙来,却处处含着“思”情;其次,写自己思家,却从对面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