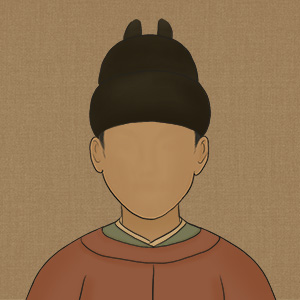孙竞称周紫芝的《竹坡词》“清丽婉曲”。这首《鹧鸪天》可以安得上这个评语。词中以今昔对比、悲喜交杂、委婉曲折而又缠绵含蓄的手法写雨夜怀人的别情。上片首两句写室内一灯荧荧,灯油将尽而灯光转为暗红,虽说是乍凉天气未寒时,但那凄清的气氛已充溢在画屏帏幕之间。这里从词人的视觉转到身上的感觉,将夜深、灯暗而又清冷的秋夜景况渲染托出。
“梧桐”二句,写出词人的听觉,点出“三更秋雨”这个特定环境;此系化用温庭筠《更漏子》下片词意:“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满满,一声声,空阶滴到明。”温词直接写雨声,间接写人,这首词亦复如此。这秋夜无寐所感受到的别离之悲,以雨滴梧桐的音响来暗示,能使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感受更富感染力量。所谓“满满声声是别离”,与欧阳修的“夜深风竹敲秋韵,万满千声皆是恨”(《玉楼春》)异曲同工,都是借情感对声音的反应表达由此构成的心理影响。那“空阶滴到明”和“满满声声是别离”,同样都是为了更深入地刻绘出别离所带来的悲苦心情。
换头“调宝瑟”三句展开回忆,犹记当年两人相对而坐,伊人轻轻调弄弦索,自己则拨动着金猊炉中的香灰。两人低声唱起那首鹧鸪词,乐声悦耳,歌声赏心;这恐怕是聚首期间最难忘的一幕了。联系着这段美妙往事的纽带是这支鹧鸪词,仍然是音响,不过这是回忆中的歌声和乐曲声,并非现实中的秋雨声。下片回忆中的欢乐之音与上片离别后的凄凉雨声,构成昔欢今悲的鲜明对照,真是袅袅余音只能引起悠悠长恨了。
结末“如今”两句,是使词意转折而又深化的着力之笔。“如今”两字,由“那时”折回眼前。那时同唱小调,如今却独居西楼,唯闻风声萧萧,雨声滴滴;“不听清歌也泪垂”,以未定语气呼应上片末句,显示了词人心头的波涛起伏;自从别离以后,经常闻歌而引起怀人的伤感,记忆中的美妙歌声无时不萦回耳际,而在今夜那风雨凄凄、“万满千声皆是恨”的情况下,即使不听清歌也就足以使人泪下而不能自止了。这里转折词意,也是为深化词意,暗示出从曲终人不见、闻歌倍怀人到不听清歌亦伤神的内心感情变化,以悬念方式道出对伊人的情之深,思之切。
周紫芝在另一首《鹧鸪天》词的小序里指出:“予少时酷喜小晏词,故其所作,时有似其体制者。”可以拿晏几道的《鹧鸪天》来作一比较:“彩袖殷勤捧玉钟,当年拚却醉颜红。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上片写昔年相逢于豪筵之前,下片叙别后思念。末两句先直说今夜重逢,本为久别再见,应该十分欢欣,只因以往失望次数太多,反而相对而不敢相信。一个“恐”字,转折词意,把惊喜怀疑的神情表现无遗,不仅道出相逢前相思之苦,而且通过疑真为梦,反映了目前的相逢之乐更是不同寻常。这种写法是直说而仍有转折,有感情起伏。
两者相比,这首词所采用的手法,如昔与今、喜与悲、正面说与反面说等等手法,做到委婉曲折而又含蓄深沉,确乎从小晏词变化而来。特别是末尾两句,以“如今”作为“昔与今、喜与悲”的转折词,以否定语气点出别离之苦,再相见之难,较直说更易引人深思。
这首词上片首三句明写荷花,实写美人,以“碧玉堂深”点出美人所居之地;以“水”兼写“小芙蓉”及美人所在玉堂的清姜环境。后三句连用“闭”、“掩”、“倚”、“拖”四个有独特含意的动词,把女主人公如痴如醉如怨的情状淋漓写出。
下片“迟迟”二句以乐景写愁情,以鸳鸯兴相思。结尾二句,是女主人公对上二句“凝望”后的瞬间表情,如梦如幻,以笑写愁,笑得愈沉醉,愁情也愈酸楚。
《富贵不能淫》的内容是孟子批驳景春关于大丈夫的错误言论。我们首先来看文章批驳的“靶子”,即景春的观点。
景春认为公孙衍、张仪之流是大丈夫,为此,他用反问句向孟子询问说:“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公孙衍和张仪难道不是真正的大丈夫吗?言外之意就是说,公孙衍和张仪是真正的大丈夫。景春提出这个观点的依据是,公孙衍、张仪能够左右诸侯,“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他们发起怒来,诸侯们都会害怕,安静下来,天下就会平安无事,他们威风八面,权倾天下,能够左右时局。
针对景春的“论点”和“论据”,孟子先破后立,先批驳景春的错误观点,再阐述什么是真正的大丈夫。
首先,孟子针锋相对地用了一个反问句:“是焉得为大丈夫乎?”这个怎么能够叫大丈夫呢?对景春的观点给予直接的否定。
其次,孟子进行了分析,回答了“公孙衍、张仪之流”为什么不能称为大丈夫。
孟子的说法含蓄而幽默,只是通过言“礼”来说明女子嫁时母亲的嘱咐,由此得出“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这里值得 我们注意的是,古人认为,妻道如臣道。臣对于君,当然也应该顺从,但顺从的原则是以正义为标准,如果君行不义,臣就应该 劝谏。妻子对丈夫也是这样,妻子固然应当顺从丈夫,但是,夫 君有过,妻也就当劝说补正。应该是“和而不同”。只有太监小老婆婢女之流,才是不问是非,以一味顺从为原则,实际上,也就是没有了任何原则。“妾妇之道”还不能一般性地理解为妇人之道,而实实在在就是“小老婆之道”。
孟子的挖苦是深刻而尖锐的,对公孙衍、张仪之流可以说是 深恶痛绝了。遗憾的是,虽然孟子对这种“以顺为正”的妾妇之道已如此 痛恨,但两千多年来,这样的“妾妇”却一直生生不已,层出不穷。时至今日,一夫一妻已受法律保护,“妾妇”难存,但“妾妇说”却未必不存,甚或还在大行其道哩。
孟子的办法是针锋相对地提出真正的大丈夫之道。这就是他 那流传千古的名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怎样做到? 那就得“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就 还是回到儒学所一贯倡导的仁义礼智上去了。这样做了以后,再 抱以“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的立身处世态度,也就 是孔子所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或孟子在 另外的地方所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尽心上》那就能够成为真正的堂堂正正的大丈夫了。
孟子关于“大丈夫”的这段名言,句句闪耀着思想和人格力量的光辉,在历史上曾鼓励了不少志士仁人,成为他们不畏强暴, 坚持正义的座右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