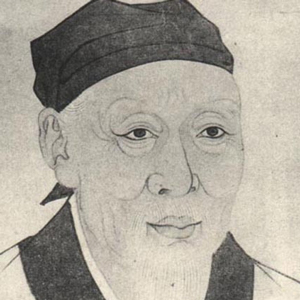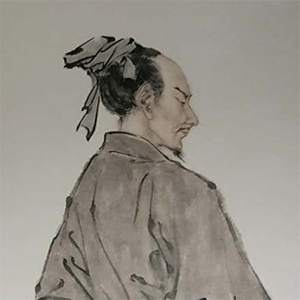这首诗描绘了一幅萧瑟衰败的旧居景象,基调凄凉哀怨。房屋的变迁,人事的推移,直接的原因是社会的动荡,而又像是生命枯荣变幻的必然。全诗以“一觞聊可挥”做结,看似要以及时行乐来驱散心中的“恻怆”和“所悲”,但是诗人的“及时行乐”有其自身的独特性,是其人生智慧的表现形式:纵浪于“自然”之中,身心达到适意之境。陶渊明的生活建立在田园生活的“自然”的基础之上,他解决人生问题的智慧也是由此生发出来。
陶渊明在回旧居之前已经历了辞官归田后的六年躬耕生活,可以说历尽艰难困苦,而今体力渐衰,迫使他不得不回到老家。眼前破落的故里,又增添了诗人的恻怆之情。浔阳(今江西九江)为京都建康(今江苏南京)与西境重镇江陵(今湖北荆州)之枢纽。在过去十年中,桓玄篡乱,卢循起义,浔阳地区及左近都有激战。社会动荡与战乱,使浔阳日益凋敝。这首诗表面上似乎是专因环境、体衰而悲慨,但如果联系“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八首》之五)来看,那就会令人感到陶渊明可能有更多而未明言的悲哀。诗的最后两句“拨置且莫念,一觞聊可挥”,便透露了这一消息。
古代诗词中,以“游春”、“咏春”为主题的作品何止千百篇,但内容大多不外乎“伤春”、“怅春”。赵秉文的这首《青杏儿》不与前人雷同,风格清新,语句明白如话,本色天然。
上片首句:“风雨替花愁”,语句凝炼,一个“替”字,生动地表达出作者对花的关切之情。当暴风雨袭来的时候,娇嫩的花儿必将遭受风雨的摧残。多情的词人不免“替”花儿深深地担忧。“风雨罢,花也应休”,想来当肆虐的狂风暴雨过后,遍地残红,花期也该成为过去了吧。花开又花落,不由人不惜花,而那多情善感的赏花人、惜花人,也就在这花飞花谢、春去春来中白了少年头。所以,年年岁岁,岁岁年年,时光如流水,莫负春光啊,这也是“劝君莫惜花前醉”的缘故。词的上片写至此处,词人表达了几许怅惘悲伤之感。
然而,词人却不想用更多的悲凉、迟暮感来感染读者。笔调轻轻一转,“乘兴两三瓯”,下片意境立刻由沉闷、苦恼转向了明彻、欢快。“莫惜”深化为“乘兴”,揭示人们要积极开创美好的生活,良辰美景、赏心乐事要尽情享受。两三盏薄酒,听江山清风,观山间明月,柳绿花红,莺飞草长,造物是这样的神奇,大自然是这样的美妙,做人应该“拣溪山好处追游”,得欢愉时且欢愉,莫要自寻烦恼。“但教有酒身无事,有花也好,无花也好,选甚春秋。”词的结尾表达只要胸襟豁达,有美酒相伴,无俗事缠身,有花也罢,无花也罢,春天永远常在,春光永远无限。
这首词上下片对比鲜明,语言通俗易懂,又不流于俗白,体现了作者的艺术修养和旷达的人生情怀。
这首吟咏落梅的诗作,寄托了深沉的政治感慨,这对于只求形似的六朝一般咏物诗来说,是一大发展。
“新叶初冉冉,初蕊新霏霏”,起首两句便暗寓忧惧的心理。“冉冉”,说明梅花的嫩叶还很柔弱,意指自己在政治上并不是强有力的;“霏霏”,说梅花的新蕊随风飘落,暗寓自己政治地位的不稳。明写落梅,暗写政治。
从“逢君后园讌”至“翡翠比光辉”,这六句以美人自拟,写他同随王的亲密关系。意思说他的美才可比战国晋文公时的美女南威之貌;参与随王后园宴会,又如《诗经·卫风》所写“硕人”之“巧笑”,相随而归;又说随王亲手摘下梅花赠送给他,他便像古美人把花插到发髻上,其光彩胜过翡翠美玉。这段话表达了他受到随王宠幸的感激之情。
“日暮长零落,君恩不可追”,结尾两句语气一转,由乐转忧,以梅花之落,喻指君恩之衰。忧君恩之衰的心理,是由介入皇室内部矛盾斗争所产生的危惧心理引发出来的,与担心“时菊委严霜”同义。这末两句,从篇幅来说,只是全诗的五分之一,然而从中心思想而言,却是全诗的主干与核心。也可以说,担心斗争失败,反而招来杀身之祸,这才是他借咏落梅委宛地向随王吐露出来的真情。
咏物诗至六朝而自成一格,宫体诗中之咏物已极尽图貌写形之能事,其所追求者在于形似。与山水诗至谢朓手中由客观之描写转而介入主观之抒情一样,咏物诗至谢朓手中亦一变,由求其形似,转而求其寄托。谢朓之咏物诗既有与时代相通的善于写物图形的特性,又汲取了《诗》《骚》以来比兴的传统,在客观的物象之中寄托主观的旨意。这首《咏落梅》诗便是如此。传统的所谓“香草”“美人”的比兴,这里都用上了。诗中既以“落梅”(香草)自拟,又以“南威”自拟,其所比拟均在似与不似之间,即所谓不即不离,不粘不脱者也。这一艺术境界成了唐宋咏物诗词的最高准则。可以说,这首诗的艺术,正标志谢朓在咏物诗方面的杰出贡献。
诗一开篇,着笔高远,“鹤鸣楚山静,露白秋江晓”,秋晨清露白鹤,一连 串明静、清丽而活泼的意象,给山描绘了一幅雄阔的背景图,寄寓诗人“知是山之特立,不与培塿为类”(《始得西山宴游记》)的浩然之气。然而现实却是残酷的,诗人以平淡的笔墨,叙述了登山的历程:“连袂度危桥,萦回出林杪。”愚溪上有木桥相连,桥之“危”,路之“萦回”,道出了诗人心怀恐惧、仕途艰危的复杂感情,与上联形成极大的反差,正表现诗人执着追求而重受挫折、处境艰危的困苦心境。临山,诗人先以九嶷与洞庭对举,重彩描绘了自己的政治理念。九疑在永州南宁远境内,是舜帝归魂之所。舜南巡,“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史记·五帝本纪第一》);洞庭在湘北,是楚怀王放逐屈原的地方。屈原在《湘夫人》中写道:湘君迎候湘夫人,秋水伊人,望眼欲穿,看到的却是“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秋绪茫茫,忧从中来。诗人描写一高一小、一明一暗的两组意象,让人联想,意味无穷。登山辽望宇宙间,心中的意念早已超出宇宙万物,“目击道存”,天地之间,惟此而高。“迥穷两仪际,高出万象表”,也可看成自况语,表现了诗人遗世独立,睥视一切的情怀。诗中意与象、情与景、神与形相互交融,把抽象的理念化作具体的物象,物化的背后却是焦渴的期盼。诗人这种理念,这种期盼,寄希望于北去的潇湘水带到遥远的长安,也希望遥迢的风能给被谪贬的人带来好消息。遭贬谪七年了,无所事事,纷扰平庸的生活使诗人内心十分痛苦,日子过得胆颤心惊。诗人把自己比作满肚子苦水的奴隶,面对愚昧,害怕再受困扰,再次扑倒;面对“亲爱”者的疏远,期盼愈觉渺茫。在执着追求与重遭挫折这对矛盾中,诗人无可奈何,只好到现实中求解脱:“偶兹循山水,得以观鱼鸟。”诗人这种祈祷解脱,正反衬出诗人受羁绊不得自由的内心巨痛。
这是赠给崔策的诗,崔策字子符,柳宗元姐夫崔简的弟弟,属中表亲,当时就学于诗人。柳写有《送崔子符罢举诗序》,说他“少读经书,为文辞,本于孝悌,理道多容,以善别时,刚以知柔,进于有司,六选而不获。”亲戚加师生的双重关系,心中的真实得以应时而发。诗中以“鹤鸣”暗喻、“连袂”点题,点明这种关系和崔策对诗人的敬重,结篇以一“幸”字收束,以表诗人的感激之情。除此之外,通篇未涉及崔策,而是言事抒情明志。刘熙载在《艺概》里说:“叙物以言情谓之赋,余谓《楚辞·九歌》最得此诀。”诗人自得其屈原的真传,借“九疑”、“洞庭”,让人联想到舜帝之圣明,湘夫人“倚靡以伤情”,寄寓君臣际遇、人生离合之痛,寄托自己的不幸。诗人还创设了一连串精妙意象:“两仪”暗喻崇高的理念,“驰景”、“寒篠”、奴隶、鱼鸟,无不寄托或愿望、或担心、或痛苦的情怀。诗人又精于炼字。 “危桥”并非实景,乃是心境,是恐惧的写照。“萦回”既是写实,也象征仕途艰难。还有诗中的“泛”、“递”,热盼之情溢于言表;“循”、“观”二字,无奈中的潇洒,痛人心脾。前人论诗“用字”是“撑拄如屋之有柱,斡旋如车之有轴”(罗大经《鹤林玉露》),诗人最得其妙。
纵观全诗,离骚风韵,字字心血,却又真的做到了“岭渠直道当时事,不着心源傍古人”(《随园诗话卷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