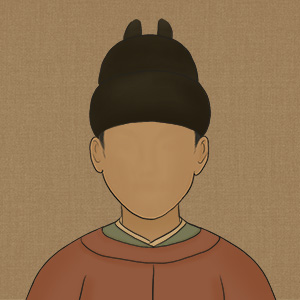毛文锡是西蜀代表词人之一,尤工小词,此阕为其杰作,素受赞诵,沈初有诗曰:“助教(温庭筠)新词《菩萨蛮》,司徒(毛文锡)绝调《醉花间》。晚唐风格无逾比,莫道诗家降格还。”推崇其为一代诗雄。文锡词多“以质直见情致”,此阕却写得含蓄婉转,曲致其意,颇耐寻味,表现出风格的多样化。
此词破题用“陡健之笔”(《词徽》卷五),劈头便云:“休相问,怕相问,相问还添恨。”云起马面,突兀而来,挟带着强烈的感情。词用口语,用民间文学的重复、回环的手法,语言流利清新。通观全篇,乃替思妇设辞,有个性特征。女主人公不愿人问,更怯惧人问,唯恐平空再增添一段怅恨伤心;既云“添恨”,显见心头已有恨郁积。所“恨”什么?怕“问”什么?为什么“相问”会如此深深地触动心底隐痛?首三句无端而降,平地起波,顿时结成一个悬念。接下“春水”两句并不予回答,而是宕开一笔,折入景中,拉展出一卷池塘春意图。女主人以徘徊池塘畔,只见:微风徐拂,春水满塘,碧池如镜,洗映蓝天;水面上浮游着三五成群的紫色鸂鶒,头披五彩缨,双双相嬉,活泼的生机,不时打破池塘的宁静。画面讲究色彩,动静相映。这幅画深有寓意,不仅“春水”交代时令,“池塘”交代地点,更主要的是“鸂鶒相趁”表面写景,实际暗示幸福的爱情生活。“鸂鶒”,一种水鸟,头有缨,尾羽上矗如舵,羽毛五彩而多紫色,似鸳鸯稍大,故又名紫鸳鸯。花间派词人常将之视作鸳鸯来咏写。“趁”,因利乘便之意,词指鸂鶒双双相嬉、爱抚。词人写鸳鸯,鸂鶒,“不是鸟中偏爱尔,为缘交颈睡南塘”(牛峤《望江南》),是以双双相随的水鸟象征美满恩爱的婚姻。至此,读者依稀感到女主人公的“恨”,似与爱情生活的缺憾有关,但悬念仍未解。
过片二句承上片结句而来,由池塘水涨而翻忆昨夜春雨,是“春水”句的补足和延伸;水因雨而涨。一夜春雨霏霏,雨带寒意,临明一阵逼人。词化用唐韩偓《懒起》:“昨夜三更雨,临明一阵寒。海棠花在否?侧卧卷帘看”诗句,暗示女主人公彻夜不眠,卧听雨声。画面色彩气氛由热转为冷,自上片春江水暖跌入临明雨寒,心情也随之暗转。临明的寒意,侵人肌肤,女主人公由自己身上寒,推想到“伊人”的寒暖,而牵肠挂肚,逼出煞拍二句“偏忆戍楼人,久绝边庭信”。“戍楼”,征人所居,挑明女主人公身份,原来是个独居闺房的边防军人的妻子。丈夫万里从戎,边庭音信久已断绝。生死未卜,寒暖不知,不能不使妻子终日牵挂,惊忧怅悲,正是“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陈陶《陇西行》)。结尾二句,如泣如诉,解开了全阕的悬念,词旨大明,乃思妇思念征夫。这才明白:女主人公为什么在词首启唇即哀诉:“休相问,怕相问,相问还添恨。”原来她怕人家问她远征丈夫的消息。也才明白:她闲步池塘,是为了避开人目,排遣愁怀。不料春景虽美,“触景更添恨”,水鸟双双成对,自己却茕独只影,说不出的凄愁伤感。因春色而生春心,因春心而触春恨。故过片心境迅即浸入彻骨春寒之中。煞拍如泉流归海,回环通首,源流有尽而不尽之意。况周颐评曰:“《花间集》毛文锡三十一首,余祇喜其《醉花间》后段‘昨夜雨霏霏’数语,情景不奇,写出正复不易,语淡而真,亦轻清,亦沈着”(《餐樱庑词语》)。
这是首感梦词,而这与一般的感梦词又不完全一样,把梦中所见之人的容貌、服饰描摹得极其细腻逼真,并没给人以缥缈恍忽、迷离朦胧之感,因而使人一时很难看出是在写梦。
起头“润玉笼绡,檀樱倚扇。绣圈犹带脂香浅。”三句着意刻画梦中所见之人的玉肤、樱唇、脂粉香气及其所着纱衣、所持罗扇、所带绣花圈饰,从色、香、形态、衣裳、装饰等逼真地显示其人之美。“榴心空叠舞裙红,艾枝应压愁鬟乱。”两句,以“舞裙”暗示其人的身份,以“愁鬟”借喻两地相思,以“榴心”、“艾枝”点明端午节令。上句的“空叠”二字,是感叹舞裙空置,推测此因无心歌舞;下句的“应压”二字,则瞥见发鬓散乱,想象其人应含深愁。
上片五句,句句写梦,却始终不点破是说梦。直到下片换头,才以“午梦千山”一句点出以上所写原来只是南柯“午梦”。句中的“千山”二字,表明梦魂与现实距离之遥远。这一句是写山长水远,路途阻隔,只有梦魂才无远弗届。对下句“窗阴一箭”,前人大都解说为:慨叹光阴似箭,与梦中人分别已久。但这里的“一箭”,似指漏箭,这不是感叹光阴逝去之速,而是说刻漏移动之微。联系上句,作者写的是:梦中历尽千山万水,其实只是片刻光景。两句合起来,既深得梦的神理,也形象地道出了作者午梦初回时所产生的对空间与时间的迷惘之感。
换头两句刚写到梦已醒,忽又承以“香瘢新褪红丝腕”一句,把词笔重又拉回到梦境,回想和补写梦中所见之人的手腕。这一词笔的跳动,正是如实地写出了作者当时的心灵状态和感情状态。在这片刻,对作者说来,此身虽已从梦中觉醒,而此心却仍留在梦中。梦中,他还分明见到其人依端午习俗盘系着采丝的手腕,以及其人腕上似因消瘦而宽褪的印痕。
如果联系他另外写的几首端午忆姬之作,可发现,词人对伊人之在端午日以采丝系腕一事留有特别深刻的印象。这就无怪他在这次梦中也注意及此,并在梦醒后仍念念不忘了。歇拍“隔江人在雨声中,晚风菰叶生秋怨”两句,则两从梦境回到现实,并就眼前景物,寓托自己自“午梦”醒来直到“晚风”吹拂这段时间内的悠邈飘忽的情思和哀怨的心境。
此词上片正是以实笔来描摹虚象,写得十分真切;在结拍处却以虚笔来点画实景,写得情景异常缥缈。也许正因其幻而益真,真而益幻,所以才具有“天光云影,摇荡绿波”之美,使人深深地被这种境界所吸引,而又感其乍离乍合,难以追寻。就连最不喜欢梦窗词的王国维也对“隔江人在雨声中,晚风菰叶生秋怨”二语大加赞赏,这不仅是因为这两句所摄取的眼前景物——“雨声”、“晚风”、“菰叶”,既衬托出、也寄寓着作者在梦醒后难以言达的情思和哀怨,同时兼有以景托情和融情入景之妙。
《酬刘柴桑》前两句“穷居寡人用,时忘四运周”说没有什么人与他来往,所以他有时竟然忘了四季的节序变化。然事实并非如此,诗人正是在知与不知中感受生命的意趣。之后吟道:“空庭多落叶,慨然知已秋。新葵庭北墉,嘉穗养南畴。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不?命室携童弱,良日登远游。”此八句所写与前两句恰好相对,时忘四运与叶落知秋,多落叶与葵穗繁茂,甘心穷居与择日远游,此数者意象矛盾,却展现了时间的永恒性与生命的暂时性。由忘时乃知穷居孤寂落寞;而枝头飘然而至的落叶,乃知秋天的到来,生命的秋天亦在浑然不觉中悄悄来临;墙角的新葵、南畴的嘉穗,虽暂时茂盛繁荣却犹似生命的晚钟难得长久,从而暗示生命的荣盛行将不再。因此诗人在穷居忘时之际又察其生命飞逝,择良日作此远游折射出生命的亮色。“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不?”一句没有对来岁未知的恐怖,但有尽享今朝的胸襟。诗人情绪的宛转之变与物的荣悴之态,不能忘世的感慨之忧与对生命的达观之乐,交织成多层次的意义。
诗中以隐居躬耕的自然乐趣和人生无常的道理来酬答刘柴桑,在淳朴祥和之中,诗篇流露着田园生活的乐趣。这首小诗共十句,虽然比较简短,然而它内容醇厚。在写法上也比较独特,撇开与对方问答一类的应酬话,只写自己的感受、抱负与游兴,显得十分洒脱别样。在遣词造句上,粗线条的勾勒,并着墨点染,使全诗呈现出古朴淡雅的风格,又洋溢着轻快明朗的感情。
范至能,即南宋著名诗人范成大,比陆游小一岁。公元1162年(绍兴三十二年)九月,孝宗已即位,两人同在临安编类圣政所任检讨官,同事相知。公元1175年(淳熙二年)六月,范成大入蜀知成都府、权四川制置使,辟陆游为成都府路安抚司参议官兼四川制置使司参议官,范成大有一首诗:“余与陆务观自圣政所分袂,每别车取五年,离合又常以六月,似有数者。”《宋史·陆游传》说:“范成大帅蜀,游为参议官,以文字交,不拘礼法,人讥其颓放,因自号放翁。”这年春,陆游因病休居城西桥一带;范成大也因病乞罢使职,公元1177年(淳熙四年)六月,离蜀还朝。范、陆在蜀,颇多酬答唱和之作,这首词就是其中一首,如作于公元1176年(淳熙三年)秋陆游病后休官时。
公元1176年(淳熙三年),陆游五十二岁,已离开南郑军幕,在成都制置使司任官,后又因病和被“讥劾”而休官,有年老志不酬之感。故上片开头三句:“华鬓星星,惊壮志成虚,此身如寄”,即写此感。这种感情,正如他《病中戏书》说的:“五十忽过二,流年消壮心”,《感事》说的:“年光迟暮壮心违”。“壮心”的“消”与“违”,主要是迫于环境与疾病,故接下去即针对“病”字,说:“萧条病骥。向暗里、消尽如年豪气。”这一年的诗,也屡以“病骥”自喻,如《书怀》:“摧颓已作骥伏枥”,《松骥行》:“骥行千里亦何得,垂首伏枥终自伤”,这一年的《书叹》诗:“浮沉不是忘经世,后有仁人知此心。”《夏夜大醉醒后有感》诗:“欲倾天上银河水,净洗关中胡虏尘。那知一旦事大谬,骑驴剑阁霜毛新。却将覆毡草檄手,小诗点缀西州春。鸡鸣酒解不成寐,起坐肝胆空轮囷。”浮沉不忘经世,忧国即肝胆轮囷,可见所谓消沉,只是一时的兴叹而已。“梦断故国山川,隔重重烟水。”由在蜀转入对故都的怀念,而“心在天山”的心迹也透露无疑,同样也表现出作者终日忧愁,于何时才能重返前线的愤慨。另一方面,也为下文“身万里,旧社调零,青门俊游谁记”。作一过渡。“旧社”义同故里,这里紧属下句,似泛指旧友,不一定有结社之事,苏轼《次韵刘景文送钱蒙仲》:“寄语竹林社友,同书桂籍天伦”,亦属泛指。“青门”,汉长安城门,借指南宋都城临安。这三句表示此身远客,旧友星散,但难忘以前同游交往的情兴。陆游在圣政所时,与范成大、周必大等人同官,皆一时清流俊侣,念及临安初年的旧友,都引以自豪。就如《诉衷情》说:“青衫初入九重城,结友尽豪英。”《南乡子》说:“早岁入皇州,樽酒相逢尽胜流。”换头“尽道锦里繁华,叹官闲昼永,柴荆添睡”,又自回忆临安转到在蜀处境。锦城虽好,柴荆独处;投闲无俚,以睡了时,哪能不“叹”?“清愁自醉。念此际、付与何人心事”。这两句是倒文,即此时心事,无人可以交谈,只得以自醉对付清愁之意。时易境迁心事无人可付;只能是壮志未消、苦衷难言的婉转倾诉。作者“借酒浇愁愁更愁”,酒不能消“清愁”,愁反而成醉。巧妙、曲逝地反映出作者的心态。
“纵有楚柁吴樯,知何时东逝?”无计消愁,无人可托心事,转而动了归乡之念,也属自然。因“东归”而想望“楚柁吴樯”,正如他《秋思》诗说的:“吴樯楚柁动归思”,“东逝”无时,秋风又动,宦况萧条,又不禁要想起晋人张翰的故事:“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薄羹、鲈鱼脍”,遂“命驾而归”,顿感“空怅望,鲙美菰香,秋风又起。”更难堪的,是要学张翰还有不能,暂时只得“空怅望”而已。值得提出的是,作者的心情,不仅仅是想慕张翰。他的“思鲈”,还有其不得已的苦衷,诗集中《和范待制秋日书怀二首》,作于同时,不是说过“欲与众生共安稳,秋来梦不到鲈乡”吗?陆游是志士而非隐士,他的说“隐”,常宜从反面看。这也曲折反映出作者怀才不遇、壮志未酬的无奈心情、欲罢而又不甘心。因两种矛盾心情,遂发出“空怅望”的感叹。才有“思鲈”的痛苦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