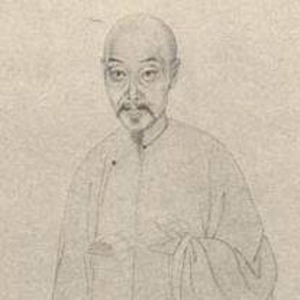乾隆三十四年(1769),黄景仁乡试落第、生计艰难之际,应浙江观察潘恂的邀请,到了杭州。他与友人郑虎文、仇丽亭等,徜徉湖光山色之间,诗酒唱和。居住月馀,他提出“母老家贫,居无所赖,将游四方,觅升斗为养耳” (左辅: 《黄县丞状》),准备谒见湖南按察使王太岳,寻求出路。友朋一再劝阻,他在《思旧篇》中回忆道:“我时抱病将远游,公等苦为狂奴忧。”这首词就是谢绝他们的好意,决意奔赴湖南而作。仇二即仇丽亭,杭州人,作者好友。他在《寄丽亭》诗中自注云: “君门前桥名一桥。余之武林,每舣舟焉”。
“一事与君说,君莫苦羁留”,与小序相应,直截了当,揭出作词本旨在于谢绝友朋劝告,决心远赴湖湘。下面就他们的劝说作回答。“百年过隙驹耳,行矣复何求? ” 回答“怜余病”。时光匆匆逝去,人生百年,“如白驹过隙”。有病在身,更应抓住时光,及时追求,怎能因此止步? “行矣复何求”有义无反顾的气概。“且耐残羹冷炙,还受晓风残月,博得十年游”,则是回答“湖湘道远”问题。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这里用个“耐”字,意味深长: 为了改变自己的坎坷境地,可以含垢忍辱。柳永《雨霖铃》名句“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这里的“还受晓风残月”,意蕴是:为了壮游,愿意忍受与亲朋的分离,忍受别离后的相思,忍受一路风霜雨雪的侵袭。反之,如果因病因远而蹉跎岁月,象东汉时向长(子平)等到“男女娶嫁既毕”,“遂肆意与同好,俱游五岳名山” (《后汉书 · 逸民传》),恐怕是时不待人,早生华发了。向子平是有名的高士,备受文人雅士的称赏。词人一反传统用意,表达了积极奋发的意气。上片回答友朋劝阻,平平道来却颇有深意。
下片开头提到历史上的三个人物,即高渐离、冯驩和王粲。“离击筑”,战国时代的高渐离,为挚友荆轲复仇,秦王弄瞎了他的眼睛。他以铅置筑内,在为秦王演奏时,乘机击秦王,未中,被杀。词人对高渐离反抗强暴的精神表示赞赏。 “驩弹铗”是讲冯驩弹铗的事。 战国时孟尝君的门客冯驩, 三次弹铗, “长铗归来兮,食无鱼”,“长铗归来兮,出无车”,“长铗归来兮,无以为家”。他的要求一一得到满足后,为孟尝君“市义”、“复位”、“立宗庙于封地”,营“狡兔三窟,万无一失”。词人借此表示向往“士为知己者用”的佳话,希望得到赏识,实现抱负。“粲登楼”指王粲登楼作赋,抒发忧国、忧民、怀才不遇之感。王粲的形象正是作者的写照。“仆虽不及若辈,颇抱古今愁”,总束一句,追踪古人,思展宏图。而远赴湖湘,谒见湖南按察使王太岳,正是为了实现这样的愿望。如果说上片是多侧面的展开,惜时、求仕、远游,而在下片,则集中理想的追求。用古人古事来表达,一是为了含蓄,二是在于带有豪言壮语性质。
回答了友人的劝说,抒发了自己的情志,兴高采烈,想象在明月之夜,手把《离骚》,直下洞庭。“大笑揖君去,帆势破清秋”,如李白的“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湖湘是屈原放逐沉江之地,《离骚》是屈原伤时感世、充满爱国激情的千古名作。直下湖湘,自然想到屈原,写得自然,又符合诗人气质。“仆虽不及若辈,颇抱古今愁”是理性的议论,是形象的刻划,互相映照,相得益彰。词人一生困顿,贫寒相继,但雄心不改,欲与历史人物相颉颃,“大笑揖君去”,正是表现此种壮志豪情。
李贺诗歌总的特色是奇崛愤激、凄凉幽冷,牛鬼蛇神纷至沓来,其诗歌内容多是他的幻想世界的外化物。这首《感春》却颇为难得,从中可以窥见李贺的生活景况。
这是一首五言律诗,首联点明时序正是春天。春天本应是万物恢复生机之时,世人在寒冬季节早在盼望春暖花开的春天。但在李贺眼中,春天却是一片愁红惨绿的伤心物。“萧条”之上着一“自”字,更显出无可奈何的凄凉。为什么诗人对春而伤春?诗中继续道:人处穷困潦倒之中实在难生赏春的雅兴,对花无端生悲。“北郭骚”是出现在《吕氏春秋》中的一位穷困之人,李贺将他比喻自己家境的萧条。
颔联承接首联之意,继续状写穷困之景况,也见出心中的悲凉:榆叶薄如莱子钱,舞儿腰若袅袅柳。这里需作一些解释:榆树之叶,其状如钱,中间有孔,人又称榆叶为榆钱。而莱子钱则是南朝宋废帝景和元年所铸的一种钱币,极薄,故价值也低。“榆穿莱子眼”意指家中贫寒,钱财无多。“舞儿”是诗人自比,穷困落魄已使自己骨瘦如柴。舞儿腰细原也是一种美,但到了李贺笔下,却令人起几多感慨。写家境萧条却不正面说出,寓意榆钱、细腰,其痛苦意味又比正面说出更为深长。
第三联中,诗人暂时置下贫困的愁苦,用两句话写春景。春日融融,落花游丝在静静的太阳光下无声无息地飘荡,时而几声伯劳鸟的哀鸣,把人的思绪带回到伯劳因被后母所害而化鸟的悲惨故事中。这两句写得蕴含无穷。现在无从考证短命的诗人是否曾经娶妻成家,但单看这两句,一丝渴望获得平和温暖的家庭、能与子女共享天伦的情思是以一种十分凄苦的笔墨写出来的。笔下经常出现“秋鬼”、“败坟”、“冷血”字眼的诗人心中原来也有着这样一颗温热、渴望的心。
尾联写的是拿起胡琴来排遣胸中的遗恨,将满腔的心事向琴槽诉说。自古才人多落魄。偏偏柔弱多病的李贺注定了没有发迹的希望,绝望的诗人只能遨游神仙鬼怪世界,可以说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与神鬼之精神相接,以此来取得心理的平衡。诗人身处贫困潦倒、忧郁悲愤的处境,其内心的痛苦纠缠着他的灵魂。所以,在诗人听来,弹奏的胡琴声中也像是寄寓着诗人的怨恨,而自己满怀愁闷,却又惟有弹琴来排遣。胡琴声骤然而急,声声滑落琴槽,这又正似啼血的杜鹃、哀鸣的伯劳。
运用大量的意象,是李贺诗歌中的一大特色。无论是自然类意象,还是社会类意象,其诗歌中核心意象群的审美特征就是“凄怨”。而形成这一审美意象的原因则是在于诗人凄怨的心态和情感。杜牧评其诗为“怨恨悲愁”。这首诗中采用了大量的意象,如榆柳等景物的美好,烘托诗人的凄苦,以榆钱、柳断补足“萧条”之意。“神燕”、“伯劳”寄托了诗人盼祥瑞、避凶灾的美好愿望。“胡琴”成为了诗人排遣苦闷的工具,而“琴槽”则成为了诗人诉说心事的对象。诗人对这一连串的意象,进行了极力的渲染烘托,展示了一种饱“悲”之美,借以强化了诗人的悲惨不幸。
韩琦的诗平易中见深劲,比较讲究炼意,但与一般的西昆体作家相比,风格又比较朴素。这首诗从水阁入题写九日宴会的兴致。
第一句写池馆园林荒凉的感觉,写景较工,而以疏淡见长,且与第三句“秋容淡”相呼应。与全诗以意胜的特点很一致。第二句点出九日宴会之事,虽然池馆倾圮。台榭荒芜,却有嘉客来助成重阳雅集,环境虽然荒僻,人的兴致却很高,这一对比的意思一直贯穿到诗尾。
三、四两句正面写九日赏菊,是韩琦的名句,这两句借赞颂重阳时节,菊花虽晚开而尤为芬芳而寄意:晚节可贵,要注重晚节。两句含比兴之意,字面上是写菊花犹有晚香,言外之意则是表达自己有岁虽晚而节弥坚的品格。
五、六两句写眼前宴会之事,重九宴会饮酒是诗歌中的传统内容,蟹螫也是展现文士风流雅致情趣的传统意象,但此诗不仅仅是简单借用这两个传统的重九意象,还更多地写到了酒和蟹螯本身,这种写日常生活中文士生活趣味的作法带有自居易的特点。
诗的最后写自己年老虽不能豪饮。但诗兴仍豪,有翻案之意。这样写诗的意思不致衰竭,章法健举。
韩琦这首七律,可谓信手拈来,“咸得于自然”,浑然天成。也就是诗人直抒胸臆而作诗,而不是“出于经史”;整首诗歌体现的并不是在秋色里持续的的消沉,而是在一片肃杀的秋景之中强调一种高洁的人品,这正是这首诗歌能够被人广为流传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首词充满了强烈的主观情绪,起笔甚为突兀,直以渊明就是自己的前生。他后来作的《和陶饮酒二十首》序云:“吾饮酒至少,常以把盏为乐,往往颓然坐睡。人见其醉,而吾中了然,盖莫能名其为醉为醒也。”陶渊明好饮酒,自言:“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饮酒二十首》序)苏轼能理解渊明饮酒的心情,深知他在梦中或醉中实际上都是清醒的,这是他们的共同之处。“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充满了辛酸的情感,这种情况又与渊明偶合,两人的命运何其相似。渊明因不满现实政治而归田,苏轼却是以罪人的身份在贬所躬耕,这又是两人的不同之处。但他以旷达的态度对待人生的逆境,以逆为顺,因而“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这些春天富于生气的景物使他欢欣,感到适意。
词的下片略叙东坡雪堂周围的景观。鸣泉、小溪、山亭、远峰,日与耳目相接,正如其《雪堂问潘邠老》所说:“余之此堂,追其远者近之,收其近者内之,求之眉睫之间,是有八荒之趣。”仅以粗略的几笔勾画,表现出田园生活恬静清幽的境界,“意适于游,情寓于望”,超世遗物。作者接着以“都是斜川当日景”作一小结,是因心慕渊明,向往其斜川当日之游,遂觉所见亦斜川当日之景,同时又引申出更深沉的感慨。陶渊明四十一岁弃官归田,后来未再出仕,五十岁时作斜川之游。苏轼这时已经四十七岁,躬耕东坡,一切都好像渊明当日的境况,而不知是否也会像渊明一样就此以了余生。那时王安石已罢政数年,章惇、蔡确等后期变法派执政,政治生活黑暗,苏轼东山再起的希望很小,因而产生迟暮之感,有于此终焉之意。结句“吾老矣,寄馀龄”的沉重悲叹,说明苏轼不是自我麻木,盲目乐观,而是对政局存在深深的忧虑,是“梦中了了”者。
这首词似随手写出,未曾着意经营,而词人胸中自有成熟的构想,故下笔从容不迫,不求工而自工。从纵的方面看:醉醒连渊明,渊明连躬耕,躬耕连东坡,东坡连及雪堂与周围景物,景物连斜川,最后回应到陶渊明《游斜川》诗之“开岁倏五十,吾生行归休”,迤逦写来,环环相扣,总不离于本题。从横的方面看:写周围景物,于所居之东坡则加细,说及一夜至晓的春雨、新晴;对西南诸景则只大略点出泉、溪、亭、丘,似零珠之散,合之则俨然是一幅东坡坐眺图,总归到“都是斜川当日景”之内,诚亦“至今使人想见其处”。以似斜川当日之景,引出对斜川当日之游的向往,对陶《游斜川》诗结尾所云“中觞纵遥怀,忘彼千载忧;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当亦冥契于心。苏轼对付逆境有自己的特殊态度。他对生活有信心,善于从个人痛苦情绪中解脱出来,很快适应环境,将生活安排得很好,随遇而安。从这首词里也侧面反映了他与险恶环境作斗争的方式:躬耕东坡,自食其力,窃比渊明澹焉忘忧的风节,而且对谪居生活感到适意,怡然自乐,令政敌们对他无可奈何。苏轼有时难免有一点衰迟之感,却也留心着局势的变化,注意保存自己,不久神宗皇帝死后,哲宗即位,他又起复,积极从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