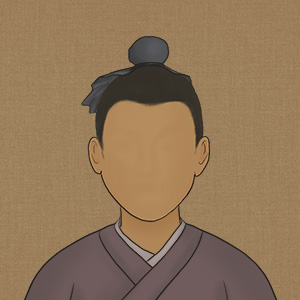这首诗写诗人在旅途中雾中行舟。语言朴实而自然,读来令人有身历其境之感。
首联总写大雾弥漫的景色,既描写晨雾之大,又点出了水、山、天。而山光水色,正笼罩于浓烟密雾之间,隐而不见,眼前唯一能见的只有大雾。作者一笔写出了可见的与不可见的,虚实相映,浑然一体。这两句先渲染出一个大的背景,为全诗做了铺垫。
山水景物,都隐藏在浓雾中,暝暝不可见,因而视觉无所可用,但听觉却转而分明。嗷嗷猿啼,淙淙濑流之声,自漫漫浓雾中传来,宛如空谷足音,显得格外震动耳骨,引人注意。“听”、“闻”、“忖”、“知”四字,用得次序井然、章法严密,细腻地表现了雾中之人凭籍冥冥之间的声音,进行揣度和判断的心理过程。隐而不见的岫峦和川流,便借助听觉的作用,转变为视觉形象,呈现于雾中人的眼前。正由于只可以借助听觉加以想象,而不能直接通过视觉以明见,这岫峦和川流,便增添了几分迷离恍惚、神秘莫测的色彩,别有一番魅力。
颈联紧紧承接上文,进一步写出了人在雾中,迷茫彷徨,茫然不知所之的真切感受。雾中的渔人、行舟,宛如飘浮于浩渺云间,左右前后,无所依傍,恍然惚然。澳浦虽近在咫尺,渔人却迷惑不知;扁舟欲上下沿沂,却茫然不得其所。作者在这里既把雾的气氛渲染得淋漓尽致,同时又将人的迷茫惶惑心境展示得细腻入微。
尾联诗人笔锋一转。一个“尽”字,下得干净利落,浓云密雾,一扫而空。阳光普照,天水清澈,全诗的境界焕然一新。“澄鲜”二字,说明雾后的山水给人以格外清澄透彻、鲜明醒目的感觉,同时也表现了舟中之人自雾中脱出,精神为之一振,豁然开朗了的心情。这结尾二句与开头二句照应得十分紧密,“氛霭”对应“雾”、“烟”,“空水”承接着“水”、“天”,“澄鲜”对照着“冥冥”,首尾呼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首写雾的诗,作者不用“蛇游”、“豹引”、“漱水”、“吹沙”之类古人写雾习用的典故套语,也并不着力于对雾的形态本身作对比描绘,而是以白描的语言,紧密结合人在雾中的感觉和体验来展示雾中的景物,表现雾的氛围,因而读者仿佛也被带入了弥漫着水雾山烟的意境,与诗人一道去体验那浓雾之间的山水、川岫、猿声、濑声,获得了非常真切的感受。这确是一篇写雾诗的佳作。全诗语言自然流畅,不事雕琢,而其格律和对仗,却几乎暗合了唐人五律的要求。
《梁书·伏挺传》谓伏挺“为五言诗善效谢康乐体。”他的诗作流传至今的仅此一首。但就这首诗而论,不仅句佳,而且全诗的意境亦统一完整,其成就看来,并不在谢灵运某些诗作之下。
上片以姑射山上的仙子相比拟,“冰雪透香肌。姑射仙人不似伊。”在词人眼中,爱妻闰之的肌肤像冰雪一般洁白细嫩,而且随时散发着微微香气,有如神话中姑射山中的神女,但是神女似乎还赶不上闰之的美貌。“不似伊”三字,倾尽了词人对闰之的钟爱之情。下文则从内在品格上着力渲染闰之的勤俭质朴,但却不直接说出,而是从她穿着打扮的外表上落笔,显得句法生新:“濯锦江头新样锦,非宜。故著寻常淡薄衣。”在濯锦江边生产着各种花样翻新的锦缎,但是,这对闰之是不适宜的,她平时所穿的都是些寻常的淡薄衣衫。词人在后来写的《祭亡妻同安郡君文》中曾这样高度评价闰之的品德道:“妇职既修,母仪甚敦。”可见,闰之是一位具有传统美德的妇女典型,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使词人对闰之的感情愈加笃厚。
下片进一步描绘王闰之的清心寡欲和雍容睡态,愈加令人惜爱。“暖日下重帏。春睡香凝索起迟。”而下文“曼倩风流缘底事,当时。爱被西真唤作儿。”则转向了词人自己,他以西汉风流才子东方朔自喻,说他当时热恋着王闰之。末句是用《汉武内传》典,以此末句之“爱被西真唤作儿”,显得极其生动亲切。“儿”字是一种亲昵之称,从西王母神仙口中唤出,不仅活灵活现,犹如目前,而且抬高了词人存在的现实价值,颇有自许傲世的味道。再从《汉武内传》叙述东方朔的毕生才干和曲折遭际来看,似蕴含了词人的身世之感,正影射出曾在朝中反对新法而屡遭贬谪和“补外”的坎坷经历。由于他的反变法是光明磊落的,是“此心耿耿,归于忧国”的,故他有着自信、自傲的心态。这也符合词人“外迁”任杭州太守时的心绪。
这首词淋漓尽致地刻画了继妻王闰之的外貌形体美和内秀品格美的形象。全词清新婉丽,明净流美,用典寓意,自然高迈。
这是李商隐作幕梓州后期之作,为咏梅而寓意之诗。写在百花争艳的春天,寒梅早已开过,所以题为“忆梅”。
一开始诗人的思绪并不在梅花上面,则是为留滞异乡而苦。梓州(州治在今四川三台)离长安一千八百余里,以唐代疆域之辽阔而竟称“天涯”,与其说是地理上的,不如说是心理上的。李商隐是在仕途抑塞、妻子去世的情况下应柳仲郢之辟,来到梓州的。独居异乡,寄迹幕府,已自感到孤孑苦闷,想不到竟一住数年,意绪之无聊郁闷更可想而知。“定定住天涯”,就是这个痛苦灵魂的心声。定定,犹“死死地”、“牢牢地”,诗人感到自己竟象是永远地被钉死在这异乡的土地上了。这里,有强烈的苦闷,有难以名状的厌烦,也有无可奈何的悲哀。屈复说:“‘定定’字俚语入诗却雅。”这个“雅”,似乎可以理解为富于艺术表现力。
为思乡之情、留滞之悲所苦的诗人,精神上不能不寻找慰藉,于是转出第二句:“依依向物华。”物华,指眼前美好的春天景物。依依,形容面对美好春色时亲切留连的意绪。诗人在百花争艳的春色面前似乎暂时得到了安慰,从内心深处升起一种对美好事物无限依恋的柔情。一、二两句,感情似乎截然相反,实际上“依依向物华”之情即因“定定住天涯”而生,两种相反的感情却是相通的。
“寒梅最堪恨,长作去年花。”三、四两句,诗境又出现更大的转折。面对姹紫嫣红的“物华”,诗人不禁想到了梅花。它先春而开,到百花盛开时,却早花凋香尽,诗人遗憾之余,便不免对它怨恨起来了。由“向物华”而忆梅,这是一层曲折;由忆梅而恨梅,这又是一层曲折。“恨”正是“忆”的发展与深化,正像深切期待的失望会转化为怨恨一样。
但这只是一般人的心理。对于李商隐来说,却有更内在的原因。“寒梅”先春而开、望春而凋的特点,使诗人很自然地联想到自己:少年早慧,文名早著,科第早登;然而紧接着便是一系列不幸和打击,到入川以后,已经是“克意事佛,方愿打钟扫地,为清凉山行者”(《樊南乙集序》),意绪颇为颓唐了。这早秀先凋,不能与百花共享春天温暖的“寒梅”,正是诗人自己的写照。诗人在《十一月中旬扶风界风梅花》诗中,也曾发出同样的感叹:“为谁成早秀?不待作年芳。”非时而早秀,“不待作年芳”的早梅,和“长作去年花”的“寒梅”,都是诗人不幸身世的象征。正因为看到或想到它,就会触动早秀先凋的身世之悲,诗人自然不免要发出“寒梅最堪恨”的怨嗟了。诗写到这里,黯然而收,透出一种不言而神伤的情调。
五言绝句,贵天然浑成,一意贯串,忌刻意雕镂,枝蔓曲折。这首《忆梅》,“意极曲折”(纪昀评语),却并不给人以散漫破碎、雕琢伤真之感,关键在于层层转折都离不开诗人沉沦羁泊的身世。这样,才能潜气内转,在曲折中见浑成,在繁多中见统一,达到有神无迹的境界。
第一联“幸自同开俱阴隐,何须相倚斗轻盈。”写牡丹“同开俱阴隐”,不必“相倚斗轻盈”,这是指牡丹花之间同开俱隐约,还是以牡丹与别的花相比较,并未言明。从诗意看,似指牡丹花之间可能性为大。“幸”字流露了作者担心、紧张情绪。“何须”则是劝告语气,正应“戏题”二字。这联写了牡丹同开俱隐约,又写了它们之“斗轻盈”。“阴隐”“轻盈”写牡丹的神态,但这并不轻松。这一联里显然凝聚着韩愈内心探处的难言之隐。清黄叔灿《唐诗笺说》认为“有比意”。究竟是比官场中人事纠葛,还是仕途升腾降落,难以探究。总之,韩愈似乎是将自己感慨寓于其中了,因而就格外有韵致。
第二联“凌晨并作新妆面,对客偏含不语情。”就牡丹的神态作进一层描绘。“并作”仍强调同样的特征,同上联“同”、“俱”呼应,更说明斗轻盈的不必要。是上联旨意的形象论证。晚唐罗隐《杜丹花》诗写道:“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亦动人。”确实可以看是受韩诗的影响,不过相比之下,韩的“对客偏含不语情”更含蓄别致,有回味的余地。再加上或许含有某种隐情于其中,就更引人入胜了。
“双燕无机还拂掠,游蜂多思正经营”一联描绘了牡丹花开之后燕舞蜂忙的嬉闹场面。实际也是渲染了牡丹花所处的环境。就牡丹自身而言,“斗轻盈”就已经具有人格意识,“新妆面,不语情”就更强化了这种意识,这都是从牡丹本体出发,自然显现,而双燕、游蜂作为牡丹的身外之物也频频关照、时时拂掠、苦苦经营,而作为牡丹自身却又有念想。诗人似乎无意涉及,也就不必探究其中是不是藏有微言大义。单就艺术描写角度看,写出了牡丹花的艳丽姿态,及其繁华场面,有很强吸引力,显示了作者深厚语言工力非同寻常。而最后“长年是事皆抛弃,今日栏边眼暂明”就很清楚表露了作者见牡丹而心喜,忘却多年尘俗之事的愉悦之情。清汪佑南《泾草堂诗话》就认为晚唐诸家咏牡丹“尽态极妍,总不如昌黎一首”,似乎有些过份,因诸家所咏自有其特点自有其角度,不能一概而论,但就艺术上的“轻清流丽,无意求工”这一点说,却道出了韩愈这首咏牡丹诗的特色。而这一特色,恰恰是韩愈将自己心理感受注于诗中所致。清张鸿《批韩诗》认为这首诗有韩愈“不著色”的体格,确是一语中的。较之那些浓彩重饰只求形似的咏牡丹之作,韩愈这首《戏题牡丹》还是充满神韵的。它不仅显示作者驾驭语言的工力,描绘了牡丹的丰采,而且,在“戏”的背后,似乎也含有严肃的命题。这才是韩愈这首诗被评诗家称道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