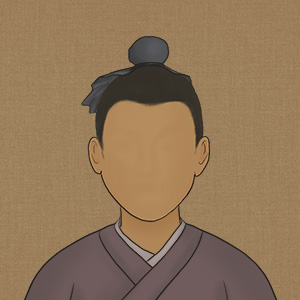据宋人洪迈《夷坚志》记载:侯蒙其貌不扬,年长无成,屡屡被人讥笑。有轻薄少年画其形容于风筝上,侯蒙见之大笑,作《临江仙》词题其上。后一举登第官至宰相。
假如有人把你的相貌绘于风筝之上,即使你相貌英俊,恐怕也不会高兴,或许要勃然动怒,或者告他个侵犯肖像权或者恶语相向或者诉诸武力了。然而侯蒙却没这样做,他不但不动怒,还见之大笑,并为此写了一首词,题写于风筝之上,可见侯蒙绝非一般人物。
绝非一般人物的侯蒙写的词又如何呢?
这首词用了托物言志的手法,借风筝来写诗人个人的志向、意愿和理想。
未遇行藏谁肯信?是自问亦是自答,自己其貌不扬,又年长无所成就,谁又能了解自己呢?世上的人有谁不以貌、以权、以钱取人呢?人们看到的都是外在的东西,内在的修养才学志向抱负谁又能看到呢?不为人理解相信当然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不知是幸还是不幸,诗人的名声却一下子显扬起来,原来不知是哪个画家把他的形象绘制于风筝上,他也就随着风筝飞上了天空。
“当风轻借力,一举入高空”,是写风筝也是写诗人的志向。诗人明明白白的正告我们,风筝只有在有风的时候才能飞上天空,如果没风,任谁风筝也飞不起来。一个人在社会上有成或者无成何尝不是如此呢?才能当然是一个方面,但机遇也必不可少,如果没有机遇,没有可以借力的风,即使一个人再有才华,也不可能有所成就。世上的人们,你们只知道我在地上的样子,和你们似乎一样;但你们要知道,一旦风起,那临风飘举就是我!诗人借风筝却写出了“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大鹏的志向。
才得吹嘘身渐稳,是写风筝已飞上天空迎风飘举的样子;只疑远赴蟾宫,是诗人借风筝来表明自己的志向,那就是去“蟾宫”折桂,成就自己的功名事业。雨余时候夕阳红,是写雨过天晴,傍晚时分夕阳无限红。风雨是自然界的风雨,同是也是诗人所遭受的人生的风雨。阳光总在风雨后,风雨之后,属于自己的阳光终究会到来,哪怕来得晚一点,但诗人始终坚定的相信,他终将会大器晚成。
几人平地上,看我碧霄中。表面是写绘有诗人形象的风筝飞翔于碧空之中,平地上人们都在观看;其实是借风筝飞翔碧空来表达自己的不凡志向。正如《红楼梦》中贾雨村借月亮来表达的自己志向的诗句“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一样,诗人要表达也是同样的志向。
或许我们今天看似一样,但谁又能知道明天会如何呢?明天,就在明天,我们也许就会判若霄壤,因为你们是“翱翔蓬蒿之间”的蜩与学鸠,而我则是“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大鹏;你们是庸庸碌碌的凡夫俗子,而我则是志向高远的豪杰之士。
非豪杰之士不能写出豪杰之词,此词便是豪杰之士写的豪杰之词
“夜深风雨撼庭芭,唤起新愁乱似麻。”两句是说夜深了,窗外的风雨,正摧撼着院子里的芭蕉。这声音萧萧瑟瑟,唤起了诗人纷乱的新愁。他是在梦中惊醒的,清冷的环境,忧郁的愁思,使他有心绪如麻之感。
“梦觉尚疑身似蝶,病乱方悟影非蛇。”句写的是梦醒以后心情恍惚的情况。梦醒了,自己还在疑心此身已经化成蝴蝶;病是刚刚好转的,这才悟到先前怀疑的影子并非是射影。从虚幻到觉醒,本是病乱梦醒以后常见的心理状态。作者是一个正直的文人,也是有志之士。他之所以有这种心理情态,显然是含有对时事的忧虑。不过在诗句中没有直接点明而已。
诗的第五六句:“浇肠竹叶频生晕,照眼银釭自结花。”写的是排愁自遣之情。“竹叶”,自然是指酒,诗人想借酒浇愁,酒还未入愁肠,脸上已经频频泛起了酒晕。他坐对荧荧照眼的灯光,这灯芯上已经结上了灯花,灯花是报喜的,然而此刻哪有什么可喜的事呢?只好任其自由结花吧。这两句可见作者是盼望有遣愁的机会和可以舒怀的喜讯的。但就是这点心愿,在当时也难以实现。
正在清愁难遣的时候,作者忽然听到杜鹃鸟的啼声,于是他感慨万千地写下了结句:“我在故乡非逆旅,不须杜宇唤归家。”杜宇就是杜鹃,它的啼声是“不如归去”,一般有家归未得的人听了之后,会触动思乡之情,作者此时身在故乡,并非旅居在外,所以感叹的说:我并没有离开故乡,不需你唤“不如归去”,劝我回家了。作者有志用世,但当时是豺狼当道,善类遭受摧残陷害的不知多少,作者只好郁郁家居。因此最后两句,才点明胸怀,倾诉出报国无门、壮志难展的感慨。
全诗即景抒怀,从深宵风雨到午夜一灯;从梦觉以后的清愁,到听得杜宇啼声所引起的悲愤;步步深入,诗人的心境,自见于诗句之中。直到秦桧死后,诗人才出而应试,以经学淹通被选拔为第一,解除了长期以来内心的痛苦。
首联开门见山,点出本诗基调:无法参禅得道,心中的不平亦不能自抑。一个“只”字仿佛自嘲,实是发泄对这个世界的不平。仙佛茫茫两未成,只知独夜不平鸣。不平鸣,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言也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自己成仙成佛的道路渺茫,都无法成功,只能在深夜独自作诗,抒发心中的不平。
风中飞蓬飘尽悲歌之气,一片禅心却只换得薄幸之名。宋道潜诗有云:“禅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风上下狂。”如此清妙之音被作者如此化用,倒成了牢骚满腹的出气筒。风蓬飘尽悲歌气,泥絮沾平薄幸名。风蓬,蓬草随风飘转,比喻人被命运拨弄,踪迹不定。泥絮,被泥水沾湿的柳絮,比喻不会再轻狂。薄幸,对女子负心。飘泊不定的落魄生活,把诗人诗歌中慷概激昂之气消磨而尽。万念俱寂、对女子已经没有轻狂之念的人,却得到负心汉的名声。
颈联更是狂放愤慨:世上的人十之八九只配让人用白眼去看,好似当年阮籍的做派;“百无一用是书生”更是道出了后平书生的酸涩心事,此句既是自嘲,亦是醒世。
尾联说不要因为诗多说愁,成了谶语,春鸟与秋虫一样要作声。不是只能作春鸟欢愉,秋虫愁苦一样是一种自然。此句传承以上愤慨之气,再次将作者心中的不平推至高潮。莫因诗卷愁成谶,春鸟秋虫自作声。
黄景仁短暂的一生,大都是在贫病愁苦中度过的。他所作诗歌,除了抒发穷愁不遇、寂寞凄苦的情怀,也常常发出不平的感慨。七言律诗《杂感》就是这样的一首诗。
这首诗首四句忆昔,叙述绿珠初进石家并倍受石崇的怜爱;次四句指出绿珠悲剧命运的根本原因;最后四句,紧承前诗,叙写绿珠的惨死,语言中充满悲愤。全诗虽咏绿珠,实则借以抒发诗人对其侍婢窈娘的爱恋和对武承嗣的怨愤。诗分三节,每四句一节,意随韵转,语调慷慨激昂,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前四句叙述绿珠入金谷园,得到石崇宠爱的情事。像石崇这样的巨富,出于对声伎的爱好,“明珠十斛买娉婷”本是常事;但在这里,着意表现的并非其一掷千金的豪举,而是石崇对自己的重视和赏爱。
“此日”二句,将一个普通下层歌女的可娉可爱,由外表到内心,都加以生动展现。这两句分别从不同角度表现了男女双方对爱情遇合的热烈感情。复沓的句式加强了感情的表达。君怜我而我亦感君,正是日后以身相殉的感情基础。
中间四句叙写权豪势力横加压迫,强取豪夺。先说石崇对自己闺中的声伎并不秘藏,常将歌妓舞女的才艺展示给外人观赏。而这,正成了致祸的直接根由,招致了“骄矜势力”的横加干求索要。这里用“意气雄豪”“骄矜势力”“非分理”“横相干”等一系列感情色彩强烈的词语,揭示出权豪势力的骄矜自得、专横无理、气焰熏天的丑恶凶暴面目。表面上指孙秀,实际上指当权的武承嗣,字里行间,充满了强烈的怨愤之情。
最后四句,写绿珠不忍辞石崇而去,决心以身相殉。 两用“君”字,如面对石崇哀愤呼告。接着用“终不忍”一笔兜转,展示出内心万难割舍的深情。尽管不忍离去,却又无法违抗,只能空自掩面饮泣,泪湿铅粉而已。去既不忍,留亦无法,只有以身相殉。
末二句是绿珠坠楼前的内心独白,是誓死忠于爱情、反抗强暴的宣示。“百年离别”,即使最相爱的情侣之间,也终有离别之时,但这离别却因横暴势力的“相干”不得不“在高楼”演出这极惨烈的一幕,却是惊心动魄的悲剧。既然不能百年相守,只能“一旦红颜为君尽”,用死来表明对所爱者的忠贞,对横暴势力的反抗了。“百年”与“一旦”鲜明对照,将誓死相殉的感情表现得更加强烈。这个结尾,是全诗感情的结穴和高度凝聚,沉痛愤激,直截决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