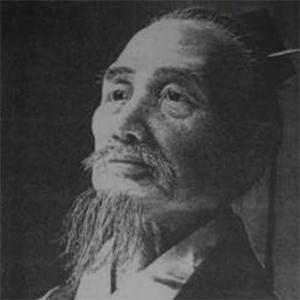这是一首送别词。上片写送别的情景。词人的朋友宇文德和被召赴行在所,词人为他饯行,坐在榕树之阴,痛饮美酒,以壮其行。二人依依难舍,全然没有顾及到叠鼓频催,促人登舟。二人一直饮到暮色苍茫新月已经悄悄地徘徊于山巅。离愁缕缕,有如秋水,二人不忍遽别。友情之深,留恋之意尽在不言之中,场面由热烈而渐次清静,又为二人留下许多畅叙衷肠的机会。由月上暮山,到次日天明,晓帆将开,二人皆已醉意朦胧,纵然难舍,也到了不得不分手的时候。
换头,化愁为慰,友人被召赴行,词人对他寄予殷切的希望,也许可以为抗金贡献力量,现在友人全家都欢欢乐乐地走了,江上行船要忘掉一切疑虑,江边的鸥鹭也不要猜疑。最后他借苏轼鸿雁归来的典故说明南宋朝廷的形势是好的,此去也许会一帆风顺。词人和他的友人都是主战派,当时秦桧之流为了卖国求荣,陷害了许多爱国大臣,鉴于宇文德和被召、吉凶未卜,尚有隐忧,故词人写词鼓励他、宽慰他,同时也把抗金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词人襟怀坦白,眼界开阔,忧国之意常现于笔端,虽为送别之词,却未写一般的离愁别绪,政治上的志同道合使全词充溢着浩然正气和豪放之情。
这首诗描述的主要是诗人思亲、见亲的全程心灵感受,言语易懂,感人至深。
首二句说妻儿们去远了,相见无期,也就不那么惦记了;而当归期将近,会面有望,则反而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去远”句固然是记录了诗人的实情,然而也深刻地表现了他无可奈何的失望和悲伤,诗人决非真的忘情于妻儿,而是陷于一种极度的绝望之中。“归近”一句正说明了他对亲人不可抑捺的情愫。
“儿女”二句写初见面的情形。因离别四年,儿女面目已不可辨认。陈师道的《送外舅郭大夫概西川提刑》中说:“何者最可怜,儿生未知父。”可见别时儿女尚幼,故至此有“眉目略不省”的说法,表明了离别时间的长久,并寓有亲生骨肉几成陌路的感喟。
“喜极”二句是见面之后复杂心情的表现。久别重逢,惊喜之余,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只是相顾无言,泪洒千行,然后破涕为笑,庆幸终于见面。此十字中,将久别相逢的感情写得淋漓尽致,诗人抓住了悲喜苦乐的矛盾心理在一瞬间的变幻,将复杂的内心世界展现出来。
“了知”二句更深一层作结,说虽然明知不是在梦中相见,但犹恐眼前的会面只是梦境,心中仍然恍恍惚惚,不能安定。这种心理的描绘,写得入木三分。由此可以推知:在与亲人分离的四年中,诗人多少次梦见亲人,然而却是一场空欢喜,反增添了无限的愁思和悲苦,正因为失望太多,幻灭太多,所以当真的会面时,反而产生了怀疑,唯恐仍是梦中之事,深沉的思念之情便在此中曲折表现了出来。这两句源于杜甫《羌村》组诗中写回家初见亲人的惊喜和疑虑:“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意谓久别重逢,如相见于梦中,后来司空曙《云阳馆与韩绅宿别》中“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即用杜甫诗意;而陈师道此二句是翻用杜甫诗的句子,与晏几道《鹧鸪天》中所说的“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意境略同,可见陈师道取前人诗意能点化出新意。
此诗通篇造语质朴浑厚,无矫饰造作之气,读来恻恻感人,其原因主要在于诗人感情的真挚,语语皆从肺腑中流出,所谓至情无文,即是艺术上一种极高的境界。此类浑朴的作品得力于陈师道向古乐府和杜甫诗的学习,然而他并不在字句上摹仿前人,而在格调立意上倩鉴前人,故张表臣在《珊瑚钩诗话》中引陈师道的话说:“今人爱杜甫诗,一句之内,至窃取数字以仿像之,非善学者。学诗之要,在乎立格、命意、用字而已。”这在他自己的作品中已有充分的表现。陈师道论诗标举“宁拙毋巧,宁朴毋华”(《后山诗话》),即是他形成这种创作风貌的理论基础。但此类作品在他的集子中也并不很多,故尤为珍贵。
陈师道论诗,提倡“宁拙无巧,宁朴无华。”(《后山诗话》)此诗就是朴拙无华而感人肺腑的好诗。说它朴拙,因为全诗没有典故,没有藻饰,章法平直,句法简洁,并不追求文外曲致。说它感人,是因为字里行间洋溢着至性至情,深挚敦厚,绝无造作虚饰。然而此诗虽不炼句而炼意:首联写久别重逢之情极为生动,尾联则活画出疑信参半之心态。用极简洁的诗句刻画出复杂深微的感情,所以耐人回味。
陈师道做诗追求古朴,讲究锤炼,自称“此生精力尽于诗”,黄庭坚《病起荆江亭即事》也有“闭门觅句陈无己”句,因此,他的诗往往枯涩生硬。这首诗纯是写情,凝练精到,表现了骨肉至情,是他诗中上乘之作。
“元日”,即农历正月初一。
“五更”两句,写一年复始,一切都趋于清静无为的状态之中。言在元旦的凌晨,卧槽之马在寂静地休息着,邻家的打更鸡,也象是在怕要惊醒人们的好觉似的,不再打鸣。“日华”两句,概述一天变化。言拂晓时太阳出来了,跟着似乎春天也降临到了人间,万物开始清明复苏,然而到了入暮时分残寒侵体,又使人感到了一种无明的忧愁。上片是概述自己元日之中的一天感受,及心情的变化。
“新岁梦”三句,写己之醉梦至醒的过程。言元旦清晨的好梦,是对去年的眷恋之情。而自己在除夕夜所饮的酒,过了一夜如今也已半醒过来。“春风”两句,醒后见闻。言柔和的春风在轻轻地飘东拂西,将梅花瓣缓缓地送至地面。忽然听到从驿亭那边传过来几声孤雁的凄鸣声,不由使人感到了一种孤独中的悲哀。下片述己孤身度日的无聊情状。
全词娓娓而谈,笼罩着一种淡淡的哀伤。
此词题为《春晚》,实写“闺情”。“春晚”之时,深闺女性自有难以明言的复杂情怀,但作者并非女性,没有高超的水平,对于那种连作者本人都难以明言的情怀是不可能写得生动感人的。
读完全词,就知道作者并未让那位闺中人吐露情怀,而是通过精细的观察,写她的神态、写她的妆束、写她的行动,并用富贵人家的花园、香径、秋千和晚春景色层层烘托,其人已宛然在目,其心态变化,也历历可见。灵活地运用传统画法,把“以形写心”和“以景传情”结合起来,乃是这首小词最突出的艺术特色。
“态浓意远”,原是杜甫《丽人行》中的成句,用以表现丽人的姿态凝重、神情高雅,其身份也于此可见。“眉颦笑浅”,写她虽愁也只略皱眉头,虽喜也只略展笑颜,非轻浮放纵之流可比,其教养也于此可见。“薄罗衣窄絮风软”,既写服妆,也写时光。北宋诗人蔡襄《八月九日诗》:“游人初觉秋气凉,衣不禁风薄罗窄。”而当“絮风”轻“软”之时,正好穿那窄窄的“薄罗衣”。“罗”那么“薄”,“衣”那么“窄”,其轮廓之分明,体态之轻盈,已不言而喻。徐步出闺,迎面吹来的是飘荡着朵朵柳絮的软风,不知她又有什么感触。“鬓云欺翠卷”一句,颇难索解。如果把“翠卷”看作“欺”的宾语,那它便是一个名词,可是实际上并没名叫“翠卷”的东西。那个“翠”字,看来也取自杜甫的《丽人行》。《丽人行》写丽人“头上何所有?翠为盍叶垂鬓唇。”是说用翠玉制成的盍叶垂在鬓边。盍叶,是妇女的一种头饰。“鬓云欺翠卷”就语法说,“鬓云”是主语,“卷”是谓语,“欺翠”则是动宾结构的状语,修饰“卷”。“欺”,在这里是“压”或“淹没”的意思,“翠”,即指翠玉制的盍叶。全句写那位女性鬓发如云,“卷”得蓬松而又低垂,以致淹没了盍叶。
下片头两句似乎单纯写环境、写景物,实则用以烘托人物。第一句是说她走到“南园”,看见“花树春光”,而且感到“暖”。第二句是说她漫步于“南园”的“径里”,看见片片飞红,嗅到阵阵花香,踏着满径榆钱。上片的“絮风”和下片的“春光暖”、“榆钱满”,都传送春天即将消逝的信息,既点《春晚》之题,又暗示女主人公由此引起的情感波澜。韶华易逝、红颜易老,但她还是孤零零的,偶然走出深闺,来到“南园”,也无人同游共乐。
结尾两句,层层转折,曲尽女主人公的心理变化。“欲上秋千”,表明一见秋千,又唤回少女的情趣,想荡来荡去,嬉笑作乐。“又惊懒”,表明单身独自,没有心情打秋千。“惊”字、“懒”字,用得十分神妙。“欲上秋千”而终于不想上,并非由于“懒”,偏不肯说出真实原因而委之于“懒”,又加上一个“惊”字。是说连秋千都不想上,竟“懒”到这种地步,自己都感到吃惊。不想打秋千,就归去吧。“且归”一顿,而“休怕晚”又是一层转折。实际情况是想玩又懒得玩,且归又不愿归。深闺那么寂寞,归去也没有意味。于是在“且归”的路上,思潮起伏,愈行愈缓。妙在仍不说明真实原因,仿佛她迷恋归途风光,在家庭中也很自由,回家甚“晚”,也不用“怕”。
这首词把封建社会中一位深闺女性的内心苦闷写得如此真切,不独艺术上很有特色,其思想意义,也是积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