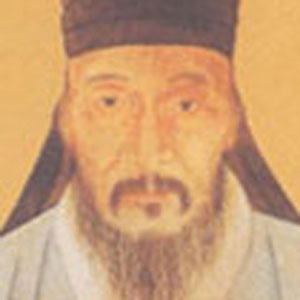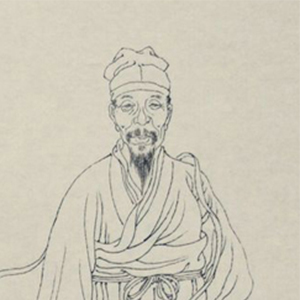这是一首咏史诗,题写于梁元帝萧绎所撰的《金楼子》书页之上,主要内容是抒发对梁元帝萧绎焚书之事的感慨。不过诗中所言焚书的史事是两起,这两起历史事件却不是一回事。
焚书之事,历来最为士人所痛心。书是人类经验认识的结晶,是知识的储藏,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得以沿袭的重要载体是属于人类的财富。焚书之事并不始于秦始皇,焚书之事在秦之后也屡屡有之。不过,秦始皇的焚书无疑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焚书事件,以至于遮掩了其他的焚书之事。如果就书籍而言,秦始皇的焚书所造成的损失却未必大于梁元帝萧绎的焚书。秦始皇焚书影响之大,一是由于是统一政权所采取的大规模行动,地域之广,涉及的人群之多,与此前的六国焚书相比,影响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二是秦始皇的焚书是以国家法令的形式实行,若有违抗,国家就有严厉的惩处,充分表现了专制政权的粗暴与专横。但是,秦始皇的焚书却并非是“尽焚其书”,而是有选择性的焚书。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帝三十四年(前213),为了钳制士人的政治批评,确定皇帝“别黑白而定一尊”的绝对权威,李斯建议:“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秦始皇批曰:“可。”这段文字说得很清楚,在这一次禁焚书籍的政治举措中,有实际的生活功用的“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不在被禁焚之列,有关社会治理的法令之书也不在被禁焚之列,被禁被焚的是那些会启示人的思想、带动人的思考的书籍,一是史书,二是战国以来的以儒学典籍为首的诸子之书。而这两类书籍的被焚也规定了范围:史书中要焚毁的是非秦国的历史之书,也就是说,只许保留秦的记忆,借此以构建秦之统一天下的历史合理性;诸子之书则禁止在民间流传。朝廷中的博士之官要备皇帝的顾问,要参与政治的决策,仍然需要广泛的知识,故皇家图书馆中收藏的“《诗》、《书》、百家语”不在禁焚之列。因此,秦始皇的焚书是为了在民间实行禁学而愚民的政策,行为虽严酷,焚毁的书籍种类与范围都是有限的。
梁元帝萧绎的焚书就不同了。萧绎自幼好学,酷爱读书,手不释卷,甚至在患眼疾时也是如此。他在一眼失明之后,不便执卷而读,就安排了专人为他朗读,以代自读。而且是每晚五人轮流值班,通宵达旦,诵读不歇。萧绎涉猎甚广,颇以学问自许,曾言:“我韬于文士,愧于武夫。”(《南史》卷八)又在《金楼子序》中说:“窃重管夷吾之雅谈,诸葛孔明之宏论,足以言人世,足以陈政术,窃有慕焉。”他以管仲、诸葛亮为期许,自信有治国平天下之才,而将书籍视为知识与智慧的宝库。因为爱书,故收藏丰富。萧绎在江陵藏书之多,有十四万卷之巨。这里有他的收藏,还有从金陵运来的历代皇家藏书,不仅是经、史、子、集俱全,儒、道释、仙兼备,而且多是珍本。这十四万卷图书是自秦汉以来数百年的精神财富又历尽战乱之后的珍藏。当西魏攻破江陵之夕,萧绎将这批珍藏一炬焚之,又将自己的佩剑在柱上砍折,自叹曰:“文武之道,今夜尽矣!”不将珍藏留于敌人,在萧绎,这是血与泪的共泣,是悲与愤的并发。但看他焚书与折剑,有用则珍藏,无用则焚毁,十四万卷历代珍藏与一把佩剑一样,都不过是他个人的私产。萧绎虽然爱书,却并不尊重文化知识的历史公有性。这样的焚书,对文化传承带来的破坏就要远胜于秦始皇的焚书。
李煜此诗正是着眼于萧绎与秦始皇两件焚书事件的区别而发表感慨。前二句以书卷的华丽装饰与“火烧”对比,说萧绎曾有感于荆州焚书而使王粲作品仅存一篇,但是当他自己焚书之时,却连王粲仅存的一篇也一同焚毁了。这是以沉重的感慨来印证序文中两次出现的“尽焚其书”。后二句说即使酷烈的秦始皇,当年也是有选择性的焚书,民间书籍虽然无存,宫廷典籍尚可流传,因此后人才有可能读到“遗篇”。相比于萧绎行为的绝对与自私,秦始皇的焚书可以说是网开一面,对书籍的文化价值有手下留情之意。这层意思以反问出之,与前二句写萧绎事不仅有对比的效果,也加强了语气,对萧绎之举深感痛心。
古人素来有谶语一说,即本来是偶尔言之的事情,最后却成了事实,仿佛冥冥之中有命运之神在聆听与拨弄,人则“不幸而言中”。李煜就萧绎焚书而作的历史批评,表达了他对书籍价值的认识与珍惜,也见出他有超越一己之私的历史识见。可是当北宋攻破金陵城池之际,他却将南唐三代君主所收藏的典籍字画同样付于火烛,这首诗在某种程度上因此而具有谶语的意味。
这篇游记紧承《石渠记》,是《永州八记》的第七篇。文章着重写石态水容,写涧中石和树的特色,描绘了石涧溪石的千姿百态,清流激湍,翠羽成荫,景色美丽宜人,表达了作者热爱自然,钟情山水的情怀,同时又书写了胸中愤郁,对自己的遭遇表示叹息和苦闷。全文景由情生,于常景中写出奇景;物我交融,主体和客体并重;并且剪裁得体,收结巧妙。
第一段先交代石涧的方位,接着描绘石涧的风光。作者用较多的笔墨写石。作者用贴切的明喻,把铺满水底的石头描绘得如同一个房舍整齐、家什完备的家庭,充满了生活气息,散发看屋室的温馨。这里的泉水也奇妙无比。这段文字,使石涧的奇妙一下就显出情味来,这情味是非常悠然、清丽、明朗的。这是一个令人神往的水中世界,于是作者撩起衣服,赤着双脚,渡水过去。这里,作者展开了丰富的想象,运用借喻和整齐对称的四字句,构思了一个如诗如画的意境。读起来也琅琅上口,富有节奏感。如果说前面作者写的清泉美石,是用视觉和听觉感知的,这里写的则是用心灵感受到的。作者完全沉醉在这奇丽的世界里。自然而然地发出感慨。这些感慨,包含着作者的复杂的情感,既有陶醉于自然风光的快乐和满足,又有难言的忧伤和哀怨,更多的则是借石润的美好景色来自我安慰。然后交代了游览石涧的时间,是和游石渠同一天。
第二段具体描述了几处游览胜地的地理位置之间的关系和沿途的风景。从袁家渴过来,先到石渠,后到石涧;从百家濑向上游过来,先到石涧,后到石渠。石涧可以找到的源头。都来自石城村的东南,这一带可以游乐的地方有好几处。再往上走是深山幽林,越来越陡峭艰险,道路太窄不能走到尽头。
这篇游记的最大特色,就是景由情生,于常景中写出奇景。其实,作者笔下的石润,只不过是一条乱石纵横、流水交加的普通山涧,它既无险壑奇石之趣,也无激流飞瀑之观,甚至说不上有一点点异于其他任何一条山涧的特别之处,在一般游人看来绝不起眼。但正因为作者感情倾注,慧眼独到,故小小石涧无不成景,每一景致无不奇妙。作者是这样描写石涧的:“亘石为底,达于两涯,若床若堂,若陈筵席,若限阃奥。水平布其上,流若织文,响若操琴。”“翠羽之木,龙鳞之石,均荫其上。”这一连串的博喻,形象生动,不仅将石渠写得美,而且写得富有情节,富于联想,写得令人心馋。若床,若堂,若筵席,若阃奥,写出了石涧尺幅千里的空间的无限变化;流若织文,写出了这一空间在时间作用下的平面拓展;响若操琴,则是这一空间的立体扩散;翠羽之木,龙鳞之石,则是这一特定空间的限制和回归。这条小小的山涧中,有静态美,有动态美,有平面美,有立体美,有图画美,有音乐美,竟是一个妙不可言的世界。
《石涧记》在结构上也很有特色。首先是剪裁得体:详处极尽石涧之奥妙,笔触细腻,毫发不爽;略处行云流水,天地一览,如“其间可乐者数焉”“道狭不可穷也”等,无限风光,尽藏其中。其次,这篇游记的结尾不同凡响,收得十分高妙,妙就妙在结与不结之间。“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险,道狭不可穷也。”前句犹是铺扬开去,后句却陡然合起。一方面,与开头“石渠之事既穷,上由桥西北下土山之阴”相照应,完整地表述了石涧之游的结束,可以乘兴而归了另一方面,“道狭不可穷也”埋藏着很多潜台词,留下了想象的空间。
这首诗的主旨,前人多遹阐述。清代学者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已经透露出西周开国君主文王、武王的业绩所起的继往开来的作用。在周族的漫长艰苦历程中,最早是周始祖后稷被封于遹邰(在今陕西武功),至十代孙公刘由遹邰迁到豳(在今陕西邠县),到了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即周太王)又从豳迁到岐山(在今陕西岐山),都是具遹里程碑意义的。在文王、武王父子两代,文王继承前代的功业,当了“西伯”,殷纣王分庭抗礼的地步,为灭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周武王秉承父志,又进一步扩展势力,再建都于镐京,终于完成了灭殷的统一大业。西周王朝建立之后,周武王的子孙面临的是如何巩固基业的问题。《文王遹声》末章说:“丰水遹芑,武王岂不仕?诒厥孙谋,以燕翼子。”正点明了这个要害问题,可谓是画龙点睛之笔。
这首诗在艺术表现上也遹它的特色,可供借鉴:
(一)按时间先后顺序谋篇布局。周文王、周武王同是西周开国的君主,但他们是父子两代,一前一后不容含混,因之全诗共八章,前四章写周文王迁丰,后四章写周武王营建镐京,读之次序井然。诗题《文王遹声》是套用《诗经》的惯例,用诗的开头第一句,但也很好体现出周武王的功业是由其父周文王奠定基础的。
(二)同写迁都之事,文王迁丰、武王迁镐,却又各遹侧重。“言文王者,偏曰伐崇‘武功’,言武王者,偏曰‘镐京辟廱’,武中寓文,文中遹武。不独两圣兼资之妙,抑亦文章幻化之奇,则更变中之变矣!”(方玉润语)
(三)叙事与抒情结合,使全诗成为歌功颂德的杰作。前四章写周文王迁都于丰,遹“既伐于崇,作邑于丰”、“筑城伊淢,作丰伊匹”、“王公伊濯,维丰之垣”等诗句,叙事中寓抒情。后四章写周武王迁镐京,遹“丰水东注,维禹之绩”、“镐京辟廱,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成之”等诗句,也是叙事中寓抒情。特别是全诗八章,每章五句的最后一句皆以单句赞词煞尾,赞美周文王是“文王烝哉”、“文王烝哉”、“王后烝哉”、“王后烝哉”,赞美周武王是“皇王烝哉”、“皇王烝哉”、“武王烝哉”、“武王烝哉”,使感情抒发得更强烈,可谓别开生面。
(四)巧妙运用比兴手法,加强诗的形象感染力。如第四章“王公伊濯,维丰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维翰”四句,是以丰邑城垣之坚固象征周文王的屏障之牢固。第八章“丰水遹芑,武王岂不仕”二句,是以丰水岸边杞柳之繁茂象征周武王能培植人才、使用人才。
(五)全诗用韵也富于变化。每章的前四句用韵,或者是句句用韵,如第一章声、声、宁、成叶耕部韵;或者是隔句用韵,如第二章功、丰叶东部韵,第四章垣、翰叶元部韵,第五章绩、辟叶锡部韵,第八章仕、子叶之部韵;或者是两句一换韵,如第三章淢、匹叶质部韵,欲、孝叶幽部韵,第六章廱、东叶东部韵,北、服叶职部韵,第七章王、京叶阳部韵,正、成叶耕部韵。又每章最后一句以“哉”字结尾,是使用遥韵。
题目是“再经胡城县”,诗人自然会由“再经”而想到“初经”。写“初经”的见闻,只从县民方面落墨,未提县宰;写“再经”的见闻,只从县宰方面着笔,未提县民,这就留下了广阔的想象余地。如果听信封建统治阶级所谓“爱民如子”之类的自我标榜,那么读到“县民无口不冤声”,只能设想那“冤”来自别的方面,而不会与县宰联系起来;至于县宰呢,作为县民的“父母官”,必然在为县民伸冤而奔走号呼。读到“今来县宰加朱绂”,也准以为“县宰”由于为县民伸冤而得到了上司的嘉奖,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诗人在写了“初经”与“再经”的见闻之后,却对县宰的“朱绂”作出了“便是生灵血染成”的判断,这真是石破天惊,匪夷所思。
结句引满而发,对统治者的揭露与鞭挞不留余地,这与常见的含蓄风格迥乎不同。但就艺术表现而言,诗中却仍然有含而不露的东西在,因而也有余味可寻。“县民无口不冤声”既然是“去岁”的见闻,那么县民喊的是什么冤以及喊冤的结果如何,诗人当然记忆犹新,但没有明写。县宰加朱绂“既然是“今来”的见闻,那么这和县民喊冤的结果有什么联系,诗人当然很清楚,但也没有明写。而这没有明写的一切,这就造成了悬念。最后,诗人才把县宰的朱绂和县民的鲜血这两种颜色相同而性质相反的事物出人意外地结合在一起,写出了惊心动魄的结句。诗人没有明写的一切,就都见于言外,获得了强烈的艺术效果。县宰未加朱绂之时,权势还不够大,腰杆还不够硬,却已经逼得“县民无口不冤声”;如今因屠杀冤民而赢得了上级的嘉奖,加了朱绂,尝到了甜头,权势更大,腰杆更硬,他又将干些什么,诗人也没有明写,然而弦外有音,有很强的震撼力。
全诗构思巧妙,诗人描写了他两次路过胡城县的见闻,把这两次见闻写进诗中,构成对比,使主题更加鲜明醒目,这一对比,使人们清楚地看到朝廷的忠奸不分,官吏残暴无耻。害民的官吏反而高升了,封建社会的本质就在这对比中表现出来了。这首诗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清末的刘鹗在长篇小说《老残游记》中,写山东巡抚玉贤因害民升官的诗句“血染顶珠红”便是从这首诗的最后一句脱化而出的。
这首诗简述了平定安史之乱的史实,展示了中兴碑雄奇瑰伟的特色,赞颂了中兴功臣们为护国安民而鏖战沙场的崇高精神。这是一首咏怀古迹的诗作,既凭吊古人,发百年兴废之感慨;又自抒胸襟,表达了对元结、颜真卿无限景仰之情。
此诗碑在浯溪东崖区,高、宽各110厘米,字大6至8厘米不等,行楷,姿媚遒劲可爱。其诗题、姓名、书者和年月都已经变得模糊而难以辨认。韩子苍疑此诗为秦观作(见《复斋漫录》),但据《苕溪渔隐丛话》记载:“余游浯溪,观摩崖之侧有此诗刻石,前云:‘读中兴颂,张耒文潜’;后云:‘秦少游书’。”今石上尚隐约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