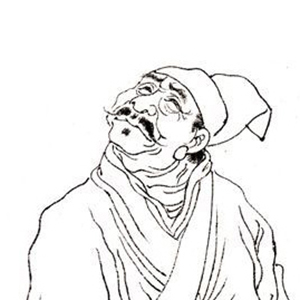苍寒满树黄昏月,碧老孤根太古春。
姑射香薰荷制好,逋仙青入草衣新。
料应不为天风冷,自恐冰肌受点尘。
铁骨槎牙花四五,虬皮封裹晕烂斑。
极知不似君芳洁,也要相依度岁寒。
苍寒满树黄昏月,碧老孤根太古春。
姑射香薰荷制好,逋仙青入草衣新。
料应不为天风冷,自恐冰肌受点尘。
铁骨槎牙花四五,虬皮封裹晕烂斑。
极知不似君芳洁,也要相依度岁寒。
此诗写蜀地一位和尚弹琴技艺之高妙。首联写和尚来自诗人的故乡四川,表达对他的倾慕;颔联写弹琴,以大自然的万壑松涛声比喻琴声之清越宏远;颈联写琴声荡涤胸怀,使人心旷神怡,回味无穷;尾联写聚精会神听琴,而不知时日将尽,反衬琴声之高妙诱人。全诗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明快畅达,风韵健爽,在赞美琴声美妙的同时,也寓有知音的感慨和对故乡的眷恋之情。
“蜀僧抱绿绮,西下峨眉峰。”两句说明这位琴师是从四川峨眉山下来的。李白是在四川长大的,四川绮丽的山水培育了他的壮阔胸怀,激发了他的艺术想象。峨眉山月不止一次地出现在他的诗里。他对故乡一直很怀恋,对于来自故乡的琴师当然也格外感到亲切。所以诗一开头就说明弹琴的人是自己的同乡。“绿绮”本是琴名,汉代司马相如有一张琴,名叫绿绮,这里用来泛指名贵的琴。司马相如是蜀人,这里用“绿绮”更切合蜀地僧人。“蜀僧抱绿绮,西下峨眉峰”,简短的十个字,把这位音乐家写得很有气派,表达了诗人对他的倾慕与敬佩。
“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句正面描写蜀僧弹琴。“挥手”是弹琴的动作。嵇康《琴赋》:“伯牙挥手,钟期听声。”“挥手”二字就是出自这里的。“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这两句用大自然宏伟的音响比喻琴声,使人感到这琴声一定是极其铿锵有力的。
“客心洗流水”,这一句就字面讲,是说听了蜀僧的琴声,自己的心好像被流水洗过一般地畅快、愉悦。但它还有更深的含义,其中包涵着一个古老的典故,即《列子·汤问》中“高山流水”的典故,借它,表现蜀僧和自己通过音乐的媒介所建立的知己之感。“客心洗流水”五个字,很含蓄,又很自然,虽然用典,却毫不艰涩,显示了李白卓越的语言技巧。
“余响入霜钟”也是用了典的。“霜钟”出于《山海经·中山经》:“丰山……有九钟焉,是知霜鸣。”郭璞注:“霜降则钟鸣,故言知也。”“霜钟”二字点明时令,与下面“秋云暗几重”照应。“余响入霜钟”,意思是说,音乐终止以后,余音久久不绝,和薄暮时分寺庙的钟声融合在一起。这句诗写琴音与钟声交响,也兼寓有知音的意思。《列子·汤问》里有“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话。宋代苏东坡在《前赤壁赋》里用“余音袅袅,不绝如缕”,形容洞箫的余音。这都是乐曲终止以后,入迷的听者沉浸在艺术享受之中所产生的想象。“余响入霜钟”也是如此。清脆、流畅的琴声渐远渐弱,和薄暮的钟声共鸣着,这才发觉天色已经晚了:“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几重。”诗人听完蜀僧弹琴,举目四望,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青山已罩上一层暮色,灰暗的秋云重重叠叠,布满天空。感觉时间过得真快。
李白这首诗描写音乐的独到之处是,除了“万壑松”之外,没有别的比喻形容琴声,而是着重表现听琴时的感受,表现弹者、听者之间感情的交流。其实,“如听万壑松”这一句也不是纯客观的描写,诗人从琴声联想到万壑松声,联想到深山大谷,是结合自己的主观感受来写的。
律诗讲究平仄、对仗,格律比较严。而李白的这首五律却写得极其清新、明快,似乎一点也不费力。其实,无论立意、构思、起结、承转,或是对仗、用典,都经过一番巧妙的安排,只是不着痕迹罢了。这种“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自然的艺术美,比一切雕饰更能打动人的心灵。
此词选自《彊村语业》卷一,通过对送春情景的描述,寄托对如暮春般飘零衰弱的时局、身世的担忧,以及对寄书故人的思念。类似题材与寓意在诗词中颇为常见,而此词的特色在于用沉稳、畅健的笔调来表达意绪,形成一种沧桑感。只因这种种寥落、孤寂、凄清的意绪由来已久,才能以司空见惯的沉稳心态来应对、排解。换言之,这种沉稳也正意味种种意绪忧结已深,刻骨铭心了。即如辛弃疾《丑奴儿》所言:“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起句已营造出与通常送春词不同的平静沉稳氛围,似乎春天与白昼在无风无雨的平静中安安稳稳地就过去了。以下三句则是在平稳的掩盖下。暗暗透出种种深层的不安,春风“匆匆染柳熏桃过”,似乎无声无息就飘逝了。而期间被略去的,是其成就又摧折桃柳繁华的过程,正是这种被隐藏的起伏跌宕,暗自酝造愁多少,流露在锦笺凄调中,体现在旧笑新颦中,残留在拆绣池台中。莺燕会在林中迷路,也正因连它们也不能适应周围景色发生了如此迅速的盛衰变化,而书稿半已残缺,则表明这凄调已不知写了几年,春去之痛已不知经历几回了。曾经轰轰烈烈,最终却去不留痕,就更显得可悲可叹。春是如此,变法、国运、青春、友情就更是如此了。
眼看着不安就要涌出,故换头二句不得不以加倍的沉稳来控制。落花随水流去,本是哀景,而作者偏说好,只因带去了西园的落花,正免得人睹物伤怀,也算是带去伤春恨了。这种兼有乐观与回避性质的宽慰与“却道天凉好个秋”何其相似!此后再接再厉——那涵盖种种愁绪的凭栏意,欲说还休,且交付给杜鹃去说吧。至于人,又何妨在东风中伴随着春光悄悄地度过年华呢?然而,出去归来都注视着这令人销魂的落花残春,满怀的愁绪终是难消,故最终决定要借酒醉摆脱愁绪。而此时已是春尽夏至,绿树成荫了——作者春愁持续的时间之长可见,消愁的种种尝试都为徒劳也可知。末道:“谁与玉山倒?”则表明连戒酒避愁的尝试也要失败了,只因能与共醉的知音人实在难寻啊。
这首诗写唐叔良溪居,带写唐叔良人品,将人与景物紧密结合,抒发自己对隐居生活的向往。首联写溪居,次联为居中望见之景,颈联为居中主人,尾联绾合宾主。全诗脉络明晰,淡淡写来,虽无惊人之笔,然轻巧细致,中间二联,尤为凝练,得韦应物诗真趣。
首联写溪居。“高斋”谓此中乃高人所住,“每到”一词,可知诗人乃唐氏好友,常来常往,过从甚密;亦可见此诗非一时之作,而是长期观察、品味、意溪居所得,故下文写景,亦是经过了严密筛选。因为“门巷玲珑野望通”,所以“思无穷”。此居虽有门有巷道,却玲珑剔透、精致小巧,即在门巷之内,亦可望见四野风情,此乃由“思无穷”三字引发。“门巷玲珑”,形容建筑之精巧细致;“野望通”,表明在庭院设计中充分考虑到“借景的妙处,所以四边美景,尽收在唐宅之中。
颔联即由“野望通”而下,写望中所见。因“野望通”,所以“片雨隔村犹夕照”,由溪居望去,隔村的夕照,四边美景,尽收在唐宅之中。“疏林映望已秋风”,则构成了一幅和谐宁穆的画面。这二句措词疏淡,微含薄凉,亦未尝无暖色调,但终可望不可即,此正是元季江南士夫之心境,其身也疏懒,其心也淡泊,于世事也无望、于将来也漠然唯微雨、远村、夕阳、疏林、秋望,最合其心境,故最堪为伴。上联既言“每到思无穷”,则此联之景,必非溪居所望全景,诗人但摄取与我会心者而已。
颈联由景及人。“药囊诗卷闲行后”,在此疏淡背景上,所见之人(唐氏),亦复萧散自放。不能为良相,则求为良医,不能以文章用世,则求以诗自遣。此亦闲散中无聊之举。“香灺灯光静坐中”,写唐叔良悠闲怡然的生活。
尾联赞唐叔良,也是自己向往脱离尘世的感慨。此唐氏为人之大节,亦诗人所深企慕者。故尾联乃问,“只今”乱世,江海之上,“如君无事几人同?”“几人同”,可见其人不多,然亦未尝没有,故尾联一问,既赞主人,又隐然自道,为绾合宾主之笔。其实,有此一笔,则可见诗人与主人实为同志者,而中四句之景之人,亦诗人胸中所有之景,心中向慕之人。
此诗脉络明晰,诗中四句甚佳,其情趣自不待言,措词亦多可味,若颔联之“犹”“已”,颈联之“后”字,均见功力。“犹”字,可见前村后村皆有夕照,前村有之后村犹有之,唯溪居上不见,然则“片雨”之“片”字亦得照应“已”字含有惊悟之意,见疏林间掩映秋望,乃悟秋日已到,树木凋零。“后”字,将前之“闲行”又归结到“行”后之溪居中,不失题意。这些措词写来又声色不露,从容不迫,不作有意强调。综之全诗写景写人、遣词,皆是出于一种风神,读此诗,可想见彼人之神情,可推知彼时之士风。诗虽无惊人之笔,然确是典型的元季士人之笔。
这是一首赠妓词,上片从女方着笔,描写她在楼上窥视恋人驾着车马飞奔而去的情景,下片从男方着笔,抒发自己不忍离别而不得不别的怅惘之情。这首词是一首较有特色的艳情词,其特色在于深情绵邈,婉转凄恻,从男女两方抒写别情,两副笔墨写出一种心情。这首词铺叙展衍,写足实情实景;委婉含蓄,轻点彼此心境。
上片从女方着笔,写她在楼上看到恋人身骑骏马,奔驰而去。这个开头是用“顿入”的手法,一下子闪出两个人物形象。然后便写别时景物。“朱帘”三句,承首句“小楼”而言,谓此时楼上佳人正穿着春衫,卷起朱帘,凝望着远去的情郎。“破暖”三句,表面上是写微雨欲无还有,似在逗弄晴天,实际上则缀入女子的感情——她也像当前的天气一样阴晴不定。如果说相别的时间在早晨或午后,那么这位女子便是一个人在楼上一直等到红日西斜。以下四句就是写这种等待的过程和情绪。轻风送来的卖花声轻脆悦耳,充满着生活的诱惑力,如梦如幻,把人引入诗意一般的甜美境界,也易触动人们的绮思幽怨。女主人公想去买上一枝,插在鬓边。可是纵有鲜花,无人适为容矣。她没有心思去买花,只好让卖花声过去,直到它过尽。
“过尽”二字,用得极妙,从中可以想像女主人公谛听的神态,想买又终于不买的惋惜之情。特别巧妙的是,词人将声音的过去与时光的流逝结合在一起写,若是一字一顿地吟诵“卖花声过尽斜阳院落”,便会体会到女主人公绵绵不尽的幽思。歇拍二句,则是以景结情。落红成阵,飞满井台,景象是美丽的,感情却是悲伤的。花辞故枝,象征着行人离去,也象征着红颜憔悴,最易使人伤怀。它同词人在《千秋岁》中所说的“飞红万点愁如海”相比,意境有些相似,但却没有点明愁字。不言愁而愁自在其中,因而蕴藉含蓄,带有悠悠不尽的情味。
下片从男方着笔,写别后情怀。“玉佩丁东别后”,虽嵌入娄琬之字“东玉”二字,然十分自然,无人工痕迹,读后颇有“环佩人归’之感。“怅佳期、参差难又”,是说再见不易。刚刚言别,马上又担心重逢难再,可见人虽远去,而留恋之情犹萦回脑际。至“名缰利锁”三句,始点出不得不离别的原因。古代士人,既向往爱情的幸福,也要追求功名富贵,这是当时社会造成的一种思想矛盾。为了功名富贵,不得不抛下情人,词人思想上是矛盾的、痛苦的,因此发出了诅咒。“和天也瘦”,从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中“天若有情天亦老”化来。但以瘦易老,却别有情味。明王世贞对此极为赞赏,他说‘瘦’字极妙。”这个“瘦”字概括了人物的思想矛盾,突出了相思之苦。多少个不眠之夜,多少次辗转反侧,都包含在一个“瘦”字中。
至“花下重门,柳边深巷,不堪回首”三句,愈出精彩。此时男主人公虽策马远去,途中犹频频回首,瞻望所恋之人的住处。着以“不堪”二字,更加刻画出难耐的心情,难言的痛苦。歇拍三句,饶有余味,写对月怀人之感,颇有“见月而不见人之憾”。古代许多诗人也常写对月怀人,或以美好的祝愿,带给读者以怡悦欣慰之情;或以凄然的远望,带给读者以惆怅迷惘之思。少游则不然,他赋予皓月以人的感情,说它当初曾多情地照着男女双方,如今虽仍像从前一样当空高照,但只照着男子的孑然一身。一种孤独之感,凄然言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