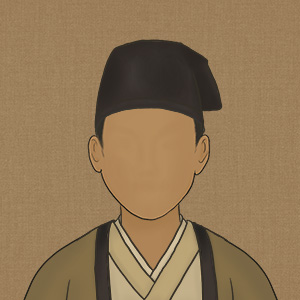此词纯用民歌形式,上下片均以“长相思”迭起,上片言只有相见才得终了相思之情;下片言由于不得相见,相思之情无处诉说,以浅情人不能理解自己的心情反衬自己一往而情深。词的上片,一气流出,情溢乎辞,不加修饰。“若问”两句,自问自答,痴人痴语。要说“相见”是解决“相思”的唯一办法,这纯是痴语,痴心,可是,小晏却认认真真地把它说了出来,正是如黄庭坚《小山词序》所云“其痴亦自绝人”。
结句非同凡响,抒写了比相思不相见更大的悲哀。“说似谁”,犹言说与谁、向谁说。纵使把相思之情说了出来,那浅情的人儿终是不能体会。浅情是深情的对面,多情的小晏却总是碰到那样的人,可是,当那人交暂情浅,别后又杳无音信,辜负了自己的刻骨相思时,词人依然是一往情深,不疑不恨,只是独自伤心而已。下片四句,以“浅情人”反衬小晏相思苦恋之情,无奈和遗憾。
此词为作者词中别调,语极浅近,情极深挚,在朴直中自饶婉曲之致,缠绵往复,姿态多变,回肠荡气,音节尤美。用对比的手法突出词人用情之深。
此诗载于《全唐诗》卷四百二十五。下面是陕西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霍松林先生对此诗是赏析。
与白居易同时的李肇在《唐国史补》里说:“京城贵游,尚牡丹三十余年矣。每春暮,车马若狂,以不耽玩为耻。执金召铺宫围外寺观,种以求利,一本有值数万者。”这首诗,通过对“京城贵游”买牡丹花的描写,揭露了社会矛盾的某些本质方面,表现了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主题。诗人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从买花处所发现了一位别人视而不见的“田舍翁”,从而触发了他的灵感,完成了独创性的艺术构思。
全诗分两大段。“人人迷不悟”以上十四句,写京城贵游买花;以下六句,写田舍翁看买花。
京城的春季将要过去,大街小巷来来往往奔驰着喧闹不已的车马。都说是牡丹盛开的时节,呼朋引伴、争先恐后地赶去买花。一开头用“帝城”点地点,用“春欲暮”点时间。“春欲暮”之时,农村中青黄不接,农事又加倍繁忙,而皇帝及其臣僚所在的长安城中,却“喧喧车马度”,忙于“买花”。“喧喧”,属于听觉:“车马度”,属于视觉。以“喧喧”状“车马度”,其男颠女狂、笑语欢呼的情景与车马杂沓、填街咽巷的画面同时展现,真可谓声态并作。下面的“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是对“喧喧”的补充描写。借车中马上人同声相告的“喧喧”之声点题,用笔相当灵妙。
这四句写“买花去”的场面,为下面写以高价买花与精心移花作好了铺垫。接着便是这些驱车走马的富贵闲人为买花、移花而挥金如土。“灼灼百朵红,戋戋五束素。”“戋戋”,委积貌,形容二十五匹帛堆积起来的庞大体积。古代以五匹为一束。“五束素”,即二十五匹帛。《新唐书·食货志》:“自初定"两税"时钱轻货重,······绢匹为钱三千二百。”当时正行“两税法”,一匹绢为三千二百,那么“五束素”便为钱八万。一株开了百朵花的红牡丹,竟售价八万,其昂贵的确惊人。那么“上张幄幕庇,旁织笆篱护,水洒复泥封,移来色如故”,其珍惜无异珠宝,也就不言而喻了。
家家以弄花为习俗,人人执迷不悟。以上只作客观描绘,直到“人人迷不悟”,才表露了作者的倾向性;然而那“迷不悟”的确切含义是什么,仍有待于进一步点明。白居易的有些讽谕诗,往往在结尾抽象地讲道理、发议论。这首诗却避免了这种情况。当他目睹这些狂热的买花者挥金如土,发出“人人迷不悟”的感慨之时,忽然发现了一位从啼饥号寒的农村“偶来买花处”的“田舍翁”,看见他在“低头”,听见他在“长叹”。这种极其鲜明、强烈的对比,揭示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本质。在热闹喧哗的买花场景中,诗人不失时机地摄下了“低头独长叹”的特写镜头,并以极其鲜明强烈的对比,从“低头”的表情与“长叹”的声音中挖掘出全部潜台词:仅仅买一丛“灼灼百朵红”的深色花,就要挥霍掉十户中等人家的税粮!揭示了当时社会“富贵闲人一束花,十户田家一年粮”的贫富差距。最后这一警句使读者恍然大“悟”:那位看买花的“田舍翁”,倒是买花钱的实际负担者!推而广之,这些“高贵”的买花者,衣食住行,都是来源于从劳动人民身上榨取的“赋税”。诗人借助“田舍翁”的一声“长叹”,尖锐地反映了剥削与被剥削的矛盾。敢用自己的诗歌创作谱写人民的心声,这是十分可贵的。
《登原州城呈张贲从事》是北宋诗人魏野创作的一首七言律诗。这首抒写羁旅客愁。首联以问句呼起,点明忧愁因独上边城城楼望远,但见满目荒寒引起。颔联渲染原州冷落萧条的景象,言置身于无尽头的孤寂之感。颈联由听觉感受和视觉感受,衬托出诗人心境的悲凉。尾联总束全篇,写出友人为异乡贫官而自身为客,离恨均难收拾的情状。全诗写景高远开阔,情调苍凉凄楚。
首联以设问形式开篇,先是自问身处异乡何处最易牵发个人愁绪,接着自答孤身一人独自登上边远城楼,这就足“答案”。身处异乡,就已令人孤寂忧愁的了,更何况是客子伶仃一人独自登上偏远边城城上之楼呢。站在边城高处,就能极目远眺,边地景色一览无余。就是这带有边地特征的景色,最能牵动客子心中之愁,此意虽然诗人没有明说,但却蕴情于景。借助逼真的画面予以展现。这就既为下文抒写展开了宏伟的画卷,又设定了“愁”这一主体旋律,颇有柳宗元“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式的开头风格。
颔联开始抒写塞外风光。“日暮北来惟有雁”,秋季黄昏,抬眼望去,眼前看到的唯有振翅而飞的北归雁群,尽管是“平沙万里绝人烟”,但却仍是“衡阳雁去无留意”,北来的雁群仿佛毫无留意,头也不同地向着南方的中原飞去了。渐渐地“几行归雁云边断”,心中不难涌起“何处行人不断肠”的愁怨。诗人的家同本在中原,但却不得不滞留两北边陲一望着那越飞越远的雁儿,令作者伤感。“地寒西去更无州”,虽说现在还是秋天,然而边地冬季来临甚早,早已天寒地冻,衰草连天了。从此再往西去,已经没有朝廷的州郡了。想到自己就像那身不由己无依无靠的蓬草,被寒风一吹,就流落到了这边远荒凉的原州边城了,作者不由得悲从中来。
颈联紧承上文进行情景描述。“数声塞角高还咽”,处在凄凉哀愁情绪中的诗人偏偏又听到了几声时而高昂时而呜咽的军中号角,就不禁在凄凉悲切的羁旅心境中又平添了几多哀愁:“一派泾河冻不流”,诗人此刻站在原卅城上,放眼望去,只见泾河之水早已被冻住不流了,更使人觉得“塞上风云接地阴”,让这种顿起“愁云惨淡万里凝”哀思。面对这样的穷荒野漠,碎丘幽壑,耳闻声声号角,呼呼北风,一介书生剩下的只有“可怜无定河边骨”的惨不忍睹的景象和“古来征战几人回”之无穷无尽的感慨了。
尾联“君作贫官我为客,此中离恨共难收”。这两句是说:你在异乡作小官,我在异乡作异客,其中的客愁,是你我两人都难以收拾的。尾联以贫官、异客之离恨作结,呼应了开头的“牵愁”,点明了主旨。
这首诗首尾两联抒情,中间两联写景。抒情,则感情悲怆;写景,则景象萧瑟。情景交融,感人至深。这首边塞羁旅行役律诗景象萧瑟,感情悲怆,和盛唐的边塞诗有霄壤之别。时代之不同是造成差异的一个原因,身份之不同则是更主要的原因,作者是个消极遁世的隐士,而高适和岑参他们则是积极进取的用世之士。
这是王维一篇山水田园之作,诗篇脉络清晰,层次分明。首句点明写作动机,夕阳西下的黄昏时节,风景这边独好,置身于如此美景之中,诗人情不自禁地想要邀请裴君一起吟诗作乐。三四句着二“态”,“淡然”显现出诗人观景之心态,恬淡自在;“支颐”描摹出诗人观景之姿态,兀自沉醉。寥寥二笔,却将诗人观景之心绪、姿态描摹得惟妙惟肖。“望”字亦为传神之笔,一则突显出所管之景的开阔伸冤之意境,二则将诗人观景之神韵流露出来,或远望,或凝望,或油然而思,或启迪而发。此渺远之境,或许是开启诗人心扉的一把密钥。沉寂了一冬的淡漠,在此等万物复苏,欣欣向荣的景致之中,总该有所萌动的。个中情致,唯作者感知。徐徐春风轻拂,惊醒了那沉睡的百草,齐齐在微风荡涤中悄然萌动;看那篱笆从中,兰惠丛生,散发出缕缕幽香,沁人心脾。一“动”一“生”,以动写静,赋予百草与兰惠以生机与活力;描兰惠之态,实则又隐约地展露出诗人才望高雅、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之情操。诗人说,暖暖的夕阳,朦胧而柔和,从他那那盛满春光的室内渐渐退去,只留下一丝尚存的余晖。春的气息,亦带来了村庄的活跃,傍晚时分,老农亦走家串户,到他那儿闲聊。后面四句为“致词”内容,水边的土地上,布满了嫩绿的草木,欣欣向荣,一派蓬勃之象;那泛着绿萍的池塘,在微风轻拂下,荡漾起丝丝涟漪,一圈一圈,向四周荡开。大片的桃李树林,一瞬间也换上了春的彩妆,前面还是光秃秃的杆儿,一缕春风吹过,焕然一新,披上了绿的衣裳,嫩绿的新芽,油然而生,疯狂向外探头,急切地渴盼着打量这个未知的世界。那青葱的长势,孕育出团团花骨朵儿,在绿色的世界里增添一丝春的芬芳。这青翠的绿芽,这悄然欲出的花蕾,饱含生机,却也蕴藏着希望,恍惚间能瞅见老农眼里充满希冀的光芒,那该是硕果累累的丰收。末句回归题目,趁此农忙时节将至,诚邀裴君过来,一同欣赏品味这春意盎然之趣。
这首诗清新欢快,淡然素雅,朴实醇厚的言语,描绘的却是最真切自然的景象。诗人处身于那样的年代,切身体验官场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却又醉心自然,情归大地,难能可贵的是乱世之中,还有志同道合之人,吟诗作乐,感慨世事。诗人之妙手,绘尽世间美景,却丝毫不着痕迹,令人赞叹。
该诗用情景交融的表现手法,生动地描绘了一位捣衣女子对出征边塞的丈夫深切思念之情,盼望战争早日结束、丈夫早日归来团聚的急迫心情。全诗五七言杂用,笔法含蓄细腻,意境优美,辞藻华丽。
前四句为第一层, 主要是运用客观描述的方法,来反映妇女们给丈夫缝制衣裳时轻捣布帛的凄凉忧伤情景。
诗一开始,通过交代捣衣的地点、时间、人物,把读者引入一种特有的凄凉境界。故事发生的地点是在长安城中,时间是秋天的夜晚,人物是美丽的女子,她们正在精美的捣衣石上用木棒轻捣黄色的布帛,使之柔软,准备为离家远戍边塞的丈夫缝制御寒的衣裳。首句的“秋夜长”,一个“长”字写出了女子的无限惆怅,她们的日子是多么难熬,有着度日如年的感受。第二句用了许多修饰词,“佳人”写出了女子的年轻美貌, “锦石”写捣衣石的精美, “流黄”是借代词,指黄色的布帛鲜艳漂亮。男耕女织本是中国劳动家庭的合理分工,秋夜里美貌的女子在精美的捣衣石上轻捣丝帛,这本来是一幅意、境俱美的织妇画, 富有强烈的审美意义,然而长夜难熬,却使这美好的生活带上了凄苦悲凉、孤独寂寞的气氛和色彩。作者运用这种笔法来突出妇女为远戍边塞的丈夫捣衣时所引起的思念之情,音调凄婉,颇有情韵。
接下去的两句 “香杵纹砧知近远,传捣递响何凄凉”写捣衣捣:妇女们捣衣的捣响有远有近, 次第传来,十分凄凉。如果说前两句是叙写一位美貌女子捣衣时的凄苦和寂寥,用词还比较含蓄的话,那么这两句则推而广之,写众多的妇女都在为丈夫赶制御寒的戍衣,秋季的到来,预兆着天气马上就要变冷了,妇女们一边捣布,一边深切地思念着自己的亲人。从这远近传来、次第错落的捣衣捣中,不仅可以听到她们的哀怨, 而且可以听到她们的泣诉!也许她们正是用响亮的捣衣捣来掩盖自己的悲苦泣诉!这彼起此伏的捣衣捣互相响应着,表现出她们对战争的愤怒抗议。
后四句为第二层,主要是抒情,表现妇女们对远戍边塞的丈夫的深切思念之情。
“七夕长河烂, 中秋明月光”,这一联是五言诗句。 银河星系是人们肉眼看见的星座最多、光彩灿烂的星系,所以这里说“长河烂”;中秋节的时候明月满弦, 月光明亮, 古代习俗常常以中秋为家人团圆的日子, 古诗中亦常用中秋明月寄托相思之情。所以这两句诗即是以牛郎织女相会的故事和中秋家人团圆的习俗,来反衬出捣衣妇女的独居凄凉及相思之苦。
最后两句“蠮螉塞边绝候雁,鸳鸯楼上望天狼”,寓意更加明确。前面一句蕴含着两层意思: 一层指天气渐渐冷了, 一年又将过去, 寓意着丈夫的戍役遥无期限; 一层是说守戍边地的亲人绝断了音信,死活不得而知,妇女们想念得更加焦虑凄苦。后面一句的意思是说,妇女们在居处的楼上观察天狼星的动向, 盼望着边塞的战争已经停息,侵略者已被击退,丈夫能够早日回家来团圆。
这两层意思之间,密切联系,浑然一体,天衣无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