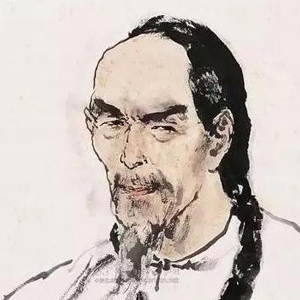《塞翁失马》通过一个循环往复的极富戏剧性故事,阐述了祸与福的对立统一关系,揭示了“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道理。如果单从哲学角度去看,这则寓言启发人们用发展的眼光辩证地去看问题:身处逆境不消沉,树立“柳暗花明”的乐观信念;身处顺境不迷醉,保持“死于安乐”的忧患意识。
从寓言本身包含的思想倾向来看,存在与主流思想不和谐的因素:“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壮者引弦而战。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独以跛之故,父子相保。”胡人大举入侵,国难当头,青壮年都拿起武器去打仗了,而且有那么多的人在战场上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足见战争之惨烈。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善术者”父子没有尽匹夫之责,倒是“以跛之故”保全了性命。
问题不在于“父子”是否上战场,毕竟年老和腿瘸的客观现实给了他们没上战场的理由。问题的关键是作者把“父子”因为没有上战场而保全了性命当做了莫大的“福”分,并为之而庆幸。这与培养爱国主义感情、道德品质,逐步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正确的价值观”的要求很不一致。
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善术者”因为腿被摔瘸了而没有为国尽力,理当感到遗憾甚至惭愧,特别是在有那么多战死者的情况下,作为苟活者,应该感到内疚甚至耻辱才是。但“父子”没有,他们只是庆幸,庆幸“堕而折其髀”的灾祸,庆幸逃脱了去战场捐躯”,庆幸继续活下去的福气。
这里没办法去讨论战争的正义与否,毕竟只是一则寓言,是为了诠释一个道理而演绎的故事。如果单从祸福相互转化的关系去看,对这则寓言不能有什么非议。但既然选入了中国的学生教材,就应该特别在乎是否有“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正确的价值观”了。
在一定的条件下,好事和坏事是可以互相转换的,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好事可以变成坏事。“塞翁失马”的故事在民间流传了千百年。无论遇到福还是祸,要调整自己的心态,要超越时间和空间去观察问题,要考虑到事物有可能出现的极端变化。
张岱是一位负奇才的杂家,他在戏曲方面造诣尤深,同时,他又是一位戏曲作家,可惜其戏曲作品未能流传下来。张岱写戏,不过是偶然为之,所谓“游戏词场”,但他酷爱戏曲艺术却是显而易见的。文章回忆了作者在崇祯二年(1629)路过镇江金山寺,兴致大发,即兴表演韩世忠抗金戏剧的故事。文中通过细致描写一位老僧的一连串动作,展现出了被惊醒的僧人们惊疑不定、惊喜交加的复杂情绪。全文语言流利畅达,刻画细腻传神。
首先,是人的情绪非常之好,停舟江口,月光溶溶,江涛漭漭,因之才有“余大惊喜”之情绪。于是乘兴又开船游于江上,这个乘兴,当是忽发奇想的第一契机,时至二鼓,来到大殿前,景致又自不同:四围寂寂,月光如霰。这又是一个刺激,人的情绪更加兴奋。其次,也是更主要的,是由于金山寺这个特定的地方,古往今来,就是征伐麈战之处。油然间,作者想起了与京口有关的历代兴亡遗事:王濬楼船,旧垒神鸦,京江怒涛,金山战鼓,……当年韩世忠,梁红玉就是在这里以八千兵勇大败兀术金兵十万。因而,作者遂有“唱韩蕲王金山及长江大战诸剧”之想。张岱在金山寺演的戏,名目不详,内容是很清楚的,后世京剧中有《战金山》,又叫《黄天荡》,都是取材《宋史》韩世忠本传及《说岳全传》,《双烈记》传奇的。张岱金山夜演的或即《双烈记》传奇的选出,亦未可知。
当时作者是赴兖州途经镇江,参读《陶庵梦忆》卷四之《兖州阅武》中有“辛未三月,余至兖州”的话,可知此行历时不短。由此推测,作者大概是在游历访古。金山夜戏演的是武戏,到了兖州又有阅武之举,这隐约透露出作者这一时期对国力不支所感到的忧虑,联系明亡后他对故国的深沉怀念以及“披发入山”,不与满清统治者合作的气节,颇有助于了解张岱其人的思想。
张岱为文,似无意于感人,然每每于寻常细寓的娓媚道来中,洋溢着深沉的情感,无论欢愉愁苦,都令人心驰神往,抚玩无厌。他特别善于点染,常常是在片言只语中传神入化。此则中写江上景物笔调十分别致:“月光倒囊入水”的“囊”字,“噀天为白”的“噀”字,都是神来之笔,颇耐寻味。特别是写老僧夜起看戏的一段,更令人叹为观止。写得一老僧活脱脱如在目前,一寺僧人便尽在眼底了,是谓一笔作百十笔用也。读张岱文,须特别注目于类似的筋节窍髓,其妙处每每在此。
首句破空而来,突兀奇警。海棠花花团锦簇,重葩叠簇,占春颜色最风流。可曾几何时,这艳媚烂漫的名花却又在春风中飘摇零落,遭众人碾踏。造化既赋予海棠以幽姿淑态,人们既培育了海棠叶茂枝柔,可为何又偏偏要作践它。真是天意无常,人心难测。“人天无据”虽仅四字,但凝聚了词人万般感慨,回荡着一腔不平之气.其情其理是经回转激荡之后喷射而出的,可谓字字千钧,撼人心魄。次句直言惜花之举:把花瓣仔细收集珍藏起来。海棠花初开如胭脂点点,开后渐成缬晕明霞,落时则若宿妆淡粉。以“香魂”言之,颇有赞美海棠花零落仍不失娇妍,继续美化人间的高贵品格之意。三、四两句感时叹花。时光流逝,迷离恍惚之中,京都悯忠寺的海棠花开花落又过去了十年。这里词人以想象之中的悯忠寺海棠花开十度,而委婉道出自己收藏花瓣已经十年。名花有几个十年,但人生又有几个十年呢。盛况难再,年华易逝。字里行间又隐约地透露出身世之伤感。
过片顶接歇拍,从时间、空间上翻进一层,渲染惜花之情。十年了,尽管与北京相隔千里,但惜花之心依然未变,一直悬念着寺中的海棠。在词人的想象中,这狼藉满地的落红,定然带有被风雨摧残的痕迹。两句既言花,又自比,是词人为求功名、谋稻粱而颠沛奔波之状况的隐喻。结拍两句由花及人,总束全篇,点明题旨,直接表达了惜花之真情、隐情,不要怪我如此爱花惜花,我的身世也和落花一样。十年前如此,十年后依然如此。这两句充满了词人的酸楚之泪,凝聚了其十七至二十七岁人生的不幸遭遇。词人饱学多才,极欲尽早用世,但十年奋斗,得到的却是打击和磨难。光阴东流,才华虚掷,功名无期。名花如此,世道人生之艰难亦如此。词人这种同命相怜何必分人花的感叹,直贯全词。因此,写花,实质上也是自咏。其涕泪横流之伤感,除了“身世”之叹,还深刻地反映出更深层次上的时代的悲哀。这也许就是在苏轼、陆游等写下咏海棠的诸多名篇之后,龚自珍这首小令依然不失其魅力,而被人们长久传诵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