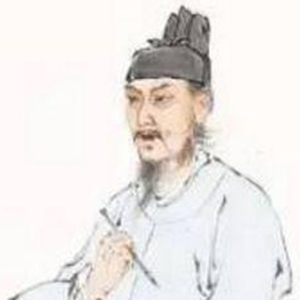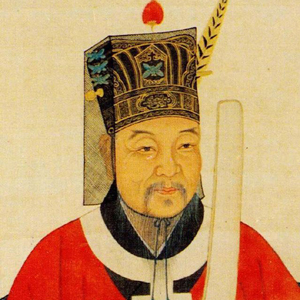千首富,不救一生贫。贾岛形模元自瘦,杜陵言语不妨村。谁解学西昆。
千首富,不救一生贫。贾岛形模元自瘦,杜陵言语不妨村。谁解学西昆。
这首词以自我解嘲的笔触抒写自己的情怀、见解,造成了一种独特的幽默气质,词中暗含着对自己诗作的自负,又对贾岛、杜甫诗和西昆体表明了态度。
这是一首极罕见的、以词论诗的作品,继承了辛弃疾《虞美人》论杜叔高诗的传统,颇感可贵。
上片,“田舍子”与“诗人”对比。词的起首“石屏老,家住海东云”,以平实的语言,点明自己的住处和出身,对自己隐居故里、生活清贫感到安然自得。但是竟被称为诗人,而作诗是“常益费精神”的事。这是自我解嘲,一则表现了自己的一种懊恼心境,二则流露了对自己作诗人的自负。运用对比反说,似直而实曲。
其次,“富”“贫”对比。“千首富,不救一生贫”,是上片的注脚,是下文的起始,承上启下,合情合理。物质贫乏,精神富有,是自己处境的写照,又是贾岛、杜甫的写照。表达了对贾岛、杜甫的同情,对自身境况的感叹,“不救”透露了一种愤慨之情。“富”又包含着对自己诗词的自负感。“富”“贫”并用,互相映照,似浅显,含意却深远。
再次,贾岛、杜甫的“瘦”“村”与西昆并提,形成对比。贾岛一生凄苦寂寞,他的诗以善于锤炼字句取胜,以苦吟著称,苏轼有“郊寒岛瘦”之说;杜甫也一生贫穷困顿,漂泊转徙,诗以沉郁顿挫的风格受人赞赏,而西昆体诗人杨亿却贬他是“村夫子”(见刘攽《贡父诗话》)。作者巧妙地抓住了一“瘦”一“村”,组织成句,其间包含着极丰富的内容,“瘦”、“村”既是贾岛、杜甫在形模、言语上的特点,也是他们诗作的突出风格,“元自”、“不妨”二字显示出作者对这两种风格的肯定。诗人固穷,穷是诗人的生存状况,正是“穷”,成就了诗名。“谁解学西昆”,为什么不去学呢?原来西昆体诗歌,内容空虚,形式上追求对仗与华美,不过摭拾典故、堆积词藻而已。似乎是不“瘦”不“村”,其实是华而不实。
词中肯定了贾岛、杜甫的诗歌,对讥刺杜甫为“村夫子”的西昆体诗人,提出了批评,又流露了对自己诗词的自负感。词的语言朴实,但词意却曲折婉转,诗乍一看,非常浅显,其含意却很深刻。表面上是自我解嘲,实际上表达了自己的深刻见解。这种婉转的风格,主要是通过反说对比手法表现出来的。
这首词以自我解嘲的笔触抒写自己的情怀、见解,造成了一种独特的幽默气质,词中暗含着对自己诗作的自负,又对贾岛、杜甫诗和西昆体表明了态度。
这是一首极罕见的、以词论诗的作品,继承了辛弃疾《虞美人》论杜叔高诗的传统,颇感可贵。
上片,“田舍子”与“诗人”对比。词的起首“石屏老,家住海东云”,以平实的语言,点明自己的住处和出身,对自己隐居故里、生活清贫感到安然自得。但是竟被称为诗人,而作诗是“无益费精神”的事。这是自我解嘲,一则表现了自己的一种懊恼心境,二则流露了对自己作诗人的自负。运用对比反说,似直而实曲。
其次,“富”“贫”对比。“千首富,不救一生贫”,是上片的注脚,是下文的起始,承上启下,合情合理。物质贫乏,精神富有,是自己处境的写照,又是贾岛、杜甫的写照。表达了对贾岛、杜甫的同情,对自身境况的感叹,“不救”透露了一种愤慨之情。“富”又包含着对自己诗词的自负感。“富”“贫”并用,互相映照,似浅显,含意却深远。
再次,贾岛、杜甫的“瘦”“村”与西昆并提,形成对比。贾岛一生凄苦寂寞,他的诗以善于锤炼字句取胜,以苦吟著称,苏轼有“郊寒岛瘦”之说;杜甫也一生贫穷困顿,漂泊转徙,诗以沉郁顿挫的风格受人赞赏,而西昆体诗人杨亿却贬他是“村夫子”(见刘攽《贡父诗话》)。作者巧妙地抓住了一“瘦”一“村”,组织成句,其间包含着极丰富的内容,“瘦”、“村”既是贾岛、杜甫在形模、言语上的特点,也是他们诗作的突出风格,“元自”、“不妨”二字显示出作者对这两种风格的肯定。诗人固穷,穷是诗人的生存状况,正是“穷”,成就了诗名。“谁解学西昆”,为什么不去学呢?原来西昆体诗歌,内容空虚,形式上追求对仗与华美,不过摭拾典故、堆积词藻而已。似乎是不“瘦”不“村”,其实是华而不实。
词中肯定了贾岛、杜甫的诗歌,对讥刺杜甫为“村夫子”的西昆体诗人,提出了批评,又流露了对自己诗词的自负感。词的语言朴实,但词意却曲折婉转,诗乍一看,非常浅显,其含意却很深刻。表面上是自我解嘲,实际上表达了自己的深刻见解。这种婉转的风格,主要是通过反说对比手法表现出来的。
这首诗作于公元750年(天宝九年)。当时,诗人供职于高仙芝幕府,不受重用,因而心情压抑,此时诗作中大都有思乡之语,这一首为其中最沉郁、伤感者。
首联两句以鲜明对比来说明离家西行已越发遥远,返回之期更是渺茫,只能在极度思乡之时偶尔回首而已,可是行程仍然继续往西,那种无奈与沉痛扣人心弦。颔联写自然环境的恶劣和景物的重复单调,使诗人在无聊的旅途中,更增对家乡的怀念。颈联极言时间之延滞,路途来回之遥远,表明诗人对域外生活已经十分厌倦,如此则更见思乡之苦,思乡之切。尾联写诗人与友人分别后不到一年就头鬓斑白,可见其受愁思煎熬之深。
该词从当涂的名胜古迹写起。开头两句概括了当涂的山川风物。缀以“青青麦”三字,引发读者“黍离麦秀”的联想。《史记·宋微子世家》写到殷商旧臣“箕子朝周,过故殷虚,感宫室毁坏,生禾黍,箕子伤之”,遂作《麦秀》之诗,诗云:“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青青麦”字面上又是用《庄子·外物》所引的逸《诗》:“青青之麦,生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昔时高台离宫,而此时麦苗青青,透露出世事沧桑的无限感慨。呈孰本是当涂县的古名,呈孰溪流贯其中,呈孰堂凌驾溪上,颇得山水之胜。所谓“馀翰墨”,实即感叹昔人已逝,只留下了佳篇名章。这两句寄寓了山谷宦海浮沉的无尽感慨,无论是称雄一世的帝王,还是风流倜傥的词客,都已成历史的陈迹,只有文章翰墨尚能和江山共存,垂之久远。接下来两句写出知太平州。经过迁谪的动荡磨难,忧患馀生的作者已把做官一事看得十分淡漠,所以他把此事只称为“管江山”、“分皂白”。再加上一个“暂”字,一个“稍”字,更突出了这种淡然超脱的态度。
下片开头两句概括了九日罢官的戏剧性变化,与上两句适成对照,大有物是人非之慨。“江山”承上而来,山川形胜,碧天浮云,着一“空”字,是因为“昨日主人今日客”,本来要“管江山”、“分皂白”的主人,一下子成了“诸公”的客人了!这一句集中揭示了政治生活的反常和荒廖,它运用当句对,一句之中既构成今昨主客的鲜明对比,语气斩截,强调了变化之突兀,其中有感叹、不平、讥讽、自嘲,内涵颇为丰富。最后两句则展现了作者自我解脱的感情变化。新妇石是千百年来历史的见证,阅尽了人世沧桑,但见人间的升沉荣辱都只如过眼烟云,本无须有是非彼此之分。“谁分宾主”句,看似作者劝大家无分宾主,尽欢一醉,深乃用“万物之化,终归齐一”的老庄哲学来作自我解脱。
这首词旷达超然之中发泄了牢骚不平,最后仍归结为物我齐一,表现出作者力图老庄哲学中寻求解脱的思想倾向。一个“暂”字表现出作者不以进退出处萦怀的超脱。变化的万物本来只是“道”运行中表现出的一种暂时形式,故宜随形任化,淡然自若,不入于心。但一夜突变,毕竟难堪,所以还是不免有牢骚,最后又用齐物论否定牢骚,达于解脱。
这首一首边塞诗,写边关将士夜闻笳声而触动思乡之情。万里别家,多年不归,有时不免思乡,无论是见景还是听声,都容易勾起悠悠的乡思。
“秦中花鸟已应阑,塞外风沙犹自寒。”写战士们在边关忍受苦寒,恨春风不度,转而思念起故乡明媚、灿烂的春色、春光来。
“夜听胡笳折杨柳,教人意气忆长安。”极力渲染出了一种思乡的氛围:寒冷的夜晚万籁俱寂,而笳声的响起更让人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并且悲凉的笳声吹奏的偏又是让人伤怀别离的《折杨柳》,悠悠的笳声在夜空回荡,教战士们的思乡之意更加浓厚。
这首诗抓住了边塞风光景物的一些特点,借其严寒春迟及胡笳声声来写战士们的心理活动,反映了边关将士的生活状况。诗风苍凉悲壮,但并不低沉,以侠骨柔情为壮士之声,这仍然是盛唐气象的回响。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诗起首作者言自己虽然居住在人世间,但并无世俗的交往来打扰。为何处人境而无车马喧的烦恼?因为“心远地自偏”,只要内心能远远地摆脱世俗的束缚,那么即使处于喧闹的环境里,也如同居于僻静之地。陶渊明早岁满怀建功立业的理想,几度出仕正是为了要实现匡时济世的抱负。但当他看到“真风告逝,大为斯兴”,官场风波险恶,世俗伪诈污蚀,整个社会腐败黑暗,于是便选择了洁身自好、守道固穷的道路,隐居田园,躬耕自资。“结庐在人境”四句,就是写他精神上在摆脱了世俗环境的干扰之后所产生的感受。所谓“心远”,即心不念名利之场,情不系权贵之门,绝进弃世,超尘脱俗。由于此四句托意高妙,寄情深远,因此前人激赏其“词彩精拔”。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中的“心远”是远离官场,更进一步说,是远离尘俗,超凡脱俗。 [4] 排斥了社会公认的价值尺度,探询作者在什么地方建立人生的基点,这就牵涉到陶渊明的哲学思想。这种哲学可以称为“自然哲学”,它既包含自耕自食、俭朴寡欲的生活方式,又深化为人的生命与自然的统一和谐。在陶渊明看来,人不仅是在社会、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存在的,而且,甚至更重要的,每一个个体生命作为独立的精神主体,都直接面对整个自然和宇宙而存在。
这些道理,如果直接写出来,诗就变成论文了。所以作者只是把哲理寄寓在形象之中。诗人在自己的庭园中随意地采摘菊花,偶然间抬起头来,目光恰与南山相会。“悠然见南山”,按古汉语法则,既可解为“悠然地见到南山”,亦可解为“见到悠然的南山”。所以,这“悠然”不仅属于人,也属于山,人闲逸而自在,山静穆而高远。在那一刻,似乎有共同的旋律从人心和山峰中一起奏出,融为一支轻盈的乐曲。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四句叙写诗人归隐之后精神世界和自然景物浑然契合的那种悠然自得的神态。东篱边随便采菊,偶然间抬头见到南山。傍晚时分南山景致甚佳,雾气峰间缭绕,飞鸟结伴而还。诗人从南山美景中联想到自己的归隐,从中悟出了返朴归真的哲理。飞鸟朝去夕回,山林乃其归宿;自己屡次离家出仕,最后还得回归田园,田园也为己之归宿。诗人在《归去来兮辞》中曾这样写道:“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他以云、鸟自喻,云之无心出岫,恰似自己无意于仕而仕;鸟之倦飞知还,正像本人厌恶官场而隐。本诗中“飞鸟相与还”两句,与《归去来兮辞》中“鸟倦飞而知还”两句,其寓意实为同一。
“采菊东篱下”四句,古人对此评价甚高。张戒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景物在目前,而非至闲至静之中,则不能到,此味不可及也。”那么,张戒所说的“味”是什么呢?为何说“此味不可及”呢?我们知道,陶诗不尚藻饰,不事雕琢,明白如话,朴素自然,故前人常用“平淡”两字以概其诗风。但陶诗之平淡乃从“组丽”中来,是平而有趣,淡而有味。这种貌似平淡实则醇美的特色,实为一种更高的艺术境界,非常人所知,亦非常人所能。张戒所说的“味”,当是陶诗醇美的韵味。此种韵味之所以“不可及”,原因固然众多。我们撇开文学修养、艺术才能等条件,可以说这种韵味只有像陶渊明那种不愿随俗浮沉,不肯汩泥扬波的诗人才能写出,也即只有寄心于远、心境“至闲至静”者才能写出。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诗末两句,诗人言自己的从大自然的美景中领悟到了人生的意趣,表露了纯洁自然的恬淡心情。诗里的“此中”,我们可以理解为此时此地(秋夕篱边),也可理解为整个田园生活。所谓“忘言”,实是说恬美安闲的田园生活才是自己真正的人生,而这种人生的乐趣,只能意会,不可言传,也无需叙说。这充分体现了诗人安贫乐贱、励志守节的高尚品德。 这两句说的是这里边有人生的真义,想辨别出来,却忘了怎样用语言表达。“忘言”通俗地说,就是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表达,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至情言语即无声”,这里强调一个“真”字,指出辞官归隐乃是人生的真谛。
此诗主要描摹诗人弃官归隐田园后的悠然自得心态,体现出陶渊明决心摒弃浑浊的世俗功名后回归自然,陶醉在自然界中,乃至步入“得意忘言”境界的人生态度和生命体验。此诗以“心远”纲领全篇,并分三层揭示“心远”的内涵。首四句写身居“人境”而精神超脱世俗的虚静忘世态。中四句写静观周围景物而沉浸自然韵致的物化忘我心态。最后两句又深进一层,写“心”在物我浑化中体验到了难以言传的生命真谛此诗意境从虚静忘世,到物化忘我,再到得意忘言,层层推进,是陶渊明归隐后适意自然人生哲学和返璞归真诗歌风格最深邃、最充分的体现。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这首诗就是陶渊明“以物观物”所创造的“无我之境”的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