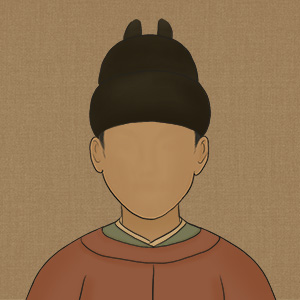词的上片由景物引出人物。清风拂过水面,明月泻下银辉,鳞鳞微浪闪动着光波,月夜恬静、皎洁、优美。此刻,一只装饰华美的小船荡离江岸,驶向迷茫的远方,一个女郎凭依着楼头的栏杆,借着朦胧的月色,凝神目送那渐渐消失在夜空中的一叶轻舟。江波、清风、明月、画船,开端并列几个富有特征的意象,就构成了一个清丽纯净、沁人心脾的意境。值此良宵美景,与意中人联袂共赏,该是何等快意惬怀;然而,其人竟登舟飘然远去,“良辰好景虚设”,令人黯然神伤。“波上清风”、“画船明月”之下,突然接上“人归后”,这三字,使意脉陡转,气氛骤变,顿时给主人公带来了无限的寥落和空虚。“人归后”三字含蕴丰厚,既点明行人,又暗示送者独留,从而逗出下文对居者的描写。“渐消残酒”是翻进一层的写法,临行前,置酒饯别,双方筵席间缱绻叮咛,依依难舍之情,一并涵盖在内,笔法较为经济。残酒渐消,说明分手已为时不短,仍要独自久久凭栏,足见依恋之深。“凭栏久”紧承“渐消残酒”,“独自”应上“人归后”。这位女郎兀自一人,夜幕中凭栏伫立,不忍离去,她对行人的无限钟情便得到了显露。
下片换头写“独自凭栏”的思绪。人之聚散,虽属常事,但别离总给人带来忧伤。苏轼《南歌子·感旧》词云:“寸恨谁云短,绵绵岂易裁。”对于恋人,短暂的分离已足可消魂,何况年年分别,岁岁离恨,而这回又归期难凭呢。这二句,像是女主人公的内心独自,她从当前的离别进而回想起昔日多少次的“聚散匆匆”,其中包含着无数的辛酸与忧虑,期待与不安,容纳了多少实际的生话内容。她凝神冥想,思绪翻腾,却没有觉察到时间如奔逝的流水从身边悄悄掠过。猛然,远处的芜城传来隐隐的更鼓声,原来夜已很深,回首遥望,向时的津渡一片沉寂,只有残月映射下的两行疏柳、几缕淡烟,依稀可辨。南朝宋竟陵王刘诞作乱,城邑荒芜,遂称芜城。鲍照写过著名的《芜城赋》,其后,诗人常借芜城以寄慨。芜城,亦可泛指荒城。煞拍三句,以景结情,言止而意无尽。“重回首”遥接“人归后”,“芜城漏”暗合“凭栏久”,全篇浑然一体,妙合无垠。
此篇词写月夜送别,侧重点在居者的忧思,别后月夜的伫望和凝想,词中对女主人公自我形象的描写着墨不多,摄取清风、明月、淡烟、疏柳、隐隐鼓漏等清丽秀逸的景物来衬映烘托,创造出一个优美的意境,从而使词人深情诚笃的心灵也宛然在目。吴蘅照说:“言情之词,必藉景色映托,乃具深婉流美之致。”(《莲子居词话》)此词正具有这种特色。
开头两句,以本住南朝京城金陵(即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而不意远嫁于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的女子,比拟自己本为南朝忠贞之臣,却于政局突变中误陷异域,羁留于北朝京城。一“住”一“嫁”,衔接紧凑,出语天然;但,是喜是悲,尚未分明。于是逗起悬念,引人观瞻。
紧接着三四两句,用“泪落”这一饱含激动情态的特有形象,回答并肯定了是悲而非喜的前面悬念;又以“何处天边”的疑问,拓开了绵远而深沉的想象与思念。由“金陵”而至“长安”,地域虽远,但都属于京都大邑,相比于荒漠苦野,犹未见其太大的不幸。申之以“不知何处天边”,就把女子(诗人自己的喻体)身在长安却终日向故乡引颈远望,望眼欲穿,终究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心态,鲜明地突现于画面。魏晋时期人们有“举目见日,不见长安”(见《世说新语·夙惠》)的说法,以“日下”喻京都。这里诗人却反拨为身居京都长安而远望天边故乡,仿佛那遥远而又分明的“天边”,才是真正的“日下”,形成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引发力。
五六两句,以“胡尘”与“汉月”并举,对仗工整,精警显豁。用一贬意分明的“尘”埃,笼括北方“胡”地;又用一美感鲜朗的“圆” “月”,象征南方的祖国。并进而一呼“应尽”,一盼“更圆”,于委婉中流溢着激越之情,在期望中潜孕着愤慨之意,产生含蓄而又深切的美学效应。
最后两句,以“君”这一为自己热恋苦思之人,象征南方祖国,并表明自己正为祖国而动情歌唱;由于异乎寻常的心情激动,在洒泪悲歌的同时,竟不知不觉地将伴奏的琴弦拨断了。以“断弦”收结,不仅使人目睹其形,亦能令人耳闻其声,还能触发人们的绵缈思绪:弦虽断而弦上之音仍余韵袅袅,回荡空间,萦绕心头,……可谓涵不尽之幽思如在眼前。
相较其他诗人写精卫的诗歌,本诗视角新颖,不是对精卫本身进行评价,而是就其填海这一行为做理性思考,其中有对精卫因为填海而奔波劳累、伤痕累累的同情,又有对精卫填海这一伤及无辜、毁坏草木的行为提出质疑,同时流露出作者无限悲悯的博大情怀。
诗歌首句“精卫谁教尔填海”,表面看是提问,实则是质疑,明知故问,因为谁都知道精卫填海是为了复仇,报“溺亡”之仇。但这一问,更能引起读者对填海这一行为的思考。接下来,作者就围绕着“填海”为读者呈现四幅画面:
第一幅:“海边石子青磊磊”。这是实景描绘,海边,石子堆积如山。这是精卫填海的凭借,石子之多,足见精卫填海的决心。
第二幅:“海中鱼龙何所为”。这是虚景假设,写填海后果。海被填平后,海中鱼龙如涸辙之鲋般陷入困境,无处求生。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因一己之私仇而可能殃及无辜的鱼龙,作者明知故问的缘由逐渐显现。
第三幅:“山中草木无全枝”。先来一句过渡。第五句“口穿岂为空衔石”照应第二句“海边石子青磊磊”,在诗中起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作者的视角从海边转向山上,然后又是一幅实景描绘,再写填海后果,山中的草木七零八落。填海殃及的不仅是鱼龙,还有山中草木!作者明知故问的缘由进一步显现。
第四幅:“朝在树头暮海里,飞多羽折时堕水”。这幅图景是虚实结合,再写填海后果。虚写精卫因填海而奔波劳累、遍体鳞伤。“朝”“暮”多为想象,互文见义,但虚中有实,突出精卫奔波劳累;“口穿”“羽折“”堕水”为实写之词,实中有虚,写精卫的遍体鳞伤。对精卫填海的行为,作者是理解的,毕竟大海是造成悲剧的元凶;对精卫填海时所遭受的苦痛,作者是饱含悲悯之情的,毕竟精卫有仇报仇的血性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这四幅画面,写填海后果,也是作者悲悯之情的蓄积过程,从伤及无辜到自伤,填海的伤害达到极点,诗人的悲悯之情也达到了极点。
此诗通过描写一场突如其来的春雪,侧面写出了富人们在屋内赏雪以美酒相伴,穷人们却在雪天流落街头,形成鲜明对比,表达了对洛阳城中那班达官贵人只图自己享乐的讽刺。此诗是一首讽刺诗,但又不同于一般的悯寒诗或讽谕诗,诗中既无直呼,诗人用曲折的笔法,就自己特殊的观照角度,从写景中微示暗讽,发人深思。
“飞雪带春风”首句不说春风吹雪,却道是飞雪“带”春风。“带”字很普通,但用得突兀而精劲。飞雪先行,春风随后,可知是严冬刚过,春风初度,余寒犹厉的季节。第二句具写飞雪情状,字字都与写风糅合。“徘徊”写出雪片在风里轻缓地旋舞,又似乎冬寒还恋恋不肯即逝;“绕空”显出气流回荡中雪的整体动态,再用一个“乱”字,更给人纷繁迷茫之感,显然这初春的风雪也并不存心要给人间装点什么美景吧。从画面看诗情,作者此际没有沉浸于自然美的享受,心情似乎是低回、怅惘而烦乱的。
三、四句以“君看”一转,着笔于洛阳城东的雪景。作者只用“似花”一语状美。用花拟雪或用雪拟花,诗中常见,春雪尤其容易引起人们对春花的联想和期待,韩愈的同名诗篇中就有“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的好句。但作者此时却无意于“似花”之美,而专注于似花之“处”。与其说他产生了“似花”的美感,更不如说他是按审美经验设想着他人的赏雪快感——洛阳城东的阔人们正在把春雪当春花观赏作乐哩!两句写景是虚,抒感是实。用“君看”这个呼语力转,也正为此“君看”和“君不见”在旧体诗中常用来引起人们注某一含有深意的事物或景象,起提醒和强调的作用。如“君看石芒砀,掩泪悲千古”(李白《丁都护歌》),“君看一叶舟,出入风波里”(范仲淹《上渔者》)。
刘方平所触目动心之处的“洛城东”,是唐代东都洛阳贵族豪门的第宅园林集中的所在。初唐诗人刘希夷的《代悲白头翁》里“公子王孙芳树下”的赏花典型环境就是“洛城东”。春雪只有在这样的大片园林亭榭才能装点出奇艳的景观,也只有权豪贵眷才能金炉香兽,华筵美酒,无虞春寒,尽情观赏。第四句中一个“偏”字就着力点到了这种特殊条件和特有的兴致。“偏”字又与第二句的“乱”字关合:春雪本自乱绕乱落于人间,也竟如同专为豪贵作美,正是特殊的社会地位使他们得以偏享,长期隐居,“不乐仕进”的刘方平,以他较多的平民意识颇触着了人间不平的深处。
然而《春雪》又不同于一般的悯寒诗或讽谕诗。诗中既无“长安有贫者”(罗隐《雪》)那种直呼,也不作朱门白屋的对比,诗人只就自己特殊的观照角度,从写景中微示暗讽,发人深思。
此诗的开篇四句,便直接了当地表现战事,渲染了全国各地被紧张、恐慌的气氛所笼罩着,人们都在惊惧不安。“羽檄”,指上插羽毛的征调军队的文书,表示紧急;“虎符”,是朝廷调兵遣将的凭据,以铜刻作虎形,劈为两半,调兵时需二者验合。说“羽檄”像夜空里的流星一样快速地飞来,可见急上加急;说“虎符”在各州各郡一个个地合着。更见征调之多、频繁不已,边疆告急,形势紧张的情况则不言而喻了。继之“喧呼”一句,紧承前两句诗意,写出催迫应边之状。是谁在“喧呼”呢?诗中并没交代,但不难体会,这里既有传檄人的呼声,也有调兵长官的命令、嘈嘈嚷嚷,一片慌乱,以至连林中的鸟雀在深夜中为之惊动都鸣叫不已,则人之被惊扰不宁可以想见了。这几句诗,尽管没有描写刀光剑影相互拼杀的战斗场面,没有具体叙述官吏随便抓兵拉夫的情景,但却把紧张慌乱形势下,人们的惊恐之状和难以承受的心理负担和盘托出,起势有力,文辞奇挺,扣人心弦。
接着,犹如影、视镜头转换一般,“白日”以下四句诗,又展示了一幅升平安宁的画图。“白日”象征皇帝,“紫救”比喻朝廷;“三公”指太尉、司徒、司空,为朝臣中官位最高的,故合称“三公”。他们掌握着国家的命运,按道理说应该把天下治理得清明太平,借用老子的话就是“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即天下统一、四方安定。这里在颂扬以往承平的景象之中,暗暗谴责了当权者,通过前后鲜明的对照,对于征南诏的发动者策划者给予了讽刺,诗人和广大人民反对不义之战的思想自然地渗透其中,意蕴深刻、耐人寻味。
“借问此为何?答言楚征兵”。这两句是对以上诗意的具体说明,意思是:国家原来很安定。现在为什么陷入一片惊慌混乱之中呢?这完全是因为南侵而大肆征兵造成的。古时以“楚”泛指南方,“楚征兵”,即征讨南方的军队。这里运用问答的形式,不仅在句式上显得灵活变化,而且在前后意思的构架上也起到了勾联纽结的作用,可谓匠心独运。“渡泸及五月”,这个“泸”指金沙江,古时称“泸水”,相传江边多瘴气,以三、四月间最为厉害,五月以后稍好些,诸葛亮的《出师表》有“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之句。“将赴云南征”,这不仅是诗人的叙述,也表达了士兵的心情,他们听说要渡过泸水,去遥远的云南打仗,心头紧缩,都感到有去无回,很少有生还的希望。写到这里,诗人对统治者这样的穷兵黩武,而不顾惜人民的生命,感到异常愤概,充满不平之气,于是议论道:“怯卒非战士,炎方难远行”,意思是说,他们都是被抓来的百姓,没有经过阵势,是难以上战场的,更何况去边陲之地的云南呢?把李唐王朝驱民于死地的罪恶深刻地揭露出来了。
从“长号”到“心摧”四句,具体地描写了出征战士被迫离家时的悲惨情景。被抓去充军的人们,临行前和他们的父母、亲人告别,这是生的分离,也是死的作别,彼此号大哭,哭得日月无光,天昏地暗,直到哭尽了泪水,流出了血水,心肝摧断,两无声息。诗中连用“长号”、“惨”、“泣尽”、“心摧”,充满感情色彩,从听觉视觉上造成强烈效果,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展现了这种生离死别惨绝人寰的悲剧。
“困兽”四句,又是议论,以“困兽”、“穷鱼”喻没有战斗力的“怯卒”、以“猛虎”、“奔鲸”喻凶悍强大的敌人。在这样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势下,进行着扩边的战争,其结果是注定要失败的,众多的应征士卒,也只能白白地送死,“千去不一回,投躯岂全生”,葬身于沙场之上,成为统治者进行不义之战的牺牲品。这几句通过形象的比喻,适当的夸饰,对当权者的罪行给予了批判和控诉,也体现出诗人对广大人民的深切同情,闪烁着人道主义思想的光辉。
诗的结末两句,内容上又发展到一个深的层次,进一步地揭示了诗的主旨,表达了个人美好的理想和愿望。“如何舞干戚,一使有苗平”,“干”是盾牌,“戚”是大斧,以这两种兵器用在误乐上,表示行德政而不用征伐。“有苗”,古代部族名,传说舜时有苗叛乱,大禹建议用武力去征服他们,舜不同意,于是修明德政,三年以后,他举行了一次操舞盾牌、大斧的演习,有苗氏便归服了。诗人引用这个典故,正是暗讥“当国之臣不能敷文德以来远人”(萧士赟《分类补注李太白集》),动辄诉诸于武力,更加明确地表达了偃武修文、实现清明政治的美好愿望。显然这里的意思与“白日”以下四句的内容,是完全一致,相互呼应的。在结构上如此巧妙的安排,前后勾联、浑然一体,亦可见诗人艺术构思上的独到之处。
李白诗歌向以浪漫主义著称于世,这首诗在运用传说、夸张及想象方面,虽也体现出来了这些特点,但基本上是以写实为主的。叙的是实事,写的是实景,抒的是实情,并运用对比、问答手法,将描写、议论、抒情等巧妙地融合起来,达到了精湛的程度,这一点可以说是他的诗歌现实主义精神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