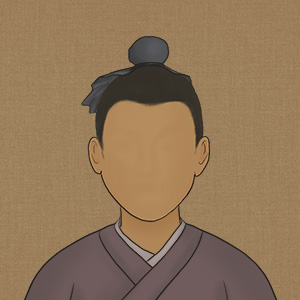起首两句是“兴”,即唤起。合浦(今属广东)指作者流寓之地,洛阳非实指,意思是合浦之杉叶尚能遥飞到洛阳,自己却流落异域,人不如叶。诗人知道岭南的杉叶飞到洛阳是不可信的,所以用“传闻”二字;然而愿望却在挑动诗人,并激发了诗人的想象力。虚幻与常识的起迭,失望与希望的对流,这种心理上的矛盾在乱世尤其表现得突出,因而这两句也有它的社会内容。
“北风”两句是对“传闻”两句的曲折承接,从南与北的地理的间隔上,又暗寓着南北朝在政治上的对立。树高千丈,叶落归根,这是诗人的迫切愿望,但国土的分裂使他无法实现这愿望,因而“南”、“北”这两个字,也成为诗人的敏感性的词眼。
前四句是诗人的独白,五、六两句才转入赠诗的对象。诗人和长安使之间应当有对话的,却以目送手挥来代替。诗人要着重表达的是离别时的情绪。这两句原是化用嵇康赠人诗的句意,但加上“徒送”的“徒”,就加强了感伤的效果。江总原来也是以使臣身分而到岭南,这时眼睁睁地望着长安使从他身边离去,自己却仍然留滞着。一去一留,其中就有多多少少要说的话,如同小河下面的潜流。
“秋蓬”句是比自己,“春草”句是说自己在客地已经度过几个春天。但春草的年年芳菲,徒然增添了自己的惆怅。《楚辞·招隐士》有“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句,唐代王维《送别》也有“春草年年绿,王孙归不归”句,用意都有共通处。
末两句以关山逗客子,以月光逗风尘:明月本是普照大地的,但对诗人来说,能够让光照到的也唯有衣衫上的风尘而已。
全诗前八句用比喻,对仗也很工整,却不雕琢,这一方面固然表现出作者的才力,一方面也因作者是南朝后期的人,诗的格律正在逐渐趋向成孰稳定。
宋朝程颢曾把《论语》的文章比做玉,《孟子》的文章比做水晶,认为前者温润,而后者明锐。一般说来,李白的诗偏于明锐而有锋芒的一路,但这首诗却气息温润,节奏和缓,真正做到了“大雅”的风度。
开首二句“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是全诗的纲领,第一句统摄“王风委蔓草”到“绮丽不足珍”,第二句统摄“圣代复元古”到最后“绝笔于获麟”。这样开门见山,分写两扇,完全是堂堂正正的笔仗。这两句虽则只有十个字,可是感慨无穷。这里的“大雅”并不是指诗经中的《大雅》,而是泛指雅正之声。雅声久矣不起,这是正面的意思,是一层。然则谁能兴起呢?“当今之世,舍我其谁?”落出“吾”字,表出诗人的抱负,这是第二层。可是诗人这时候,已非少壮,而是如孔子自叹一样“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即使能施展抱负,也已来日无多了,这是第三层。何况茫茫天壤,知我者谁?这一腔抱负,究竟向谁展示、呈献呢?这是第四层。这四层转折,一层深一层,一唱三叹,感慨苍凉,而语气却又浑然闲雅,不露郁勃牢骚,确是五言古诗的正统风度。
首两句点明正意以后,第三句起,就抒写“大雅久不作”了。春秋而后,以关雎麟趾王者之风为代表的诗三百篇已委弃于草莽之中,到了战国,蔓草更发展为遍地荆棘。三家分晋,七雄争强,虎斗龙争直到狂秦。四句一路顺叙下来,托出首句的“久”字,但如再顺叙下去,文气就未免平衍了,所以“正声何微茫”一句,用顿宕的问叹,转一口气。“正声”即是“大雅”,“何微茫”即是“久不作”,一面回应上文,一面反跌下句的”哀怨起骚人”。《诗经》本有“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说法,这里把屈原宋玉,归之于哀怨,言外之意,还是留正声于微茫一脉之中。屈宋都是七雄中楚国的诗人,论时代在秦以前,这里逆插一句,作为补叙,文势不平。于是再用顺叙谈到汉朝,“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说明扬雄、司马相如,继楚辞之后,在文风颓靡之中,激起中流,可是流弊所及,正如班固《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中所说:“竞为侈靡闳衍之辞,没其风喻之义”,和梁刘勰《文心雕龙·辨骚篇》所说“扬马沿波而得奇”一样,荡而不返,开出无边的末流。诗人写到这里,不能象帐册一般一笔一笔开列下去了。于是概括性地总束一下,“废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说明以后的变化虽多,但文章法度,总已沦丧。尤其“自从建安来”,三曹七子之后,更是“绮丽不足珍”,这与《文心雕龙·明诗篇》所说:“晋世群才,稍入轻绮”,“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大意相近。诗人反对绮丽侈靡,崇尚清真自然的文艺主张是显而易见的。诗写到这里,自从春秋战国直到陈隋,去古不可谓不远,写足了“大雅久不作”句中的“久”字,于是掉转笔来,发挥“吾衰竟谁陈”了。
“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这六句铺叙唐代的文运,诗人故弄狡狯,其实半是假话。唐代是近体律绝诗新兴的时代,未尝有所谓“复元古”。唐太宗以马上得天下,高宗、中、睿之间,历经武后、韦后之变,也不尝有所谓垂衣裳无为而治天下。王、杨、卢、骆、沈、宋的诗,虽各有胜处,但用“清真”两字,也只是李白个人的说法,而不足以代表初盛唐的风格。文才处休明之世,乘时运而飞跃,有如鲤鱼踊跃于龙门,繁星罗布于秋天。这里写唐代的进士科,比较真实,但唐代主要以诗赋取士,文胜于质,也未尝有所谓“文质相炳焕”。这些还是枝节的问题,如果唐朝统治者真能如李白这六句诗所写的那样,李白应该早就复兴“大雅”,重振“正声”,也不至于“吾衰竟谁陈”了。这六句与“吾衰竟谁陈”之间的矛盾,说明了诗人这六句是故布疑局,故意地正反相形的。所以下文从“众星”中跃出“吾”来,用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话,申说自己已无创作之意,只有把“废兴万变”之中的那些作品,像孔子删诗一般,把它整理一下,去芜存菁罢了,这样庶几还可以“垂辉映千春”。可是孔子毕竟不是仅仅删述而已,赞周易、删诗书、定礼乐之外,最后还是作了流传千载的《春秋》,直到哀公十四年猎获麒麟时才绝笔。诗人的抱负,亦正是如此。最后两句,从“吾衰竟谁陈”,“我志在删述”的较消沉的想法,又一跃而起,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的斩截之辞,来反振全诗,表示愿意尽有生之年,努力在文学上有所建树。诗人以开创一代诗风为己任,自比孔子,正说明他对自己期许很高。这一“立”字又遥遥与起句的“作”字呼应,气足神完,于是乎“大雅”又“作”了。
由于这首诗的主意在复振大雅之声,所以诗人在写作时,其胸襟风度,也一味的大雅君子之风,不能骏发飘逸,也不能郁勃牢骚,完全用中锋正笔。因此,即使在“吾衰竟谁陈”的慨叹之中,对当代有所不满,而只能以“圣代复元古”等六句正面颂扬之辞,来微露矛盾之意,这并非诗人故作违心之论,而是写这首诗的立场使然。千古以来,对此诗都是顺口随便读过,未尝抉出其矛盾之处的用心所在,未免辜负了诗人当时以此诗冠全集卷首的苦心了。
全诗一韵到底,音节安雅中和。最后两句,由于立意的坚决,音调也不自觉地紧急起来,“立”、“绝”、“笔”三个入声字,凑巧排列在一起,无意中声意相配,构成了斩钉截铁的压轴。
“为春瘦”三句,点明为“春情”而瘦矣。此言词人因春至而牵动相思情,并且被这“春情”缠绵得瘦弱不堪甚至比初春时,光零零的瘦削的梅花枝还有过之而无不及。词人说:不知道我的这份相思情,伊人(即“花”)知道不知道?“任枕函”两句,写孤寂状。言词人哀伤离别,独饮闷酒已至半醉,恰遇信使至。拿到这信函,想拆又怕看到里面的离别之言,所以更添一层愁绪,复又饮酒,不禁大醉。于是他就散乱着束发,枕着尚未打开的信函睡着了。“否声”四句,今别离昔欢聚适成对比。词人说:言在这初春的寒夜里,否声淅沥更使睡在小楼中的词人觉得寂寞难受,又想起我俩从前艳春时节,外出斗草、探花的欢娱时刻,真不啻天壤之别矣。上片重在描述词人自己的“春情”。
“娇懒”三句,转而述爱人的“春情”,这也是词人推己及人的想当然耳。言她白天时一定闲得无聊,勉强拿起绣针刺绣,不一会又走了神,背地里又惹起了无限相思。“玉合”四句,女人相思中的细节描绘。言伊人细心地用兰花膏浸渍起相思豆珍藏在玉合中,并将玉合放置在彩色绣花囊里;又因为两情分离,令她无心歌舞,所以将舞衣叠好藏起来,即使因此而损坏了舞衣上的泥金凤凰饰品,也顾不上了;她独自倚栏而呆思,忽见栏干边的柳枝已经发芽,心知春已来临,更激起她的妒春心情,所以恨恨地折断柳枝泄愤。这真有“忽见陌头杨柳色,悔叫夫婿觅封侯”(王昌龄《闺怨》)的意境,离别之苦,由此可见。“几多愁”一句,总合两地愁绪。词人说:我们俩的离愁别恨,就是因为被这眼前的春否,绵绵的远山分隔成天各一方啊!下片重在描述爱人的“春情”。
现存刘禹锡诗中有两首提到米嘉荣,另一首的题目写作《米嘉荣》,是此诗的初稿。《与歌者米嘉荣》,从反面落笔,于温柔敦厚中透愤懑不平,工巧新颖,深得风人之旨。
本首诗语言诙谐,写久负盛名的老歌手米嘉荣 年老了不受年轻一代重视的境遇,以需染胡须来迎合时尚戏之,隐含了诗人对朝中先辈受新贵排挤的激愤之意。
“唱得《凉州》意外声,旧人唯数米嘉荣。”句中《凉州 》是曲调名,原是凉州(今甘肃武威一带 )民歌,由唐玄宗时的西凉府都督郭知远进献朝廷。据记载,《凉州》在唐代宫廷中演出时,有人反对,说能引起“悖动之事”、“播迁之祸”,但也有人大声欢呼。可见,《凉州 》是具有意外之声、奇特之调的曲子。《凉州》曲调的不寻常,衬托着米嘉荣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技艺。“旧人唯数”,又从正面突出米嘉荣。因为,米嘉荣的技艺越高超,就越能赢得人们对他被冷落的同情。
最后两句笔锋一转,突出题旨。米嘉荣一身绝技,理当受人敬重,可社会上流行的风气是轻先辈重后生。诗中说:时世如此,您还是将就点,将白了的胡子染染黑,去伺候那些年轻人吧。劝慰之中,暗含着无限辛酸和诗人自己的愤世之情。被时人视作“宰相之器”的刘禹锡,由于政见不同而遭贬逐或投闲置散。如果要争取进用,就得放弃自己正确的政见,这就正像身怀绝技的老艺人“染髭须”去“事后生”。刘禹锡反对“时世轻先辈”,却奉劝人们“染髭须事后生”,这是忍着愤怒的温存,含着泪水的笑意,而自隐藏着讽刺的锋芒。这种手法,即所谓“正言若反”,于正中见反,于平和中见激荡,能使人体会到诗人的委屈,能激起人们更多的同情。老子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正说,有急切直率之嫌;反说,有尖锐泼辣之忌。只有这种正反结合的“ 正言若反”,可以化尖锐泼辣为含蓄蕴藉,化急切直率为委婉淳厚,使诗意更为隽永深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