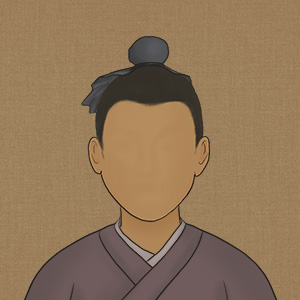这是一首咏物诗,咏物诗均有象征的意思,因为语言文字本身就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隐喻系统。隐喻的基础即人与自然的基本相似性。诗人总是不厌其烦地幻想我是树,是蝉,是鸟,是云等等,企图通过忘我、脱我、化我而与世界合一。隐喻建立在双重或多重存在之上,诗人喻自己为蝉,就是把另一种经历或活动,即把蝉的生存过程与特性加在真实的生活领域中,意味着真实中的虚幻,虚幻中的真实。像蝉一般象征廉洁、清高、悲哀。古人以为蝉栖高树,声高远,以晨露为食,蝉也就成了“清高”、“廉洁”的代名词。蝉一生十分短促,深秋天寒,蝉声哀嘶,逐渐死去,故而总被用来表达悲秋情绪。
刘勰说过一句言简意赅的话:“比类虽繁,以切至为贵。”隐喻虽多种多样,但要以贴切吻合为最高标准。“切至”就是形神兼备,形犹不似,遑论神似?在《赋得蝉》中,诗人将自然之物——蝉人格化,以此审视自身的人格价值和生存环境。对于这首诗,一般理解过程大致是,前两句直接描写蝉为了躲避黄雀的伤害(隐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典故),或藏身在高高的树枝上,或避匿在空空的宫殿内。这里实写了蝉艰难的生存状况。颔联和颈联写蝉在寒秋日暮之时,哀嘶悲鸣,声音短促,间或有单调的余韵绕耳,渲染了一种悲凉的氛围。最后两句借蝉之口直接抒写:蝉餐风饮露,无所厚求,并不是故作清高,而是容易知道满足,表达了一种知足常乐的意思。
然而,这只是构成了这首诗的表层含义,因为“饮露非表清,轻身易知足”中已经蕴含了知足常乐的意思。解读一首诗,肯定要注重其语境,什么是语境呢?用燕卜荪的话说,即“语境就是与我们诠释某个词语有关的一切事情。”文本中字或词意义的确定都要依赖于词句之间的关系,所以,一首诗句中意义的确定必然受到其它字词句的语境限制,即一首诗中每一个词、语句的意义都要彼此相互确定,这种相互确定的过程就使得文本的语义之间呈现网状化的现象,使文本的意义缠绕含混,蕴藉多义,仅凭读者从头到尾一次阅读,是不可能意识到其错综复杂的意义丛的。
认真阅读,全诗处处写蝉,实际是处处写自己,让人有一种悲哀之感。那么,我们又是怎样获得这样的深层意义和感受的呢?只要回到首联去感知,就会发现“避雀乔枝里,飞空华殿曲”很难解释,也就是说,很难和知足常乐联系起来。而知足常乐也很难和中间两联的“天寒”、“响屡嘶”、“日暮”、“声愈促”等联系起来。所以,后三联对蝉原本的意义和声音的描述,在首联大背景暗示下,发生了变化,产生了言外之意,变成了诗人对自己生存境况的深深的忧虑。中间两联写蝉声,不仅仅渲染了一种悲凉的氛围,而且还寄寓了对生命流逝的伤感以及对自己处境艰难的悲哀之情。尾联诗人以蝉自喻,蝉栖高树,饮晨露,不是为了故意显示自己的清雅高洁;自己为官清廉,也非故意显示与众不同,而是自己知道知足常乐;但“知足”这个词语来自于《老子》,“祸莫大于不知足”,由于有了首联实写的提示,可见诗人在“知足”背后潜藏着一种悲哀,在悲哀中还杂糅着一种畏祸的心态,隐含的意思是知足为避祸全身。这首诗的意义就是这样相互生成的。
李昂(即位前名李涵)在位十四年。他登基后宦官一直专权,甘露事变后他更是失去了人身自由,一生软弱,郁郁而终。他工于五言,诗风清俊有骨气。这和他的性格似乎不大一样。也许李涵本人也不是糊涂昏庸之辈,不过是唐王朝末期国家颓败的气数使他没有更大的作为罢了。
对于宫廷除了皇帝没有谁更有发言权了。这是一首先写景转而直抒胸臆的诗。
从诗的内容上看,这首作品应该写于甘露事变之后。路边的秋草和上林苑里的繁花相比,既不美丽,又不茂盛,只是平平凡凡的野草,而且这秋草是不起眼,没有人注意的道边草罢了。秋风一过,秋草只能随风而倒,全没有坚定自主的力量。所以看似在写宫中的一般气象,实际也说明了文宗只是个傀儡而已。后面的诗句里就带着骨气了,他宁愿凭高无限意的生活下去,而不稀罕整日复同侍臣的虚假君主生活。
就算御花园是天下最美的花园,但是文宗皇帝是不贪图这将要凋零的美丽的,他心中的理想是按照自己的意愿登上统治者的高位,而不是做一棵依附于宦官的墙头草。王室的后代能有这样的理想,也算难能可贵了。唐代末期混乱的局势下,李姓王室已经处于了衰颓中。诗的开头说辇路上长起了秋草,这是不应该的,宫人连起码的除草工作都不认真对待了,可见王室的没落程度。这时候的文宗皇帝可能只有说说心中理想的权力了,要真的振兴唐王朝似乎仅是空想了。文宗远大的理想可贵在还没有忘记昔日先人打下的江山,但是这只能被理解为文宗身上有着贵族的骨气,他一个人是不能实现如此艰巨的目标的。其实他就是一个空想家。
他的心理后人是应该理解的,长期受人摆布,连人身自由都成问题的文宗皇帝很难抒发自己的苦闷。这首作品的立意还是有它的高明之处的。文字上抓住了宫廷的特点,像上林苑、辇道、侍臣,都是宫廷特有的。宫中题,表现在环境上,也是宫中人生活的写照。
宫廷除了它应有的繁华,热闹,也有许多神秘的黑暗面。书籍里也曾记载了许多宫廷中阴险复杂的倾轧,宫廷斗争历来是最危险的斗争,连皇帝本人都深陷这种漩涡的时候,一个王朝就处于深深的危机当中了。
金山是江南名胜,地处今江苏镇江西北。原在长江中,后因砂土堆积,到清末便与长江南岸相连。据宋人周必大说,此山大江环绕,每风起浪涌时,其势欲飞动,故南朝时人称“浮玉山”(见《杂志》)。唐时有裴姓头陀于江边拾得黄金数镒,因改名金山。
此诗四句四景,合成一幅金山晚眺的优美图景,十分清丽。前半部分是并列的两句,分写江上的明月和蒙蒙的水气。西津在镇江西北九里,与金山隔水相望,是当时南北交通要道。诗人站于金山之颠,西向遥望,只见一轮新月,悬于西津渡口之上;江上水气,非烟非雾,正冉冉升起,几与天接。烟水迷蒙,使皎皎明月也蒙上了-层淡淡的云翳。这两句明暗交错,上下相对,不仅使画面具有明显的层次,而且避免了色调上的不和谐。“西津江口”四字,既点明“晚眺”方向,又划定了所见景色的区域。“月初弦”三字也有双重功用,既是写景,又是记时这种借星月在天空中位置移动和形状变化来点明时间的手法,古人诗中常用,远如曹植的《善哉行》:“月没参横,北斗阑干。”近如唐代刘方平的《夜月》:“北斗阑干南斗斜。”机杼正自相同。
诗的后半部分是相对的两句。“清渚”、“白沙”,则写出了月下之景。“清渚白沙茫不辨”是承前一句“水气昏昏上接天”而来。白天从金山眺望西津渡,对岸景物是可以看清的,唐代诗人张祜有“树影中流见,钟声两岸闻”(《题金山寺》)之句;但此时既已入夜,又有水气,诗人眺望的结果只能是“茫不辨”了。“只应灯火是渔船”作一转折:尽管对岸清渚、白沙,望去茫茫一片,但透过水气,还能看到江上灯火,隐现明灭,诗人因此判断道:那一定是对岸的渔船了。诗人在这两句中运用了反接法,便使诗句显得摇曳生姿,别具风调,比前两句的平叙景色更引人入胜。元人刘壎在《隐居通议》中说:“作绝句,当如顾恺之啖蔗法,又当如饮建溪龙焙。”也就是说,绝句不能“虎头蛇尾”,而要“渐入佳境”。这首《金山晚眺》正体现了这一要求。
此诗脱胎于张祜的七绝《题金陵渡》:“金陵津渡小山楼,一宿行人自可愁。潮落夜江斜月里,两三星火是瓜洲。”只要稍加比较,就能看出秦观诗至少在三个方面与张祜诗相同:一,时间和地点相同,都是写镇江江面的夜间景色;二,描写手法相同,一用“潮落”、“斜月”来暗示时间的推移,一用“月初弦”来点明时间;三,境界相似,秦观诗中的“只应灯火是渔船”是化用了张祜诗的“两三星火是瓜洲”以及张继《枫桥夜泊》中的“江枫渔火对愁眠”。由此可见秦观这首诗的出处。但张祜诗明写了诗人的羁旅之愁,属触景生情,形象地表达出诗人夜不成寐的情形,而秦观诗没有直接抒写诗人的情感,而是将情感蕴涵在所描写景物之中,景中含情。这又是二者的同中之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