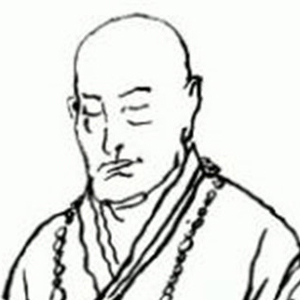年年客里故人多,饮水逢君朱颜酡。
鹊去鸠来有空屋,牝乳雏飞无啄粟。
香火飘零甘死休,无辜怜我兄遭戮。
暗中魑魅籍姓名,我有朋俦等不足。
十事上心九事忘,一日囘首千日长。
谁登百丈岭,我到钟山傍。
登堂拜丘嫂,推手戏诸郎。
诸郎挽衣幼女亲,汝母磊落如吾人。
哀我若见韩氏孤,敬我宁知苏子贫。
吁嗟尺市谣,空道天属真。
年年客里故人多,饮水逢君朱颜酡。
鹊去鸠来有空屋,牝乳雏飞无啄粟。
香火飘零甘死休,无辜怜我兄遭戮。
暗中魑魅籍姓名,我有朋俦等不足。
十事上心九事忘,一日囘首千日长。
谁登百丈岭,我到钟山傍。
登堂拜丘嫂,推手戏诸郎。
诸郎挽衣幼女亲,汝母磊落如吾人。
哀我若见韩氏孤,敬我宁知苏子贫。
吁嗟尺市谣,空道天属真。
诗的前四句着力描绘岳阳楼周围景色;后四句承接前四句抒发身世之感,家国之恨的感慨。纵观全诗,诗人俯仰今古,伤时感世,含蓄深远,气象浑厚,格调沉郁。
诗的前四句,诗人着力描写岳阳楼周围的景观特征。在初登岳阳楼之时,诗人注意到了楼之地理方位:“洞庭之东江水西驴(《登岳阳楼》);再次登临,诗人选择最佳观察角度,站在楼之西北角。从这一角度望出去,北面是浩浩长江,江风阵阵,浊浪腾涌,一往无前;江边长堤,曲折蜿蜒,连绵不断。西南面则是碧波千顷的洞庭湖,波光潋滟,湖岸草木葱茏,相连不绝,一直延伸到穷荒僻远的南方天边。江水浊黄,湖水清碧,对比强烈,异态纷呈。
面对此景,诗人凭栏良久,自身迁谪之恨、国家兴衰之感,不觉一齐涌上心头。万千感慨、诸种情怀,凝成掷地有声的一联诗句:“乾坤万事集双鬓,臣子一谪今五年。”作者从谪监陈留酒税以来,迄今已有五年了。五年之中,发生太多的变化。国无宁日,人无宁日。靖康之难,宋室南迁,诗人颠沛流离,到处流浪。是年,诗人仅三十九岁,但头发却已愁白了,真是天下之事、迁臣之恨都反映在双鬓之上。作者壮年头白,确是实写,非是夸张,同年所作诗曾多处提到。如《登岳阳楼》云:“白头吊古风霜里,老木苍波无限悲。”《巴丘书事》云:“腐儒空白九分头。”《晚步湖边》云:“终然动怀抱,白发风中搔。”可见诗人此时的景况确同杜甫一样:“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陈衍《宋诗精华录》盛称“乾坤”一联为“学杜而得其骨”者,为家国之忧而心碎,而头白,正是杜诗与陈诗共具的思想特色。
此时,诗人思绪缥缈。登高怀古,乃题中应有之义。诗人联想到古往今来,与自己遭际略同的不止一人。昔时,汉代的贾谊被贬长沙,途经湘水,曾作赋以吊屈原。尾联所谓“欲题文字吊古昔”,即指此事。然而,作者此时的处境却比贾谊更坏,心境也比贾谊更劣。所以,即使像贾谊一样抒发吊古之情,也感到力不从心,难于下笔。于是只得面对风壮浪涌的长江、洞庭而茫然无语了。
为了表达欲语又止、抑塞难堪、郁戾不平的思想感情,此诗采用了拗体格律,音节拗怒,陡折峭拔,与老杜《白帝城最高楼》等拗体律诗格调相同。王嗣爽曾评杜甫拗体诗说:“愁起于心,真有一段郁戾不平之气,而因以拗语发之。公之拗体,大都如是。”(《杜臆》卷七)此说简斋亦足以当之,不愧“学杜而得其骨者”也。
词精粹警拔,甘之如饴。上片四句,前两句写景,后两句抒情。写景清冷空寂,抒情韵悠意远。“路远人还远”前冠“因惊”,遂上精警拔俗之妙。所谓“人还远”,即人更远也,即心远也。与欧阳修“平荒尽出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用意想埒。只是欧词是从闺妇感受言之,柳词则以行人心会出之。俱可称俊语。
下片妙在后两句,前生有缘爱自可相期,是自慰语,也是祝祷语,更是期待语,语“愿天下有缘上都成了眷属”词异意同,它使全词拔高了一个音节,可堪细味。《全宋词》此词调名下唐圭璋括注一行小字曰:“案此首调名原作《瑞这股》,非,今按律改。”
这首诗的作者热情地塑造出一个襟怀嵚崎磊落,慷慨豪勇,报恩酬知己,不畏死难的剑客形象,借以寄托自己的人格理想 。真可谓志陵山岳,气吞江海, 撼人心魄。
开头两句凌空起笔,描写饯别的场面和剑客的出门。酒宴将散 ,剑客的豪兴借酒而发,遂拔剑起舞, 慷慨高歌 ,歌罢出门,扬长而去。“拔剑”二字点出 剑客的身分,一个“绕”字,隐写剑客且歌且舞的场面,十分生动传神。我们可以想见,酒酣之际,拔剑起舞,旁观者可以一睹剑客高超的剑术及风采;舞剑作歌,人们又可以从其歌词中了解其超凡脱俗的情怀,在情绪上深受感染;而剑客高歌方罢,不顾而去,态度是那样毅然决然,毫无留恋之态,表现出一副大丈夫的英雄气概,又该是何等令人赞叹。这里,“歌终”的“终”字和“便”字的衔接使用,极见功力。应该说仅此开头二句 ,剑客英雄豪迈的形象已跃然纸上。 三、四句描绘此剑客出门之后,踏上行途的景象。
“西风满天雪”,这是北方冬季的大自然特有的最雄浑壮丽的画图。诗人把剑客放到如此西风狂啸,漫天大雪纷飞的背景衬托之下,有力地烘托出剑客的英雄气质 。风雪茫茫,天地浩大,中有一人,持剑独立, 瞻视前路..,那该是怎样的形象,如何的气度!更妙的是 ,作者还要对剑客问上一句“何处报人恩”, 意思是说,这样大的风雪,连道路都难以识别,你到哪里去替你的恩人寻仇找敌为他报仇,来报答他对你的知遇之恩呢?表面上这是对剑客的置难之词,却是赞扬他下定决心,不为风雪所阻,不辞艰苦,一定要达到目的的坚定信念。
接下“勇死寻常事,轻仇不足论”二句,正面议论;点出此剑客固然可以为酬知己而勇赴死难;但他也决不是那种气量狭窄,为睚眦之怨而轻生舍命的亡命徒。这里强调了剑客的有胆有识,襟怀开阔,使其思想境界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但这两句的妙处还不仅在于此,它又暗示了此剑客的外出“报人恩”,是一次重大的有意义的行为。
最后,全诗以“翻嫌易水上,细碎动离魂”作结,赞扬此剑客的豪气更在战国时代为燕太子丹去行刺秦王的荆轲之上。荆轲的勇敢事迹见于《史记·刺客列传 》,书中描写太子丹及其宾客在易岸送别荆轲的场面 ,历来脍炙人口:“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 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
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 ,壮士一去兮不复 还 !’复为羽声忼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而此剑客却嫌荆轲的反复悲歌,感伤别离,感情未免过于细腻缠绵了,可见二人比较,自有高下之分。
齐己是一位僧人,这首诗写得这样豪壮刚猛,肝胆照人,可见他并未完全心归禅寂,超然物外。
这是一首慨叹人情冷暖的诗作。表面上看,全篇既没有精彩的警句,也很少有环境氛围的艺术描绘,似乎是平平淡淡、语不惊人;实际上它以“直说”见长,指事状物,浅切形象;信口信手,率然成章;言近旨远,发人深省,别具一种淡而有味的诗趣。
全诗结构紧凑,层次分明,步步围绕主题,写得颇有情致。首段六句,作者以概述的笔调,指出妻室儿女态度好坏的关键在于一个“钱”字。拥有钱财时,一切都好,妻室儿女也显得十分殷勤。假如要脱衣服,很快就会有人把脱下的袍袄折叠得整整齐齐;假如离家出外若商,还要一直送到大路旁边。诗人在这里选取习见的生活现象,以凝炼的笔触,不加修饰地叙写出各种场景,给人以平凡而生动的感觉。
接着,作者利用贴切的比喻,进一步刻画出金钱引起的种种媚态:“将钱入舍来,见吾满面笑。绕吾白鸽旋,恰似鹦鹉鸟。”当携带金钱回到家中时,他们一个个笑脸相迎,像白鸽那样盘旋在周围,又好似学舌的鹦鹉在耳边喋喋不休。人们向来把鸽子当成嫌贫爱富的鸟类,而鹦鹉则被视作多嘴饶舌、献媚逢迎的形象。因此诗人用“白鸽”、“鹦鹉”来比喻见钱眼开的贪财者。
最后六句,概括全篇主旨,也是王梵志对世情险薄的愤激之语。句中的“邂逅”、“貌哨”,皆为唐人口语。这几句诗中,作者直率地警告那些庸俗的贪财者,如果只为贪图钱财,而毫不顾及人的情义,那就要看看来时的报应了。这里,诗人率直地写下了他的愤激之情。
这首诗在艺术表现上明显的特点是:以锐敏的观察力捕捉生活中某些不大为人重视的动作和事理,运用通俗凝炼的语言,设想奇巧的对比描写,着墨不多,无意于渲染,但是那种贪钱者的丑态便跃然纸上。与此同时,诗人的不平之气也豁然而出。作者利用比较娴熟的驾驭民间语言的能力,出语自然,质直素朴,言近旨远,从而开创唐代以俗语俚词入诗的通俗诗派,为唐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