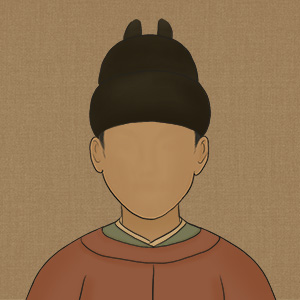首三句从时间的推移下笔,起句写斗转星移、玉漏频催,已由“月上门”到“三更天”了,女主人把视线由室内的云母屏风移到室外栖息的黄莺身上,不仅表示时间的推移,而且是感情的升华。她等待的情人,未到约定的兰更而不来,她虽然急不可待,但还能自解。这一句用“转“、“移”、“频”连续三个动词表达少女对时光流逝的焦虑,以异于常人的感觉来表现她的炽热感情,给读者留下强烈而深刻的印象。独坐三更,面对栖莺,女主人公的情思是可以推知的。她会由夜莺都已栖息联想到自己还不能与所期待的潘郎相会,而有感于人不如鸟,由愁而怒。女主人公的遐想幽思可以是无边无际的,她的忧愁怒情也看似无穷无尽。
但下两句却一下子打破了静夜的沉闷空气,扫去了她心头的重重愁云和脸上的怒容,成为全词的起伏、转折之点。“已三更”时她仍然还在倾听着马嘶声。不过,此刻从花间小路上传来的不是老远就可听到的马嘶声,而是近处才可听到的马蹄声。这分明是她一直盼望听到的声音。末尾三句则急转直下:盼望已久的潘郎终于骑马疾驰归来,女主人公欣地的整理好衣服头饰,打开门户,轻快地走出房门,走下台阶到庭院相迎,从而结束了大半夜的期望与等待。
这首词与前一首都采用了直陈其事的手法,通过自然景物和人物一系列动作的描绘,展示了青年男女密约幽会的动人意境。在细节和心理描写上,细腻、生动、逼真,因而人物形象非常鲜明,真有呼之欲出之感。
首句“觥船相对百分空”写觥船送别。在船上依依话别,对饮离杯,回首当年,真有百事成空之感。次句“京口追随似梦中”追忆京口旧游。当时陆游任镇江通判,恰好诗人来镇江省亲,两人同游金山,互相酬唱。一年后,诗人改任京官,又来镇江同游,与陆游有京口唱和一集,“道群居之乐,致离阔之思。”而诗人现在回想起来,往事竟像在梦中一样。这两句寄慨深沉,为全诗定了基调。
“落纸云烟君似旧”一句称誉陆游,言他虽然入蜀多年,而诗风慷慨,挥毫染翰,满纸云烟,气魄雄劲,不殊昔日。“盈巾霜雪我成翁”则感叹自己此刻已满头霜雪,在国事艰虞之秋,未能多为国家宣劳,匡扶时局,现在已经成为老翁了。这两句分别写两人当前的情况,表达了彼此都有壮志未酬的感慨。
接着五六两句,笔锋一转,借景抒情。“春来茗叶还争白,腊尽梅梢尽放红。”诗人设想陆游到福建的时候,已是下一年的春天,那里的白叶茶,该争先吐出白色的芽叶了。而在此刻分手之际,已经腊尽春回,红梅好都已迎年开放一片嫣红了。这两句笔姿潇洒,深见诗人旷达的胸怀,不专为别情所牵恋;而情景交融,不落凡响。结尾两句“领略溪山须妙语,小迂旌节上凌风。”再振一笔,以慰行人,并回映前文,有余音绕梁之妙。诗人和陆游在壮年的时候,都曾任官闽中,陆游开始做官的时候,任福州宁德县主簿,那时正当秦桧死后,陆游年三十四岁,诗人也曾任过建安守。彼此对闽中溪山之胜,是非常熟悉的。现在陆游再度任官福建,旧地重来,已经相隔二十年了。所以结笔前一句是希望友人把妙笔重新点染那里的溪山。诗人守建安的时候,曾登过那里的凌风亭,建安地近福州,所以在结句“小迂旌节上凌风”语意双关,希望陆游此去福州,不妨稍为迂回一下道路,登上凌风亭,一访那里的胜景,那么诗人虽然未能同行,也可以因友人访问自己的旧游地而一慰平生了。
这首送别诗,从十几年前写到赴任以后,有感慨,但不颓唐,对未来有展望,但不虚发豪言,而且情感特别真挚。
此词为苏轼于熙宁五年(1072)至七年在杭州通判任上与当时已八十余岁的有名词人张先(990-1078)同游西湖时所作。
作者富有情趣地紧扣“闻弹筝”这一词题,从多方面描写弹筝者的美丽与音乐的动人。词中将弹筝人置于雨后初晴、晚霞明丽的湖光山色中,使人物与景色相映成趣,音乐与山水相得益彰,在对人物的描写上,作者运用了比喻和衬托的手法。
开头三句写山色湖光,只是作为人物的背景画面。“一朵芙蕖”两句紧接其后,既实写水面荷花,又是以出水芙蓉比喻弹筝的美人,收到了双关的艺术效果。从结构上看,这一表面写景,而实则转入对弹筝人的描写,真可说是天衣无缝。据《墨庄漫录》,弹筝人三十余岁,“风韵娴雅,绰有态度”,此处用“一朵芙蕖开过尚盈盈”的比喻写她,不仅准确,而且极有情趣。接着便从白鹭似也有意倾慕来烘托弹筝人的美丽。词中之双白鹭实是喻指二客呆视不动的情状。
下片则重点写音乐。从乐曲总的旋律来写,故曰“哀筝”,从乐曲传达的感情来写,故言“苦(甚、极的意思)含情”;谓“遣谁听”,是说乐曲哀伤,谁能忍听,是从听者的角度来写;此下再进一步渲染乐曲的哀伤,谓无知的大自然也为之感动:烟霭为之敛容,云彩为之收色;最后再总括一句,这哀伤的乐曲就好像是湘水女神奏瑟在倾诉自己的哀伤。湘灵,用娥皇、女英之典故。词写到这里,把乐曲的哀伤动人一步一步地推向最高峰,似乎这样哀怨动人的乐曲非人间所有,只能是出自像湘水女神那样的神灵之手。与此同时,“依约是湘灵”这总绾乐曲的一句,又隐喻弹筝人有如湘灵之美好。词的最后,承“依约”一句正待写人,却又采取欲擒故纵的手法,不仅没有正面去描写人物,反而写弹筝人已飘然远逝,只见青翠的山峰仍然静静地立在湖边,仿佛那哀怨的乐曲仍然荡漾在山间水际。“人不见,数峰青”两句,用唐代诗人钱起《省试湘灵鼓瑟》诗“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是那样的自然、贴切而又不露痕迹。它不仅意象动人,而且在结构上还暗承“依约是湘灵”一句,把上下用典结合起来。“数峰青”又回应词的开头“凤凰山下雨初晴”描写的雨过山青的景象,真可谓言尽而味永。
此诗可分为四段。每段都是以“笑矣乎”开头。第一段,诗人化用汉代童谣。“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来讽刺是非错位、黑自颠倒的丑恶社会现实。接着举了战国时张仪、苏秦的例子来说明“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的现象。张仪和苏秦是战国时有名的纵横家。他们凭着三寸不烂之舌,权诈之术,取得了人主的信任。张仪曾作过秦国的丞相,而苏秦却能佩六国相印,成了纵约长。他们都凭着“曲如钩”的本领,成了显赫一时的权贵。如果他抱诚守直,老老实实在家种地的话,说不定他们早就饿死在道边了。李白的这些诗句,借古讽今,旨在揭露当时国君昏聩,才使得象张仪、苏秦那样朝秦暮楚、反复无常的小人,一个个受宠得势,而象自己守直不阿的人,却只能作阶下囚了。
由于李白自己将社会看透了,认为不值得为统治者卖命卖力,思想反转为出世。第二段就写出了这种思想的转变。“君不见”四句,借用《楚辞·渔父》的典故,先写那位“避世隐身” 、“欣然自乐”的渔父,后写抱直守忠的屈原。屈原被楚王放逐,行吟泽畔,遇到了隐者渔父。渔父劝他和光同尘,与世推移,而屈原要坚守正义,正道直行,不愿“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宁赴湘流,葬身子鱼腹之中,也不愿“以皓皓之自,而蒙世之尘埃。”渔父听完后:“荛尔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君足’。遂去,不复言。”李白在这里以调侃的口气,表面上是奚落屈原“平生不解谋此身,虚作《离骚》遣人读”,其实骨子里是对现实社会的冷嘲热讽。在“曲如钩”的社会里,正直如屈原的人,是没有立足之地的。还不如学沧浪老人,“避世隐身”为好。
第三段,诗人运用豫让、屈平、巢父、许由、伯夷、叔齐等古人以不同方式求得“身后名”,深入展开议论。屈平自投汨罗,博得“以身殉国”的美名。豫让,春秋时晋国人,为智伯多次行刺赵襄子未遂而自杀,成为历史上著名的“刺客”。巢父和许由为古代著名隐者,传说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听后,认为有污自己的耳朵,便逃到颖水边洗耳,当时,巢父正牵犊饮于下流,就责怪许由污其犊口,遂牵犊到上游。伯夷、叔齐为殷朝末年孤竹国君之子,武王伐纣之后,不食周粟而饿死,被孔子称为“古之仁人”。但是,诗人认为这些古人都是为“爱身后名”的奴役,不如“我爱眼前酒”。这个中的妙理在于“饮酒眼前乐”是实实在在的,“身后虚名”则不是。“男儿穷通”自有机遇,不必强求,即使求得“身后名”,死后人们弯腰向你礼拜,你也不知道了。这一“虚”一“实”的反差,正是李白的牢骚话。“自古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李白《将进酒》)诗人正是以这种惊世骇俗的牢骚话博得千古美名。诗人借用猛虎不屑一顾案头肉和洪炉不熔铸囊中小锥进行类比反衬,表现自己不汲汲于“身后名”的傲骨和大志,嘲笑那些贪图靠“身后名”者不过是些心底狭窄之辈!
最后一段,又以宁武子和朱买臣宕起一笔。宁武子,即宁戚,春秋齐人,有奇才,隐于商旅,齐桓公夜出巡访,他正在喂牛,并击牛角而歌唱,桓公闻而奇之,委以重任。朱买臣,西汉人,家贫,以卖柴为生,好读书,能朗诵《楚辞》,后被汉武帝征用。诗人用这两个古人的事迹,旨在说明穷通有时,应该顺其自然,从而嘲讽那些被“曲如钩”者迷惑了心窍的当权者,即是遇到宁、朱二人,也不会了解他们,他们也只好去佯狂避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