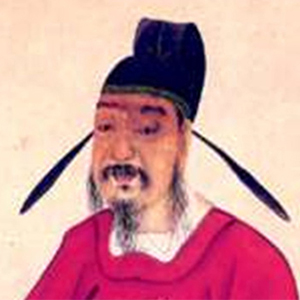咏物诗词一般以咏物抒情为主,绝少议论。李清照的这首咏桂词一反传统,以议论入词,又托物抒怀。咏物既不乏形象,议论也能充满诗意,堪称别开生面。“暗淡轻黄体性柔,情疏迹远只香留。”短短十四字却形神兼备,写出了桂花的独特风韵。
上句重在赋“色”,兼及体性;下句重在咏怀,突出“香”字。据有关记载,桂树花白者名银桂,黄者名金桂,红者为丹桂。它常生于高山之上,冬夏常青,以同类为林,间无杂树。又秋天开花者为多,其花香味浓郁。色黄而冠之以“轻”,再加上“暗淡”二字,说明她不以明亮炫目的光泽和秾艳娇媚的颜色取悦于人。虽色淡光暗,却秉性温雅柔和,像一位恬静的淑女,自有其独特的动人风韵。令人爱慕不已。她又情怀疏淡,远迹深山,惟将浓郁的芳香常飘人间,犹如一位隐居的君子,以其高尚的德行情操,赢得了世人的敬佩。
“暗淡轻黄体性柔,情疏迹远只香留。”形神兼备地写出了桂花的独特风韵。她的颜色并不艳丽,“暗淡轻黄”,与很多名花相比,外表逊色得多。她的社会声望也很一般,“情疏迹远”,并没有得到什么荣耀和宠幸,更不会有人给她热捧恭维。但是她的体性温柔,香留天地之间。
“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从这两句起直至歇拍,都是以议论的方式行文。这两句是议论的第一层。花当然是以红为美的。至于碧牡丹、绿萼梅之类,那就更为名贵了。这些都是桂花没有具备的。但是作者认为,内在美,比外在美更为重要。“何须”二字,把各种名花一笔荡开,突出了色淡香浓、迹远品高的桂花,断定她是“花中第一流”。
“梅定妒,菊应羞,画栏开处冠中秋。”这是议论的第二层。梅花既有妍丽的外美,更有迎霜雪而开的高洁的内美。菊花更是人所共同认可的“君子之花”,兼具内外之美。但是这两种名花,在桂花的面前都自叹不如,都产生了羞愧和妒忌的心理。经过这样的比较抑扬,桂花的定位就很清楚了。所以作者论定:桂花是众多的秋季名花之冠。
“骚人可煞无情思,何事当年不见收。”这是议论的第三层。“骚人”,指屈原。屈原在《离骚》中,用褒扬之笔,列举了各种各样的香草名花,以比况君子修身美德,可是偏偏没有提到桂花。所以作者抱怨他“可煞无情思”。屈原的人品和才德,是人所共同景仰的,这也包括作者李清照在内。对这位先贤的抱怨,更突出了作者对桂花的珍重。
李清照的这首咏物词咏物而不滞于物。草间或以群花作比,或以梅菊陪衬,或评骘古人,从多层次的议论中,形象地展现了她那超尘脱俗的美学观点和对桂花由衷的赞美和崇敬。桂花貌不出众,色不诱人,但却“暗淡轻黄”、“情疏迹远”而又馥香自芳,这正是词人品格的写照。这首词显示了词人卓尔不群的审美品味,值得用心玩味。
“巴江上峡重复重”,诗中明显有一舟行之旅人的影子。沿江上溯,入峡后山重水复,屡经曲折,于是目击了著名的巫山十二峰。诸峰“碧丛丛,高插天”(李贺《巫山高》),“碧峭”二字是能尽传其态的。十二峰中,最为奇峭,也最令人神往的,便是那云烟缭绕、变幻阴晴的神女峰。而“阳台”就在峰的南面。神女峰的魅力,与其说来自峰势奇峭,毋宁说来自那“朝朝暮暮,阳台之下”的巫山神女的动人传说。次句点出“阳台”二字,兼有启下的功用。经过巫峡,谁都会想起那个古老的神话,但没有什么比“但飞萧萧雨”的天气更能使人沉浸于那本有“朝云暮雨”情节的故事情境中去的。所以紧接着写到楚王梦遇神女之事:“荆王猎时逢暮雨,夜卧高丘梦神女。”本来,在宋玉赋中,楚王是游云梦、宿高唐(在湖南云梦泽一带)而梦遇神女的。而“高丘”是神女居处(《高唐赋》神女自述:“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一字之差,失之千里,却并非笔误,乃是诗人凭借想象,把楚王出猎地点移到巫山附近,梦遇之处由高唐换成神女居处的高丘,便使全诗情节更为集中。这里,上峡舟行逢雨与楚王畋猎逢雨,在诗境中交织成一片,冥想着的诗人也与故事中的楚王神合了。以下所写既是楚王梦中所见之神女,同时又是诗人想象中的神女。诗写这段传说,意不在楚王,而在通过楚王之梦来写神女。
关于“阳台神女”的描写应该是《巫山曲》的画龙点睛处。“主笔有差,余笔皆败。”(刘熙载《艺概·书概》)而要写好这一笔是十分困难的。其所以难,不仅在于巫山神女乃人人眼中所未见,而更在于这个传说“人物”乃人人心中所早有。这位神女绝不同于一般神女,写得是否神似,读者是感觉得到的。而孟郊此诗成功的关键就在于写好了这一笔。诗人是紧紧抓住“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高唐赋》)的绝妙好辞来进行艺术构思的。
神女出场是以“暮雨”的形式:“轻红流烟湿艳姿”,神女的离去是以“朝云”的形式:“行云飞去明星稀”。她既具有一般神女的特点,轻盈飘渺,在飞花落红与缭绕的云烟中微呈“艳姿”;又具有一般神女所无的特点,她带着晶莹湿润的水光,一忽儿又化成一团霞气,这正是雨、云的特征。因而“这一位”也就不同于别的神女了。诗中这精彩的一笔,如同为读者心中早已隐约存在的神女撩开了面纱,使之眉目宛然,光艳照人。这里同时还创造出一种若晦若明、迷离恍惝的神秘气氛,虽然没有任何叙事成分,却能使读者联想到《神女赋》“欢情未接,将辞而去,迁延引身,不可亲附”及“暗然而暝,忽不知处”等等描写,觉有无限情事在不言中。
随着“行云飞去”,明星渐稀,这浪漫的一幕在诗人眼前慢慢消散了。于是一种惆怅若失之感向他袭来,“目极魂断望不见”就写出其如痴如醉的感觉,与《神女赋》结尾颇为神似(那里,楚王“情独私怀,谁者可语,惆怅垂涕,求之至曙”)。最后化用古谚“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作结。峡中羁旅的愁怀与故事凄艳的结尾及峡中迷离景象打成一片,咀嚼无穷。
全诗把峡中景色、神话传说及古代谚语熔于一炉,写出了作者在古峡行舟时的一段特殊感受。其风格幽峭奇艳。语言凝练优美,意境奇幻幽艳,余味无穷。
这首词大约是作者北宋首都汴京留别友人之作。全词以别易会难为主旨,上片写留饮,下片写惜别。
开篇写作者满斟绿色的美酒,劝友人暂留,且不要匆匆归去。继而,词中又写作者纵酒高歌,劝友人钧,切切絮絮倾诉离情。这里,用春色、离愁、风雨,构成了一幅离别图:阳春佳月,风雨凄凄,离愁万绪,为下片抒情作了有力的铺垫。“三分春色二分愁,更一分风雨”,虽然还是以词家习惯运用的情景交融的手法来描写离愁,但设想奇特,不落俗套,给人以新颖巧妙的感觉。词人设想“春色”总体为“三分”,而其中的“二分”是“愁”,“一分”是“风雨”。这样,此时此刻的“春色”就成了“愁”与“风雨”的集合体。而此处的“风雨”,只是表象,实质上是明写风雨暗写愁。
这里写“风雨”,用的就是这种以景写情的笔法。所谓三分春色实际上都是愁。词人用全部的春色来写与挚友分手时的离愁别绪,其友情之深,离别之难,不言而喻。作者用笔,貌轻实重,饱和了作者的全部感情,确实是情景交融、情深意长。苏轼著名的《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有句云:“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大约即是从此处脱胎。
上片,由举杯挽留写到离别情怀,由外部行动而至内心感情,多为顺笔。下片则转折颇多。过片“花开”两句,紧承上片的离愁别绪,并进一步预写别后的相思。“花开”句,用韩偓《谪仙怨》“花开花谢相思”句意,但作者只写“花开花谢”而不说“相思”,实际上“相思”已包容上片的离愁别绪之中。“都来几许”,是说这种相思总的算来会有多少,由挚友不得长聚而引起的时序更迭、流年暗换的慨叹与迷惘,亦暗寓其中。这两句深化了上片的离愁。但作者马上又冲破了感伤缠绵的氛围,用“且高歌休诉”句一变而为高亢旷达。这是对友人的劝慰,也是作者的自我排遣,表现出作者开朗豁达的胸怀。可是一想到别易会难,明年此际不知能否重逢,心里不免又泛起怅惘之情,使全词再见波折。这首词先写离愁,继而排解宽慰,终写怅惘之情,曲折细致,语短情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