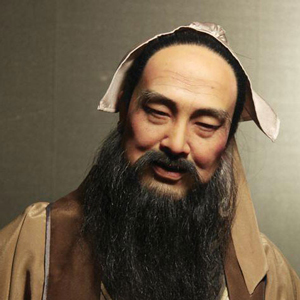诗从自己的行程写起,天还没有大亮就趁着月光从云阳出发,到太阳落山才到达朱方,按这两地相距甚近,根本用不着花一天时间,所以这里言外显然是要说自己在途中有相当长的时间呆在庐陵王墓下(刘宋皇室的陵墓都在朱方的郊区)。诗人对这位不幸遇害的少年王子表示最沉痛的哀悼。“道消”两句要表达的意思是,在徐羡之等人横行的岁月里,小人猖獗,君子道消,自己十分愤懑,但无从表达,郁积于胸中已久;现在拨乱反正,国运中兴,才得以一抒其哀悼的深情。“开运”二字有歌颂刘义隆之意。
“神期恒若存,德音初不忘”两句说逝者虽死犹生,当年的谈话自己是不会忘记的。自己与墓中人的关系一般来说乃是伤逝一类诗歌最重要的内容,往往会写得比较多;但这里却一笔带过,点到即止,很快就转入“徂谢易永久,松柏森已行”,感慨时光过起来真快那种比较常见的叹息当中去了,似乎不免有些奇怪。
这里有些不得已的原因。在刘宋王朝开国皇帝刘裕的七个儿子中,首先继承皇位的老大刘义符最缺乏政治家素质,他的爱好是乱玩一通,或模仿民间如何做小生意,于是很快就在一场政变中下台并被杀。他的二弟庐陵王刘义真则要出色得多,他很早就参加过刘裕恢复中原的战争,差点牺牲在关中;回到首都以后,注意笼络人才,与文化名人、宗教精英相接纳,对未来有所规划。《宋书》本传说他“美仪貌,神情秀彻”,“与陈郡谢灵运、琅邪颜延之、慧琳道人周旋异常,云得志之日,以灵运、延之为宰相,慧琳为西豫州都督”。刘裕去世前,他被任命为使持节、侍中、都督南豫雍司秦并六州诸军事、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出镇历阳(今安徽和县),“未之任而高祖崩”,稍后才去历阳赴任,出发前“义真与灵运、延之、慧琳等共视部伍”,一个影子政府公开亮相了。
谢灵运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召回首都任高官的。他对朝廷一举粉碎徐羡之集团、为庐陵王刘义真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当然是衷心拥护的,但是刘义真当年的狂言却绝对不宜去谈,于是他借用《诗经》中现成的“德音”一词,将自己与这位小王爷的深交含含糊糊地一提就告结束——再多说一句就成蛇足。
这时候只有哀叹刘义真的死于非命是不会犯任何忌讳的,宋文帝刘义隆在口头和书面上多次说起他那十八岁就被人害死的二哥义真乃一“冤魂”。所以谢诗也从这一角度切入,他主要用了两个典故,延州季子挂剑的故事见于《史记·吴太伯世家》,谢诗用这一典故既表明自己不忘故旧,也表明生者的纪念无法让逝者复生,这样做也没有任何用处。这是动了真感情的话,不是一般的门面语。“楚老惜兰芳”典出《汉书·龚胜传》,谢诗用这一典故的含义显然是痛惜刘义真毁灭于高尚,“抚坟徒自伤”则是觉得自己也可能有同样的命运。以脱俗的言辞来吊唁龚胜的楚老当是道家者流,他看清了一个人的高明之处往往给他带来麻烦以至于毁灭。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谢灵运在诗中大发这一类感慨,既以哀悼庐陵王刘义真,也表达了他本人深沉的忧虑。
“平生疑若人,通蔽互相妨。理感深情恸,定非识所将”四句比较曲折,不易索解。曾经有过不同的理解。《文选·庐陵王墓下作》李善注云:“若人,谓延州及楚老也。令德高远,是通也;解剑抚坟,是蔽也……言己往日疑彼二人,迨乎今辰,己亦复尔,斯则理感既深,情便悲痛,定非心识所能行也。”而吕向注则认为:“若,此也,此人谓王也。通,言聪明好古;蔽,谓与群邪不协,自见灭亡也。此两者互相其妨。”黄节先生《谢康乐诗注》大体取后一说并有所修正,指出:“通,谓生为帝子;蔽,犹塞也,谓废为庶人。此互相妨矣。”黄说甚是。追寻作品中词语典故的来源,李善本事很大;而对文学作品的理解,他的悟性似乎不是最佳,有时反不如学问要小得多的五臣。这四句诗略谓像庐陵王刘义真这样的人,他的高贵出身同他的悲惨遭遇实在是太矛盾了,简直不能理解,只好痛哭流涕。这里很有些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意思,但仍然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这四句略带玄言色彩,而正能表达其悲痛之深。最后几句说,刘义真死得太早,又死得特别冤枉,现在虽然得到昭雪,也不过是一个空名,我巨大的哀痛无法抑制,只好长歌当哭,根本算不上什么诗篇。
谢灵运的山水诗往往精细地描绘风景,感情色彩并不很浓,有一点也特别含蓄深沉,不大容易感觉到;他的政治抒情诗则不同,这一首更是很动了感情的。由于形势的微妙复杂,他不可能畅所欲言;但他其实把什么都说出来了,不愧是大诗人的手笔。
词的上片写词人到妻子墓地祭扫悼亡时的见闻和感伤情绪。
“松门石路秋风扫,似不许,飞尘到。”开头两句,写墓地的环境:苍松两排,挺立如门,青石铺路,平平展展,秋风吹扫,不染飞尘。洁静、尘幽,犹如冷寂的仙境。这既写出了墓地的特点,又点出了死者在词人心目中所占的位置。正是由于这位置的重要和非同一般,词人才把她的安息地描绘得如此幽静和庄严肃穆,显示了词人对死者的崇敬与哀伤。
“双携纤手别烟萝,红粉尘泉相照。”这两句写词人在墓地的情绪和心态。面对墓丘,睹物思人,极度悲苦,过份痛伤,使词人的情绪进入了似梦非梦,似幻非幻的状态。他好像又和妻子双手相牵,告别了那烟雾迷蒙,萝蔓丛生的墓地,在尘澈的泉水边去映照红润粉嫩的面庞。这里所写的情状,均是生前生活的写照。两人的感情是那样浓郁、真挚、深厚,依依难舍,如胶似漆。正因为生前有如此之深情,悼亡时才会出现如此之幻觉。看似浪漫,实则真实,读来十分感人。
“几声歌管,正须陶写,翻作伤心调。”写乐声惊醒幻梦之后的感情。前边两个分句是倒装的。“双携纤手”两句,写的本是幻觉。幻觉中出现男女团聚愉悦的景况,实在是“正须陶写”的。“陶写”即陶冶性情,排除忧闷。“写”者“泄”也。在幻觉中,词人的痛苦和忧闷正要得到排除和发泄,突然之间,远处传来了笙、箫、笛等“歌管”演奏的声音,这声音使词人如梦方醒,从幻境回到了现实。于是,重又堕入了痛苦和忧闷的深渊之中。上片全写在东山墓地悼亡时所见所感,心潮起伏变化,达情委婉曲折,蕴涵丰厚,耐人寻味。
下片写东山周围的景物,进一步抒发失去妻子之后无法忘怀的忧苦。
“岩阴暝色归云悄,恨易失,千金笑。”东山的山岩、峰峦慢慢地暝色四合,云雾聚集,夜幕悄悄地就要到来了。很自然地,随着时间的推移,悼亡者就要离开东山,突然之间,一阵痛苦再次袭上心头,他尘醒地懂得,这魂牵梦绕,挥之不去的悲痛,皆因失去“千金笑”所致。
外景外物,对悼亡者都有尖锐的刺激,揉搓着他敏感的神经,再不知“更逢何物可忘忧”了。此时抬头四望,映入眼帘的是茫茫无际、肥嫩丰茂、绿遍江南的芳草。芳草赏心悦目,芳草陶情娱人;芳草是春的使者,美的象征。面对多姿多情的芳草,词人只能“为谢”。“谢”为“辞谢”之谢。“为谢江南芳草”,是因为美好景物非但不能解除或减轻胸中的恨和忧,往往反而加重它的份量。这与杜甫《春望》中“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极为相似,不过手法更为曲折隐晦罢了。
“断桥孤驿,冷云黄叶,相见长安道。”最后三句,点破题目,落到了“别东山”上。“断桥”、“孤驿”、“冷云”、“黄叶”,都是东山墓地周围的景物,何其寂寞,何其孤冷,何其颓败,何其萧瑟。这固然是对景物的客观描绘,更多的则是词人的主观感受。即将离开坟场,最后这一眼,叫人目不忍睹了。“相见长安道”既是对往昔生活的回忆又是对亡灵进行安慰。
历代学者一般认为这是一首宴享诗。但诗的作者及创作年代前人没有深考。
《伐木》和《伐檀》不同,它不是描述伐木劳动,而是由伐木兴起,说到友情可贵。无论亲朋故旧还是新的相识,都要相互关心,相互帮助,并且常来常往。
诗共三章,除首章外,都集中笔墨写宴饮。显然是把宴饮当做建立和联系友情的重要手段。
在抒情方式之选择上,《伐木》的作者采用了一种先迂回后正面的表达方式。诗一开头,就以“丁丁”的伐木声和“嘤嘤”的鸟鸣声,令读者仿佛置身于一个远离尘世的仙境。在这里,时间仿佛停止,一切自在自为。只有这伐木之声和悦耳的鸟鸣在空旷的幽谷里回荡。一个孤独的伐木者,一个出谷迁乔去寻找知音的鸟儿,这两个意象在这仙境一般的氛围中被不断地进行视觉和听觉上的重叠和加强:声音使人联想到形象,形象又赋于声音特殊的内涵。从而最终幻化出一个远离现实政治的、借以寄托内心苦闷的超然之境。这一境界是诗人内心的人生理想在潜意识中迂回曲折的表露。同时也是厉王暴政下朝臣们心有余悸、不敢谈论政治而另寻寄托的普遍心态。现实毕竟是现实,随着这一比兴手法的完结,作为政治家的诗人终于强迫自己面对这冷酷的存在世界:“相彼鸟矣,犹求友声。矧伊人矣,不求友生。”号召人们起来改变现实,叙亲情,笃友谊,一切从头开始。然后又申之以“神之听之,终和且平”。从人情天理处说起,避开政治而为政治,这就是诗人既体察人心,又深谙做诗劝戒之道的地方。
第二章全然是写人的活动,也就是“求友生声”之具体表现。开头用语与首章部分重叠,显得整饬又有变化,读来流转而且自然。这里仍然由物兴起,但只用“伐木许许”一句,其余如对鸟鸣的描述一概略去。论者往往因为“伐木”句与后面的“酾酒”句联系紧密,就误认为它也是“赋”(直陈其事)。其实“伐木”云云,乃相应之词,不止形式上叠合延绵,内容也相仿佛,只是为避免刻板滞重,才作此省略。省略也是变化的方式,有变化才有发展,内容为之深化,形式也愈加富丽多姿。于是出现备办筵席的热闹场面:酒是甘美的,菜肴中有肥嫩羊羔,还有许多其他可口的食物,屋子也打扫得干干净净,可以看出主人的诚心诚意,因为宴请客人,不仅是出于礼仪,更是为了寻求友情。被邀请的客人都是长者,有同姓的(诸父),也有异姓的(诸舅)。诗人希望他们全都光临。“宁适不来?微我顾弗!”“宁适不来?微我有咎!”这是他的担心。由于希望甚殷,就生怕它落空。这种“患得患失”的情绪是真实的,也是感人的。它表明主人的态度十分诚恳,对友情的追求坚定不移。
诗人还批评了不顾情谊、互相猜忌的不良现象:“既有肥羜”,“於粲洒埽,陈馈八簋”,邀请“诸父”、“诸舅”而“不来”,又于我“弗顾”。这样的局面是不利于重振祖业的政治理想的。
第三章分两部分。前半部分是第二章的延续和发展,依然写设宴请客,不过用笔极简,旨在“示异”,以免拖沓。“笾豆有践,兄弟无远!”这次邀请是同辈,但酒菜之丰盛,礼节之周到不减于前。联系前面的有关描述,它明确地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无论长幼和亲疏(即诗中所谓“诸父”“诸舅”和“兄弟”)都应互相有爱。这种类似博爱的思想充斥整个诗篇,可以说是总的命意所在。但建议和发展友情的手段却比较单调,用现代的观点来看也未见合适,因为在酒席台上交的朋友多不可靠。也许饮食还是古人主要的交际方式,他们又多以诚待人,布设酒肉圈套,故而被诗人选作表达友情题旨的材料。另外还有反面教训,就是“民之失德,乾餱以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纷争往往由饮食细故引起,要创建和平局面,就得处理好饮食问题。
后半部分是尾声,似乎由众人合唱,表达了欢乐的情绪与和睦亲善的愿望。三方面的人(主人、来宾和受邀而未至者)团结一致,气氛和谐,令人鼓舞。
作者还为失去的友情和亲情而振臂高呼,他用饱经沧桑的笔调描绘着自己的希望和要求:普通人之间以诚相待绝不“乾餱以愆”。亲友之间相互理解(“有酒湑我,无酒酤我”)、信任,和睦快乐地相处。人和者政必通,最后,作者又是以一个超越于现实之上的境界结束全诗:在咚咚的鼓声伴奏下,人们载歌载舞、畅叙衷情,一派升平景象。这是作为政治家的诗人中兴周室之政治理想的艺术展示。
此诗是燕乐歌词,因而它的博爱的题旨可广泛传播,有一定的影响。在艺术上它给人的突出印象有三个方面:一是靠头的比兴部分不仅构成比较鲜明的画面,而且有生动的情节,它既是独立的,又与主题部分联系紧密,这样,主体部分的命意就更加明朗,便于读者和听众感受;二是把被邀的客人分别用“诸父”“诸舅”和“兄弟”指代,覆盖面大,而又意象分明,对表达诗歌的题旨起着重要的作用,可见作者选用词语的匠心;三是结尾表现的场面色彩浓丽,节奏明快,全然是就筵席写筵席,没有穿插“点题”笔墨,却成功地渲染出团结友善的醉人气氛。诗人把自己的人生追求化作可以闻见景象,因而颇具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