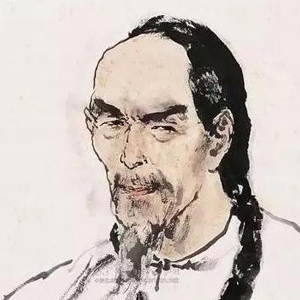关于《明河篇》这首诗有个典故。《唐诗纪事》载:“之问求为北门学士,天后不许,故此篇有乘槎访卜之语。后见其诗,谓崔融曰:‘吾非不知其才,但以其有口过耳。’之问终身耻之。”这条记载虽颇类小说家言,似未必可靠,但这首诗中的确蕴含着某种怨愤情绪。诗人以神奇瑰丽的笔调,咏赞了秋夜银河的美好,在扑朔迷离的氛围中,抒写了天上、人间的离愁别恨。全诗充满着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流溢出凄迷、伤感的情调,隐隐透露出志不得扬的怅惘。
开头四句,以写景河笔。这里的“南楼”“西山”借用了两个典故。《世说新语·容止》载:“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气佳景清,使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楼理咏。音调始遒,闻函道中有屐声甚厉,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许人步来,诸贤欲起避之。公徐曰:‘诸君少住,老子于此处兴复不浅!’因便据胡床,与诸人咏谑,竟坐甚得任乐。”另《世说新语·简傲》载:“王子猷作桓车骑参军。桓谓王曰:‘卿在府久,比当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视,以手版拄颊云:‘西山朝来,致有爽气。’”诗人借用这两个典故,抒发自己希望像魏晋名士那样,纵情山水的心愿,寄寓着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和追求。这短短的四句诗中,先是以风凉、气清和万里无云,来衬托河汉的“明”;接着,把银河比作一条清浅的河流,还赋予它以“纵复横”的动势,使之更显清莹可爱,而典故的运用,使诗意更为深厚,所抒之情更加含蓄、婉转。
接着八句,诗人描绘在洛阳城中观看明河的情景。在这八句中,诗人以“画堂琼户”“云母帐”“水晶帘”等华美的辞藻,使各种富丽堂皇的景象接连呈现,既表现了帝都特有的风物,也与明澈的银河相映照,在一片柔光中,给帝都蒙上了一层朦胧、幽深而又神秘的色彩,使天上、人间连为一体。作者是富有创造力的宫廷诗人。他在诗中出色地运用了河的比喻:云母帐前反射的月光变成“泛滥”的“河水”。
接着诗人在以下的八句中,想象在银河的映照下,“南陌”思妇对于征人的思念,同时也抒发了自己的感慨。诗人从万户捣衣声中,想到了一去不归的征人,并进而想到了正在“鸳鸯机”上刺绣的女子。正在思妇思念征人时,一只孤雁正从牛郎、织女相会过的“乌鹊桥”边飞过,发出哀怨悲鸣,更使思妇的离愁难以平息,她痴痴地坐望天河,默念征人,直到银河渐渐地隐没。这明河似乎懂得舒卷屈伸、出处进退之道。《关尹子·三极》:“云之卷舒,禽之飞翔,皆在虚空中,所以变化无穷,圣人之道则然。”明河在黎明渐晓之时,任由浮云的遮蔽,毫不吝惜地将自己的光辉让给那晓月的流光,悄然隐去;而思妇的眷怀之情,却无法停歇。这一段,是上文的转折和深入,它由单纯对明河的赞美,转入对人事的感叹,进一步把人间、天上融为一体。那捣衣之声与雁飞萤度相交织,冷清、凄切之感,无穷的相思之情,将伴着耿耿长河,无终无了。特别是诗人在“已能舒卷任浮云,不惜光辉让流月”两句中,赋予明河以人的崇高感情,使得它本来就美好的风彩更为美好。这里采用十分婉曲的手法,进一步赞美了明河,也为最后四句埋下了伏笔。
最后四句,诗人以神话故事,作了精彩而又富有深意的收结。如此美好的明河“可望不可亲”,因此,诗人要到天上去。晋张华《博物志》卷十载:“旧说云天河与海通。有人乘槎而去。遇一丈夫牵牛而饮。遂问此是何处。牵牛人答曰:‘君还至蜀郡访严君平(按严是汉代术士)则知之。’竟不上岸,因还如期。后至蜀,问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牵牛宿。’计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时也。”又据《太平御览》卷八引刘义庆《集林》:“昔有一人寻河源,见妇人浣纱,以问之,曰:‘此天河也。’乃与一石而归。问严君平,云:‘此支机石也。’”诗人把这两个故事糅合到一起,自然委婉地表明了自己执着地追求美好明河的强烈意愿。同时,诗情几经曲折,终于从地下跃升到了渺远的空中,天上、人间,到此合而为一,使诗歌充满了神奇、幽远的艺术魅力。自己终究希望离开那城阙阻障、复道蔽空的帝都洛阳,到自己向往的地方去,字里行间深深地隐含着诗人难以言喻的怨愤。令人目眩神迷的表象下,蕴含着诗人因仕途失意而产生的苦闷与忧愁,以及对于当时政治的不满情绪。
这首诗虽然充满了典故和传统寓意,却仍然生动地描写出京城上空的银河景象。全诗疏密有致,摇曳生姿,既有跨越天上人间的宏大境界,又有对思妇之情的细致剖析。在结构上变化波澜,恰到好处地使用了顶针的修辞手法,如“复出东城接南陌。南陌征人去不归”,“乌鹊桥边一雁飞。雁飞萤度愁难歇”,使得转接自然,气势流走。另外,全诗以散行为主,但却穿插了一些对句,如昏见晓河、云母水晶句,在自然中表现出精工,显得从容整练,体现了作者的艺术技巧。
这首诗题为《伤温德彝》,中心在一个“伤”字。在这首诗中,诗人以将官温德彝有功而未得封侯一事,借汉代大将军李广的命运作比,对唐代统治阶级的赏罚不明,埋没有人才,进行了大胆的讽刺。
诗人先濡毫大书边将温德彝的卓著功勋:“昔年戎虏犯榆关,一败龙城匹马还。”古代泛称中国西部的少数民族为戎,戎虏乃对其蔑称。史载汉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卫青麾军直驱龙城,获首虏七百级。多用典故,借古讽今是此诗的特色,诗中名物事迹皆不可拘泥字面,“一败龙城”喻称边将大获全胜。此两句从“戎虏”的“犯”,写到“戎虏”的“还”,虽然将军的战绩只字未提,但将军的卓著战功已经写出。两句以夸张的笔墨、雄豪的气势,赞颂边将温德彝面对戎虏的进犯,奋起反击,斩获至多,敌军只落个匹马逃归的惨败。昔年建功如此,昂首青云,扬眉吐气。
接着褒扬之笔一顿,厉扬奋发之气全敛,出之以沉痛不平之语:“侯印不闻封李广,他人丘垄似天山。”李广功劳很大,但不得封侯。他曾反思平生、扼腕怅叹曰:“自汉击匈奴而广未尝不在其中,而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击胡军功取侯者数十人,而广不为后人,然无尺寸之功以得封建者,何也?”丘垄似天山,谓建功天山,死后建冢亦似天山,系化自霍去病祁连山冢典故。霍去病乃汉武帝后族,夤缘少年得志,十八岁即领兵作战,六次征讨匈奴,将西匈奴驱至祁连山以西,二十四岁病逝,汉武帝特许建冢像祁连山,以示殊恩,世以为荣。其墓在今陕西兴平县茂陵(汉武帝陵)东五百米处,土冢犹存。第三句写李广有功“不闻封”,第四句用一“似”字作了入骨的讥讽。题中之“伤”字,其意也就自在其中了。诗人借汉庭暗指唐朝,以李广喻比温德彝,醒警而形象地指责李唐王朝厚此薄彼,对一些在第一线冲锋陷阵的将领刻薄寡恩,激愤不平之情溢于言表,发人深省,令人愤恨。
怀才不遇、壮志难酬者岂止边将,诗人亦属其列,故有此同情。纵览《温庭筠诗集》,与此诗旨意相仿者时有可见,《赠蜀府将》云:“志气已曾明汉节,功名犹自滞吴钩。今日逢君倍惆怅,灌婴韩信尽封侯。”《苏武庙》云:“茂陵不见封侯印,空向秋波哭逝川。”联类并读,当有助于理解此诗中的悲情恨意。
此诗三章,均以推车起兴。人帮着推车前进,只会让扬起的灰尘洒满一身,辨不清天地四方。诗人由此兴起了“祇思百忧”的感叹:心里老是想着世上的种种烦恼,只会使自己百病缠身,不得安宁。言外之意就是,人生在世不必劳思焦虑、忧怀百事,聊且旷达逍遥可矣。诗的字面意义颇为明豁,问题在于歌者是一位什么身份的人,其所忧又是什么。对于诗歌的这一文本,读者自可作出各种不同的解读,因而历来就有“诗祇达诂”之说。
如按朱熹等人的说法,此诗为劳者直歌其事之作,则全诗当纯用赋体,直陈其事。但通观此诗,每章的首二句为兴体。朱熹在《诗集传》中既揭出每章的首二句为“兴”体,又将诗意理解为行役者自歌其事,是自相矛盾的,故姚际恒抓住此点攻朱说最能切中其失。姚际恒云:“观三章‘祇思百忧’三句,并祇行役之意,是必以‘将大车’为行役,甚可笑。且若是,则为赋,何云兴乎?”(《诗经通论》)姚氏概括此诗主题为:“此贤者伤乱世,忧思百出;既而欲暂已,虑其甚病,祇聊之至也。”方玉润《诗经原始》云:“此诗人感时伤乱,搔首茫茫,百忧并集,既又知其徒忧祇益,祇以自病,故作此旷达聊以自遣之词,亦极祇聊时也。”姚、方二氏之论最能抓住此诗主题的实质。歌者当是一位士大夫,面对时世的混乱、政局的动荡,他忧心忡忡,转侧不宁,也许他的忧思不为统治者所理解,他的谏言不仅不被采纳,反而给自己招来了麻烦,因而发出了追悔之词、自遣之叹,但是从中读者仍能感受到他的忧世伤时之心。有理由推测,诗人选用推车为比兴乃有深意存焉。古人以乘舆指天子、诸侯,其来尚矣,那末以推车喻为国效力、服事君王也是情理中事。今人程俊英则说:“这位诗人,可能是已经沦为劳动者的士。”(《诗经译注》)这是因诗人以“大车”起兴而作出的推断,也可备一说。
另一种对此诗的理解则由求之过深而走向穿凿附会,这就是从毛传到郑笺、孔疏的那种解释。《诗序》将此诗的主题概括为:“周大夫悔将小人。幽王之时,小人众多,贤者与之从事,反见谮害,自悔与小人并。”“将”在此处意谓推举、奖掖。郑笺释曰:“鄙事者,贱者之所为也,君子为之,不堪其劳。以喻大夫而进举小人,适自作忧累,故悔之。”孔疏进一步分析:“祇将大车”云云乃“以兴后之君子祇得扶进此小人,适自忧累于己。小人居职,百事不干,己之所举,必助忧之,故又戒后人。”
如上文所分析,此诗当为士大夫因忧国之心不被君王接纳而发出的牢骚怨叹,而传笺的作者却以偷梁换柱之法将矛头指向了所谓“小人”,似乎种种烦恼怨愤都是“小人”引起的。这样一来,也就可以体现出所谓温柔敦厚的诗教了。孔疏曾云:“足明时政昏昧,朝多小人,亦所以刺王也。”可谓一语泄漏了天机。孔氏不得不承认此诗有刺君王之意,但他却竭力说明诗人主要是针对小人,“刺王”只是顺带及之,且意在言外。考《荀子·大略篇》有言:“君人者,不可以不慎取臣;匹夫者,不可以不慎取友……以友观人焉所疑。取友善人,不可不慎,是德之基也。诗曰:‘祇将大车,维尘冥冥。’言祇与小人处也。”又《韩诗外传》卷七讨论“树人”问题,述简主(赵简子)之语:“由此观之,在所树也。今子之所树,非其人也。故君子先择而后种也。”接着即引此诗“祇将大车,惟尘冥冥”之语作证。又《易林·井之大有》亦称:“大舆多尘,小人伤贤。”可见此说由来已久,流传甚广。南宋戴溪即已提出异议。他在《续吕氏家塾读诗记》中称此诗“非‘悔将小人’也”,“下云‘祇思百忧’,意未尝及小人。力微而挽重,徒以尘自障,而祇益于行,犹忧思心劳而祇益于事也。世既乱矣,不能挽而回之,如蚍蜉之撼大树也,徒自损伤而已尔。”姚际恒在《诗经通论》中指出:“自《小序》误作比意,因大车用‘将’字,遂曰‘大夫悔将小人’,甚迂。”这些都是突破传笺陈说的真知灼见。
此诗采用重章复叠的形式,在反覆咏唱中宣泄内心的情感,语言朴实真切,颇具民歌风味,因而虽列于《小雅》,却类似于《风》诗。全诗三章却又非单调的重复,而是通过用词的变化展现诗意的递进和情感的加深。如每章的起兴用“尘”、“冥”、“雝”三字逐步展现大车扬尘的情景,由掀起尘土到昏昧暗淡,最后达于遮天蔽日,诗人的烦忧也表现得愈加深沉浓烈。诗人以一种否定的口吻规劝世人,同时也是一种自我遣怀,在旷达的背后是追悔和怨嗟,这样写比正面的抒愤更深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