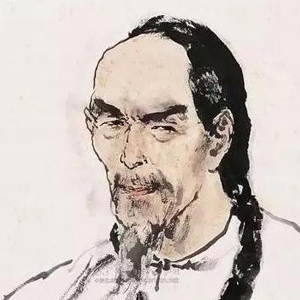拔地数千丈,凌空十八盘。
飞泉鸣乱石,危磴护重关。
俯视人寰隘,真疑长羽翰。
拔地数千丈,凌空十八盘。
飞泉鸣乱石,危磴护重关。
俯视人寰隘,真疑长羽翰。
词中的女主人公思念着离她而去的远行人,与一般闺怨诗词不同的是,这位远行人不是去求仕、戍边、经商,而是去“游冶”,这就使女主人公处在更为悲惨的境地:相思之苦加上被弃之痛。
词从“绣帏睡起”开端,写了一整天的情况,实际是女主人公在爱人远行后长长一段时间的缩影。看似平淡无奇,却为下文尽情展衍留足余地。“藻井凝尘”言室内凌乱,无心洒扫,“金梯铺鲜”言室外冷落,无人来往,这是写她生活的环境。“寂寞凤楼十二”一句中的“寂寞”二字,可说是对刚才的总结,也是上片的核心。“风絮”二句以反衬的手法写美丽的春景,与“藻井凝尘,金梯铺鲜”形成鲜明的对比。“永日画阑,沉吟独倚"是她一天寂寞生活的概括,突出女主人公无心欣赏美景的心态。“望远行”二句写女主人公登高望远,希望游子会回到自己的身边。春已归却不见远人归影,着一“悄”字,说明女主人公不知几度登高又几度失望,这是寂寞中的希冀与希冀后的失落,失落自然更加重了她的寂寞。
过片换头“凝睇”二字有承上启下的作用,这不是她凝神远望归骑的目光,而是盼望落空后那失神而凝滞的目光,这目光又开启下片抒发内心情愫的一连申行动。她想排遣离愁,但却苦于“无计”;只有拔下头上的金钗换酒,求助于酒醉后的解脱,无奈无聊的自斟自饮反更添愁情以至珠泪涟涟。愁中的醉,醉后的泪,欲昏反醒,欲笑反泪。“待伊游冶归来”五句为女主人公的心理想法,最后她还是寄望于远行人的重归,待那时,要故意换下宽大的衣饰,束紧薄薄的丝裙,让那薄情人看看瘦减的“纤腰”,让他相信我因思念他而变得如此憔悴。此五句虽化用了武则天《如意娘》:“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诗意,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将思妇恨游子不归,盼游子快归,幻想游子归来之后悲喜交加的心态写的淋漓尽致。
这下片自“凝睇”开端以后,先以“无计”,继之“但……”、“空……”、“争奈……”、“待……”,一连串行动,从纪实写到设想,从行动写到内心,写出了这个女子怨而不怒、徒劳挣扎的整个过程。但这个远行人会不会归来呢?设若他真的归来了,会不会因为女主人公的憔悴而动了怜爱之心从此不再去“游冶”呢?词结束了,女主人公的悲剧却并没有结束。
柳永作为一个男性词人,极真实地写出了被弃的善良弱女子可悲的无助的境遇,这是基于柳永对女性深切的了解和同情。
这是一首山水隐逸诗,在盛唐已传为名篇。到清代,更受“神韵派”的推崇,同《题破山寺后禅院》并为常建代表作品。
此诗题曰“际王昌龄隐居”,一是指王昌龄出仕前隐居之处,二是说当时王昌龄不在此地。王昌龄及第时大约已有三十七岁。此前,他曾隐居石门山。山在今安徽含山县境内,即此诗所说“清溪”所在。常建任职的盱眙,即今江苏盱眙,与石门山分处淮河南北。常建辞官西返武昌樊山,大概渡淮绕道不远,就近到石门山一游,并在王昌龄隐居处住了一夜。
首联写王昌龄隐居所在。“深不测”一作“深不极”,并非指水的深度,而是说清溪水流入石门山深处,见不到头。王昌龄隐居处便在清溪水流入的石门山上,望去只看见一片白云。齐梁隐士、“山中宰相”陶弘景对齐高帝说:“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因而山中白云便沿为隐者居处的标志,清高风度的象征。但陶弘景是著名阔隐士,白云多;王昌龄却贫穷,云也孤,而更见出清高。清人徐增说:“惟见孤云,是昌龄不在,并觉其孤也。”这样理解,也具情趣。
中间两联写诗人夜际王昌龄隐居处所见所感。颔联“松际露微月,清光犹为君”,诗人际在此处,举头望去,松树梢头,一弯明月慢慢升起,光照入室。“君”指王昌龄。说王昌龄虽不在这里了,明月多情,却仍来陪伴着他的客人。王昌龄隐居处清贫幽雅,只有一座孤零零的茅亭。“茅亭际花影,药院滋苔纹”,是说夜际茅亭,看见窗外团团花影,错落斑驳;而到院子里,则看见莳养的各种药草,依然生长得很好,只是由于长久没有人来往,路边已长满了青苔。这似乎只是写隐逸生活的情趣,其实字里行间流露了诗人对王昌龄没有坚持退隐的惋惜心情。
尾联就写诗人自己的归志以及对朋友的讽劝: “余亦谢时去,西山鸾鹤群。” “鸾鹤群”用江淹《登庐山香炉峰》“此山具鸾群,往来尽仙灵”语,与鸾鹤合群,与仙灵为伴,即表示要终身归隐。这里表达了诗人自己的心志,也有对朋友的期待。“亦”字很妙,此时王昌龄已登仕途,常建却借赞扬王昌龄归隐之处,说我也要跟随你一起归隐。这是故意这样说,是对王昌龄一种善意的讽劝。这是本诗的主题所在,是与题目《际王昌龄隐居》的意思相合的。也即是说,常建是在招王昌龄归隐,与本文开头所介绍的《鄂渚招王昌龄张偾》一诗同其旨趣。
这首诗的艺术特点确同《题破山寺后禅院》,“其旨远,其兴僻,佳句辄来,唯论意表”。诗人善于在平易地写景中蕴含着深长的比兴寄喻,形象明朗,诗旨含蓄,而意向显豁,发人联想。就此诗而论,诗人巧妙地抓住王昌龄从前隐居的旧地,深情地赞叹隐者王昌龄的清高品格和隐逸生活的高尚情趣,诚挚地表示讽劝和期望仕者王昌龄归来的意向。因而在构思和表现上,“唯论意表”的特点更为突出,终篇都赞此劝彼,意在言外,而一片深情又都借景物表达,使王昌龄隐居处的无情景物都充满对王昌龄的深情,愿王昌龄归来。但手法又只是平实描叙,不拟人化。所以,其动人在写情,其悦人在传神,艺术风格确实近王维、孟浩然一派。
上阕“山寺微茫背夕曛”,如认为确有此山、确有此寺,而欲指某山、某寺以实之,则误矣。此词前片三句,但标举一崇高幽美而渺茫之境界耳。近代西洋文艺有所谓象征主义者,静安先生之作殆近之焉。我国旧诗旧词中,拟喻之作虽多,而象征之作则极少。所谓拟喻者,大别之约有三类:其一曰以物拟人,如吴文英《浣溪沙》词“落絮无声春堕泪,行云有影月含羞”,杜牧《赠别》诗“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是以物拟人者也:其二曰以物拟物,如东坡《永遇乐》词“明月如霜,好风如水”,端己《菩萨蛮》词“琵琶金翠羽,弦上黄莺语”,是以物拟物者也;其三曰以人托物,屈子《离骚》“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骆宾王《在狱咏蝉》诗“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是以人托物者也。要之,此三种皆于虚拟之中仍不免写实之意也。至若其以假造之景象,表抽象之观念,以显示人生、宗教,或道德、哲学,某种深邃之义理者,则近于西洋之象征主义矣。此于古人之作中,颇难觅得例证。《珠玉词》之《浣溪沙》“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六一词》之《玉楼春》“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东风容易别”,殆近之矣。以其颇有人生哲理存乎其间也。然而此在晏、欧诸公,殆不过偶尔自然之流露,而非有心用意之作也。正如静安先生《人间词话》所云:“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许也。”而静安先生之词,则思深意苦,故其所作多为有心用意之作。樊志厚《人间词甲稿序》云:“若夫观物之微、托兴之深,则又君诗词之特色。”此序人言是静安先生自作而托名樊志厚者,即使不然,而其序言亦必深为静安先生所印可者也。“山寺微茫”一起四字,便引人抬眼望向半天高处,显示一极崇高渺茫之境,复益之以“背夕曛”,乃更增加无限要渺幽微之感。黄仲则《都门秋思》有句云“夕阳劝客登楼去”,于四野苍茫之中,而举目遥见高峰层楼之上独留此一片夕阳,发出无限之诱惑,令人兴攀跻之念,故曰“劝客登楼去”,此一“劝”字固极妙也。静安词之“夕曛”,较仲则所云“夕阳”者其时间当更为晏晚,而其光色亦当更为黯淡,然其为诱惑,则或更有过之。常人贵远而贱近,每于其所愈不能知、愈不可得者,则其渴慕之心亦愈切。故静安先生不曰“对”夕曛,而曰“背夕曛”,乃益更增人之遐思幽想也。人于此尘杂烦乱之生活中,恍惚焉一瞥哲理之灵光,而此灵光又复渺远幽微如不可即,则其对人之诱惑为何如,静安先生盖尝深受西洋叔本华悲观哲学之影响,以为“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一欲既终,欲随之,故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也。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也。”锄静安先生既觉人生之苦痛如斯,是其研究哲学,盖欲于其中觅一解脱之道者也。然而静安先生在《静庵文集续编·自序二》中又云:“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然则是此哲理之灵光虽惚若可以瞥见,而终不可以求得者也。故曰:“鸟飞不到半山昏。”人力薄弱,竟可奈何,然而人对彼一境界之向往,彼一境界对人之吸引,仍在在足以动摇人心。有磬声焉,其音孤寂,而揭响遏云,入乎耳,动乎心,虽欲不向往,而其吸引之力有不可拒者焉,故曰“上方孤磐定行云”也。
于是而思试一攀跻之焉,因而下阕乃有“试上高峰窥皓月”之言。曰“试上”,则未曾真筒到达也可知;曰“窥”,则未曾真筒察见也可想。然则此一“试上”之间,有多少努力,多少苦痛。此又静安先生在《红楼梦评论》一文所云:“有能除去此二者(按指苦痛与倦厌),吾人谓之日快乐。然当其求快乐也,吾人于固有之苦痛外,又不得不加以努力,而努力亦苦痛之一也。且快乐之后,其感苦痛也弥深。故苦痛而无回复之快乐者有之矣,未有快乐而不先之或继之以苦痛者也。”(按:此实叔本华之说)是其“试上高峰”原思求解脱、求快乐,而其“试上”之努力固已为一种痛苦矣。且其痛苦尚不止此。盖吾辈凡人,固无时刻不为此尘网所牢笼,深溺于生活之大欲中,而不克自拔,亦正如静安先生在《红楼梦评论》中所云:“于解脱之途中,彼之生活之欲,犹时时起而与之相抗。”夫如是,固终不免于“偶开天眼觑红尘”也。已知其“偶开”必由此不能自己、不克自主之一念耳。陈鸿《长恨歌传》云:“由此一念,又不得居此,复堕下界,且结后缘。”而人生竞不能制此一念之动,则前所云“试上高峰”者,乃弥增人之艰辛痛苦之感矣。窃以为前一句之“窥”,有欲求见而未全得见之憾;后一句之“觑”,有欲求无见而不能不见之悲。而结之日“可怜身是眼中人”,彼“眼中人”者何,固此尘世大欲中扰扰攘攘、忧患劳苦之众生也。夫彼众生虽忧患劳苦,而彼辈春梦方酣,固不暇自哀。此譬若人死后之尸骸,其腐朽靡烂乃全不自知,而今乃有一尸骸焉,独具清醒未死之官能,自视其腐朽,自感其靡烂,则其悲哀痛苦,所以自哀而哀人者,其深切当如何耶,于是此“可怜身是眼中人”一句,乃真有令人不忍卒读者矣。
上片开头便由骑马出游写起。先写骑马出游的风貌。“一帽红尘”,点明出游时风尘仆仆, 同时,还说明了出游所经之路是尘埃飞扬的闹市。再写骑马出游的行踪,以“韦杜人家北”代指清都京师中的显贵豪门的住宅区。随后, 写所见到的显贵豪门住宅区的楼台,并以“满城风色”作比,认为有“隔”。作者在此未发一个议论, 但却表示了对显贵豪门厌弃的态度。
下片转写飞鸿南去。飞鸿飞去的地方正是作者家乡所在的江南,于是,禁不住对家乡的思念而“目送飞鸿”,一直望到飞鸿的影子在远天消失。作者的思乡之心便飞过了隔绝的关山,从千迭的乱云中穿过,想象到家乡可能也正是千里飞雪。下片写南去的飞鸿,进而抒发了思乡之情,表面上看来与上片表达的思想关系不大,实际上,越写思乡之切,就越使得对显贵豪门厌弃的态度更加鲜明。
词的上、下两片,虽各有侧重,但又是完整的一体。两片相接,照视线的移动,由望高楼到望空中,再到望飞鸿,合理而自然。全词无议论,以形象的语言写所见、所想,再透过所见、所想显露出要表达的思想。写所想,能驰骋想象,飞过关山,穿过乱云,展现了千里飞雪的壮阔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