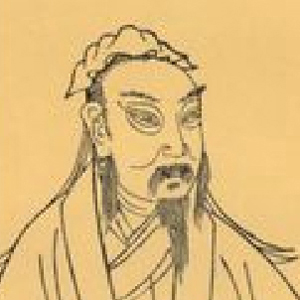上阕以“传情入景”之笔,抒发男女间的相思之苦。作者借“移情”笔法,赋予视野中的客观景象以强烈的主观情感,使天边新月、枝上红豆都染上别离相思的情愫。“新月曲如眉,未有团圞意”,明为写月,实则喻人,作者以眉比月,正暗示出相思人儿因不见团聚而双眉紧蹙,郁闷不欢的愁苦之态。“红豆”本是相思的信物,但在离人的眼里却是贮满了忧伤,令人见之落泪。一弯新月,数枝红豆,词人撷取传统的寄寓人间悲欢离合、别离思念之情的两种意象,正表达出对爱人的无限深情和思之不得的痛切缺憾。
就内容而言,下阕为上阕之顺延;就感情的“走向”而言,二者又有着微妙的差异。如果说上阕中写相思还只是借助于意象的寄托,情感的附着还比较虚幻,词中的情绪基调也是一种充满残缺感的低沉.那么下阕中的情感就相对地落到了实处,词中流露着的、是充满希冀的向上的基凋。“终日劈桃穰,仁儿在心里”,一语双关,看似百无聊赖的行为,正寄托着主人公对心上人丝丝缕缕的情爱和日复一日的期盼。“两朵隔墙花,早晚成连理”更表明对爱情的充满信心,尽管花阡两朵,一“墙”相隔,但相爱的人儿终将冲破阻碍,喜结连理。整首词写得情致深长,淋漓沉至。
这首词在艺术上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极其自然地运用了南北朝民歌中的吴歌“子夜体”,以下句释上句,托物抒情,论词家评曰:“妍词妙喻,深得六朝短歌遗意。五代词中希见之品。”
此诗是刘禹锡以牡丹为题的唱和诗作。诗人以牡丹入题,借物抒怀,写别牡丹而实叹别京国,一句“春明门外即天涯”道尽沉浮感慨。
诗作前句与令狐楚唱和,从其诗意点明了临到开放主人却不在的创作背景,平铺直叙不起一字波澜。值得体会的,是诗人借别牡丹写别家别京城的写作手法,以牡丹的鲜明形象寄托了家和京国的含义在其中,字在牡丹而意属别离,使得诗意委婉清新。
而紧随话锋突转:“莫道两京非远别,春明门外即天涯”。“莫道”两字戳破“两京非远别”之谬,用否定的句式表达出作者强烈的情感。“春明门”则以小处着眼,以出春明门这离京赴东都的必经之门代指离京去国。“即”字是言离京一步便是天涯,情感强烈,笔法夸张。从“一栏花”之小,到“天涯”之大;以“春明门”之近,到“天涯”之远。作者用鲜明的对比、强烈的句式、借代夸张的修辞手法十分精炼的表达了离京的深深感慨。前句委婉清新,后句却尽意抒怀,前后情感强度反差也使诗中情感愈加鲜明,更是将离京之凄楚眷怀诉说的淋漓尽致。全诗借牡丹为题,言在牡丹,韵系离愁,道尽去京国赴天涯的沉浮感慨,是一篇借物抒怀之佳作。
刘禹锡唱和之作较令狐楚诗情感更强烈,能言令狐楚所未能言,此宜结合作者生平体会。刘禹锡因“永贞革新”失败连贬远州司马,又受尽谗言所害,一生多数时间都是远离京国的逐放生涯。故而尽管是写令狐楚离京,刘禹锡唱和为友不平,又何尝不是杂糅了刘禹锡对自己坎坷仕途的感慨,此诗非是为一人而不平。
这首诗首二句纪行,叙述他自镇江逃脱,回到长江口的艰险经历。末二句抒情,以“磁针石”比喻忠于宋朝的一片丹心。这首诗语言浅近,运用比兴手法,触景生情,字里行间表现出坚定不移的爱国主义精神。
诗的首二句纪行,叙述他自镇江逃脱,绕道北行,在海上漂流数日后,又回到长江口的艰险经历。首句的“北海游”。指绕道长江口以北的海域。次句“回从扬子大江头”,指从长江口南归,引起三、四两句。
末二句抒情,以“磁针石”比喻忠于宋朝的一片丹心,表明自己一定要战胜重重困难,回到南方,再兴义师,重整山河的决心。“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表现了他不辞千难万险,赶到南方去保卫南宋政权的决心。忠肝义胆,昭若日月。
诗人运用比兴手法,触景生情,抒写了自己心向南宋,不到南方誓不罢休的坚强信念,真实地反映了作者对祖国的坚贞和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