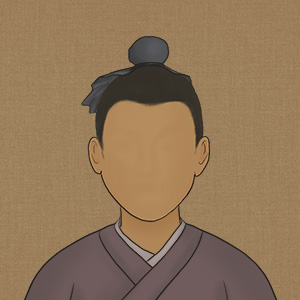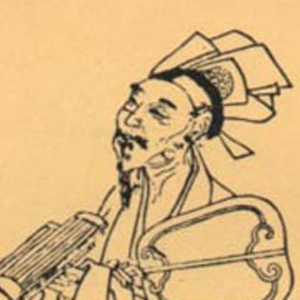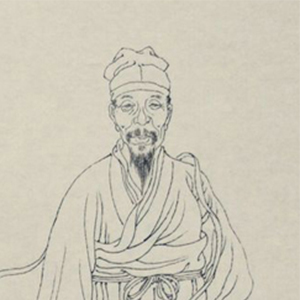这是一首送别诗,但不是一般的亲朋好友间的送往迎来,而是送僧人归山。这首诗前两句以凌云的野鹤形容僧人,贴切有味,理应不失孤云野鹤般脱俗的品性;末两句写诗人对方外上人的讽喻规劝,劝上人隐居冷寂的深山,而不要到热闹的名胜去沽名钓誉。这首诗语言妙趣横生,闲散淡远,构思精巧。
“孤云将野鹤,岂向人间住。”以凌云的野鹤形容僧人,贴切有味。“云”与“鹤”本来已不是俗世凡物,何况还是“孤云”与“野鹤”,这样超尘脱俗之物在人世是留不住的。因此诗人诙谐地说:“岂向人间住。”尘世难留方外高人。方外高人理应去深山古刹,静心修炼;因此,上人归山,恰得其所,理应祝贺,不该作儿女之态,像俗人那样依依不舍,甚至怅惘无极。
“莫买沃洲山,时人已知处。”是对上人的讽喻规劝,劝上人隐居冷寂的深山,而不要到热闹的名胜去沽名钓誉。不少僧人爱住名山宝刹,实际上并不是为了修行,而是为了扬名,然后接近权贵,以求闻达于皇帝,达到加官进爵的目的。这与假隐士走终南捷径的手段相似。“莫买沃洲山”,暗寓出沃洲山名声太大,人们都知道那地方,会影响修行,会成为走“终南捷径”的人。这后两句与裴迪《送崔九》的后两句:“莫学武陵人,暂游桃源里”是同一用意,但此诗说得更直率。由此可见,作者与上人的关系亲密,可以直接规劝,所以吴瑞荣在《唐诗笺要》中说:“索性勉其入山之深,是何等交谊?”
观此诗作,写得妙趣横生、闲情逸趣,流露出诗人很看重灵澈孤云野鹤般脱俗的境界,向往隐居深山之中,却规劝方外上人要另觅他处,“莫买沃洲山”,表现出诗人劝上人隐居冷寂的深山,领悟真隐和假隐之真谛,莫隐居变成趋时,失孤云野鹤般脱俗的品性。
此诗前两句用“山外山”、“树边树”的视觉形象引发国破家亡的愁怨和遗恨;后两句诗人紧承前语,针对元代统治者发出的反抗心声,揭示出诗人自己与元朝统治者“不共戴天”的主题。全诗以浅近通俗的语言,生动质朴的比喻,率直地表示亡国之恨,字字咬牙,句句切齿,有颠倒乾坤,截断众流之气魄。
第一、二句作者为了表现胸中的“愁和“恨”,不是采取怒发冲冠式的直接表露,而是借物寓怀,以一种环境衬托的比喻手法,巧妙地用“山外山”“树边树”的视觉形象引发国破家亡的愁怨和遗恨。这里的“山”“树”,不仅指自然的“山”“树”,更寓意元兵占领的一片浑浊世界。山、树本可使人赏心悦目,然而在亡国遗民眼中,只能勾起无限的愁和恨。
第三、四句紧承一、二句,诗人设想,如果眼前的山和树能够隔断秋月的光明,照我就不照他,照他就不照我,使我和他“不共一处”。这样以含蓄的手法,揭示出诗人自己与元朝统治者“不共戴天”的主题。诗人虽未明言同谁“不共一处”,不过,从诗人所写“无处堪挥泪”(《书文山卷后》),“我愁无地可耕渔”(见《宋遗民录》)等句,则可以清楚地看出,正是灭宋的元代统治者,使诗人陷入“无处”“无地”的厄运,所以诗人在月色如银的秋夜,迸发出的愁恨,不能仅仅看作是个人的恩怨。确切地说,全诗乃是针对元代统治者发出的反抗心声,誓欲隔断明亮的秋月,虽然想隔断秋月的光明,事实上却是不可能的,但诗人不愿与元代新贵们“共一处”,其态度之坚决,气节之坚贞,给读者以强烈的感受。
前人评谢翱诗曰:“所作歌诗,其称小,其指大,其辞隐,其意显,有风人之余,类唐人之卓卓者。”(《谢翱传》)此诗即可见诗人风格之一斑。
这是欧阳修晚年退居颍州时写的十首《采桑子》中的第四首,抒写了作者寄情湖山的情怀。虽写残春景色,却无伤春之感,而是以疏淡轻快的笔墨描绘了颍州西湖的暮春景,创造出一种清幽静谧的艺术境界。而词人的安闲自适,也就在这种境界中自然地表现出来。情景交融,真切动人。词中很少修饰,特别是上下两片,纯用白描,却颇耐寻味。
这首词是欧阳修晚年居住的颍州西湖的暮春景象,从而表现了作者异常的、幽微的心理状态。
“群芳过后西湖好,狼藉残红,飞絮濛濛,垂柳阑干尽日风。”这首词上阕是说,虽说是百花凋落,暮春时节的西湖依然是美丽的,残花轻盈飘落,点点残红在纷杂的枝叶间分外醒目;柳絮飘舞,柳枝在和风中随风飘荡,在和煦的春风中,怡然自得,整日轻拂着湖水。
西湖花时过后,残红狼籍,常人对此,当是无限惋惜,而作者却赞赏说“好”,确是异乎寻常的。首句是全词的纲领,由此引出“群芳过后的”湖上一片实景,笼罩在这篇实景上的是寂寞空虚的气氛。落红零乱满地,杨花漫空飞舞,使人感觉春事已了。“垂柳阑干尽日风”与上二句相联系,写出了栏畔翠柳柔条斜拂于春风中的姿态;单是这风中垂柳的姿态,本来是够生动优美的,然而著以“尽日”二字,联系白居易《杨柳枝》“永丰西角荒园里,尽日无人属阿谁”来体会,整幅画面上一切悄然,只有柳条竟日在风中飘动,其境地之寂静可以想见。在词的上阕里所接触到的,只是物象,没有出现任何人的活动。眼前的是自然界,显得多么令人意兴索然。
“笙歌散尽游人去,始觉春空。”下阕前两句是说,游人尽兴散去,笙箫歌声也渐渐静息,才开始觉得一片空寂,又仿佛正需要这份安谧。“笙歌散尽”,虚写出过去湖上游乐的盛况;“游人去后,始觉春空”,点明从上面三句景象所产生的感觉,道出了作者的复杂微妙的心境。“始觉”是顿悟之词,这两句是从繁华喧闹消失后清醒过来的感觉,繁华喧闹消失,既觉有所失的空虚,又觉得获得宁静的畅适。首句说的“好”即是从这后一种感觉产生,只有基于这种心理感觉,才可解释认为“狼籍残红”三句所写景象的“好”之所在。
“垂下帘栊,双燕归来细雨中。”末两句是说,回到居室,拉起窗帘,等待着燕子的来临,直到双燕从蒙蒙的细雨中归来,才放下了帘子。
最后两句,写室内景,从而使人揣想,前面所写的一切,都是词人在室外凭栏时的观感。末两句是倒装。本是开帘待燕。“双燕归来”才“垂下帘栊”。着意写燕子的活动,反衬出室内一片清寂气氛。“细雨”字还反顾到上阕的室外景。落花飞絮,着雨更显得春事阑珊。这首词从室外景色的空虚写到室内气氛的清寂,通首体现出词人生活中的一种静观自适的情调。
这首词是欧阳修颍州西湖组词《采桑子》十首的第四首。诸词抒写作者以闲退之身恣意游赏的怡悦之情,呈现的景物都具有积极的美的性质,如“芳草长堤”、“百卉争妍”“空水澄鲜”等等。独此首赏会的是“狼籍残红”。整组词描写的时节景物为从深春到荷花开时,“狼籍残红”自然是这段过程中应有的一环。如果说诸词表现了词人作为闲人对各种景物的欢然会意,本词却不自觉的透露出来他此时的别样情绪。作者这时是以太子少师致仕而卜居颍州的。他生平经历过不少政治风浪,晚年又值王安石厉行新法,而不可与争,于是以退闲之身放怀世外,这组词总的是体现了他这种无所牵系的闲适心情。但人情往往也有这样的矛盾,解除世事的纷扰固然觉得轻快,而脱去世务又感到空虚。本词“笙歌散尽游人去,始觉春空”却是极其微妙的反映出这种矛盾的心情。结尾“垂下帘栊”两句,乃极静的境界中着以动象,觉余情袅袅,表现出对春的流连眷恋意识,不免微露怅惘的情绪。
这首诗颈联所谓“吾衰久矣双蓬鬓,归去来兮一钓丝”,反映的就是既然难遇明主,退隐才是正路的思想。其余各联首颔两联说荒园萧瑟、花鸟不通人情,自己也毫无情绪,典型地表现了刚刚从政治核心隐退时难免出现的苦闷消极情绪。转念一想,退隐方是上策(颈联),于是尾联提出:料想春水已涨,小船正停在岸边等待我驾舟泛游呢!全诗写心理活动,写思想情绪的变化,真实而深入;且全用形象的语言,显得含蓄而能尽意,表现了作者很强的艺术功力。
诗起笔描写暮春园景:园中已不再是百花争艳,而是又“荒”又“萧瑟”,可见其春老花残,落英狼藉。“懒追随”,透露出诗人已无游赏之兴。然而这“荒园”毕竟不乏“追随”者。那些燕与莺,又“舞”又“啼”,多么得意;但他们贪恋荒园,不过是因为腐枝败叶问小虫多,便于捕食罢了,故日“各自私”。这里,“各自私”的燕与莺,“萧瑟”的“荒园”,显然别有喻意,隐射时事,他联想到即将崩溃的南宋小朝廷,联想到朝廷中那班争权夺利的小人。颔联紧承首句。“日长”、“花老”,既点出暮春时令,也暗示诗人心绪。常言道:“欢愉恨夜短,愁闷觉日长。”昏昏醉眠,日长难遣,尊前花老,诗情难觅,于是止不住把满怀愁绪,直接抒写出来。
“吾衰久矣双蓬鬓,归去来兮一钓丝。”这是全诗的转折,也是全诗的点睛之笔。诗人由“花老”而联想到人老。这里“吾衰久矣”,既是字面义,也是暗用典。诗人巧借其意,以“吾衰久矣”慨叹当时南宋小朝廷不能振作,他所向往的大宋王朝一统天下的局面恢复无望。自己心力交瘁,回天乏术,只好“归去来兮一钓丝”——退归故里,隐居垂钓。“归去来兮”也是用典。陶渊明身处东晋行将灭亡之际,因不甘心向小人折腰,毅然抛弃官职,赋《归去来兮辞》,归隐故乡。诗人以陶渊明自况,表明了他的高洁情操。
诗到此,意旨已明,似无可说,但诗人荡开一笔,另辟新境:“想见篱东春涨动,小舟无伴柳丝垂。”好一幅江南水乡暮春图:春水漫漫,疏篱如屏,柳丝垂挂,小舟荡漾,该诗句描绘了一个美丽的意境。“小舟无伴”,那小舟似乎急切地等待诗人归来作伴哩。这里还需弄清“篱东”一词源于陶句“采菊东篱下”,后借指故园。这一联,不仅进一步渲染思归之情,而且这幅美好的暮春图,与开头那“萧条”的“荒园”,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更见诗人的爱憎和归意。“春涨动”、“柳丝垂”,还点明《春晚》诗题。
这首抒情诗深沉婉曲,寓愤世之情于暮春之景。描写景物,不作精雕细刻,意会即止;描写心境,也只略现迹象,巧妙用典,使情意表达委婉含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