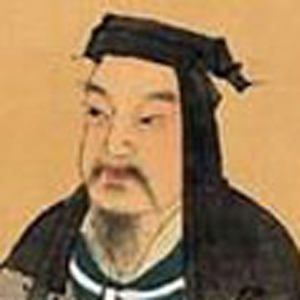这首诗是写古时的读书人,一心埋头书案,浸沉在书中的那种专注精神。一、二句表现书房的宁静,三、四句表明自己专心读书,因此,春天过去了许久,也不知道,只是在瓦雀影动、杨花入砚的惊扰中,才晓得已是暮春时节。语言平易,景物生动贴切,开头两句对仗得也很自然,增强了喜悦的气氛。
一二句“双双瓦雀行书案,点点杨花入砚池。”一心埋头书案,浸沉在书中的那种专注精神。十分宁静的书室,垂柳飞絮的季节,春风娇弱的日子,屋里似乎没人,几只麻雀儿悠闲自在地漫步在书桌上,柳絮轻盈地随风飘落,赖在砚台上不肯动弹,竟然无人拂拭。书室的宁静是由动态的画面表现出来的。这里感觉不到人的影响。不然,麻雀不能闲步书案,柳絮那得安卧砚台。这是以动衬静的反衬手法。
书室里其实有人,那是诗人,“闲坐小窗读《周易》”。然而,书室却宁静得似乎没有人的存在,看来书室的一切动静同诗人都毫不相干,他如老僧入定,全部心思都在《周易》这本书上呢。书室的宁静正衬托出诗人的宁静。
结句“不知春去几多时”是推进一层的写法,拓展了全诗的时间容量。诗句描写的是眼前之景,表现的却是一春之事,花开花落纯任自然,诗人未曾留意,何尝动心。进一步表现了诗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然而,这只是这首诗的表层意思。
“闲坐小窗读《周易》”,《周易》的哲学思想是理学的理论基础,诗人通过这一细节,不着痕迹地透露了全诗的主旨。当诗人全身心地沉浸在理学世界中的时候,内心世界一片从容,一片自然和乐,世间万物都不能进入他的意识。诗人表现的是他的理学涵养功夫。
这首诗通篇是一个女子睹旧物而生哀怨的语气。由“织锦”这个典故可知,这首诗的主人公是位思妇,其丈夫或游宦,或征戍,不必坐实。她感叹青春不再,桃李疏,芙蓉落,已到了人生的秋天。
“楼前桃李疏,池下芙蓉落”。这是思妇眼中之景,而且景中寓情。可以想象这位少妇,独坐幽闺,愁眉深锁,凝神呆望着楼外。流光冉冉,桃李之花已经纷纷落下,花疏叶繁,大好春光即将逝去,这就增添了她许多愁绪。次句写秋天。池塘之中,秋风乍起,荷花飘零,黯然凝望,惆怅无限。舒亶《虞美人》中的“芙蓉落尽天涵水,日暮沧波起”,情景亦相似。第三句谓织锦以寄相思,然思极恨极,致使思绪繁乱,未能织成。此中有相思莫寄、四顾茫然之意。末句以景结情,用蟋蟀鸣声入于深闺罗帏来渲染秋夜凄凉的气氛。在古诗词中,蛰声往往同织妇联系在一起,且多写夜间悲愁。如姜夔《齐天乐·蟋蟀》云:“哀音似诉,正思妇无眠,起寻机杼。”陆龟蒙《子夜变歌三首》云:“蟋蟀吟堂前,惆怅侬愁。”秋凉已届,万户捣衣,又是最为关情之事;岁云将暮,又是一年,不禁令人倍增哀愁。
王国维说:“一切景语皆情语也。”王夫之也说:“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这首诗,除第三句用典为情语之外,共他三句皆为景语。然而却是情景相生,互藏其宅,交融一体,妙合无垠。在结构方面,首句写春,次句写秋,两句结合,暗示春秋代序,年华转换,迟暮之感,相思之殷,尽在其中。末句以景托情,总括全诗,意在言外,余韵悠然。
这是一首祝酒歌。前两句敬酒,后两句祝辞。话不多,却有味。诗人以稳重得体的态度,抒写豪而不放的情意,在祝颂慰勉之中,道尽仕宦浮沉的甘苦。
古人用“金屈卮”敬酒,以示尊重。诗人酌满金屈卮,热诚地邀请朋友干杯。“不须辞”三字有情态,既显出诗人的豪爽放达,又透露友人心情不佳,似乎难以痛饮,于是诗人殷勤地劝酒,并引出后两句祝辞。
从后两句看,这个宴会大约是饯饮,送别的那个朋友大概遭遇挫折,仕途不利。对此诗人先作譬喻,大意说,你看那花儿开放,何等荣耀,但是它还要经受许多次风雨的摧折。言外之意是说,大自然为万物安排的生长道路就是这样曲折多磨。接着就发挥人生感慨,说人生其实也如此,就要尝够种种离别的滋味,经受挫折磨炼。显然,诗人是以过来人的体验,慰勉他的朋友。告以实情,晓以常理,祝愿他正视现实,振作精神,可谓语重心长。
于武陵一生仕途不达,沉沦不僚,游踪遍及天南地北,堪称深谙“人生足别离”的况味的。这首《劝酒》虽是慰勉朋友之作,实则也是自慰自勉。正因为他是冷眼看人生,热情向朋友,辛酸人作豪放语,所以形成这诗的独特情调和风格,豪而不放,稳重得体。后两句具有高度概括的哲理意味,近于格言谚语,遂为名句,颇得传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