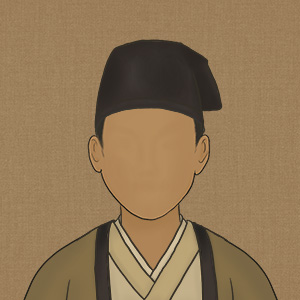《九歌》是屈赋中最精、最美、最富魅力的诗篇。它代表了屈原艺术创作的最高成就。《九歌》以楚国宗祖的功德和英雄业绩为诗;以山川神祇和自然风物为诗;以神话故事和历史传说为诗,淋漓尽致地抒发了诗人晚年放逐南楚沅湘之间忠君爱国、忧世伤时的愁苦心情和“荡志而愉乐”,“聊以舒吾忧心”,“寓情草木,托意男女”,“吟咏情性,以风其上”的心旨。
《九歌》包括11章,前人为了使它们符合“九”的成数,曾作过种种凑合。如清代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主张《湘君》、《湘夫人》并为一章,《大司命》、《少司命》并为一章。《闻一多》《什么是九歌》主张以《东皇太一》为迎神曲,《礼魂》为送神曲,中间九章为“九歌”正文。但多数人的意见,以“九”为虚数,同意汪瑗《楚辞集解》、王夫之《楚辞通释》之说,认为前十章是祭十种神灵,所祭的十种神灵,从古代人类宗教思想的渊源来考察,都跟生产斗争与生存竞争有密切关系。十种神灵又可分为三种类型:①天神──东皇太一(天神之贵者)、云中君(云神)、大司命(主寿命的神)、少司命(主子嗣的神)、东君(太阳神);②地□──湘君与湘夫人(湘水之神)、河伯(河神)、山鬼(山神);③人鬼──国殇(阵亡将士之魂)。有人认为,在上述十种神灵里面,篇首“东皇太一”为至尊,篇末“国殇”为烈士,都是男性;其余则是阴阳二性相偶,即东君(男)与云中君(女),大司命(男)与少司命(女),湘君(男)与湘夫人(女),河伯(男)与山鬼(女)。《九歌》原来的篇次,也基本上是按照上述的关系排列的,今本《东君》误倒(闻一多《楚辞校补》)。
从《九歌》的内容和形式看,似为已具雏形的赛神歌舞剧。《九歌》中的“宾主彼我之辞”,如余、吾、君、女(汝)、佳人、公子等,它们都是歌舞剧唱词中的称谓。主唱身份不外三种:一是扮神的巫觋,男巫扮阳神,女巫扮阴神;二是接神的巫觋,男巫迎阴神,女巫迎阳神;三是助祭的巫觋。所以《九歌》的结构多以男巫女巫互相唱和的形式出现。清代陈本礼就曾指出:“《九歌》之乐。有男巫歌者。有女巫歌者;有巫觋并舞而歌者;有一巫唱而众巫和者。”(《屈辞精义》)这样,《九歌》中便有了大量的男女相悦之词,在宗教仪式、人神关系的纱幕下,表演着人世间男女恋爱的活剧。这种男女感情的抒写,是极其复杂曲折的:有时表现为求神不至的思慕之情,有时表现为待神不来的猜疑之情,有时表现为与神相会的欢快之情,有时表现为与神相别的悲痛与别后的哀思。从诗歌意境上看,颇有独到之处。
朱熹曾评《九歌》说:“比其类,则宜为三《颂》之属;而论其辞,则反为《国风》再变之《郑》、《卫》矣。”(《楚辞辩证》)同是言情之作,而《九歌》较之《诗经》的郑、卫之风,确实不同。但这并非由于“世风日下”的“再变”,而是春秋战国时期南北民族文化不同特征的表现。郑、卫之诗,表现了北方民歌所特有的质直与纯朴;而《九歌》则不仅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宗教外衣,而且呈现出深邃、幽隐、曲折、婉丽的情调,别具一种奇异浓郁的艺术魅力。
男女之情并不能概括《九歌》的全部内容。作为祭歌,由于它每一章所祭的对象不同,内容也就有所不同,如《东皇太一》的肃穆,《国殇》的壮烈,便与男女之情无涉。《国殇》是一首悼念阵亡将士的祭歌,也是一支发扬蹈厉、鼓舞士气的战歌。它通过对激烈战斗场面的描写,热烈地赞颂了为国死难的英雄,从中反映了楚民族性格的一个侧面。
《九歌》是以娱神为目的的祭歌,它所塑造的艺术形象,表面上是超人间的神,实质上是现实中人的神化,在人物感情的刻画和环境气氛的描述上,既活泼优美,又庄重典雅,充满着浓厚的生活气息。
此诗先是描写蝉的境遇,后面直接跳到自身的遭遇上来,直抒胸臆,感情强烈,最后却又自然而然地回到蝉身上,首尾圆融,意脉连贯。全诗以蝉起,以蝉结,章法紧密,对蝉的刻画与诗人的情意婉转表达到了浑然交融与统一,是托物咏怀的佳作。
“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首联以蝉的生活习性起兴。“高”以蝉栖高树暗喻自己的清高;蝉的“难饱”又与作者身世感受暗合。由“难饱”而引出“声”来,所以哀中又有“恨”。但这样的鸣声却是徒劳,并不能使它摆脱难饱的困境。这是说,作者由于为人清高,所以生活清贫,虽然向有力者陈情,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最终却是徒劳的。这样结合作者自己的感受来咏物,看似把物的本来面貌歪曲,因为蝉本来没有“难饱”和“恨”。作者这样说,看似不真实了,但咏物诗的真实,是作者感情的真实。作者确实有这种感受,借蝉来写,只要“高”和“声”是和蝉符合的,作者可以写出他对“高”和“声”的独特感受来,可以写“居高声自远”(虞世南《咏蝉》),也可以写“本以高难饱”,这两者对两位不同的作者都是真实的。
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颔联是说,五更以后疏落之声几近断绝,满树碧绿依然如故毫不动情。
蝉的鸣声到五更天亮时,已经稀疏得快要断绝了,可是一树的叶子还是那样碧绿,并不为它的“疏欲断”而悲伤憔悴,显得那样冷酷无情。这里接触到咏物诗的另一特色,即无理得妙。蝉声的“疏欲断”,与树叶的“碧”两者本无关涉,可是作者却怪树的无动于衷。这看似毫无道理,但无理处正见出作者的真实感情。“疏欲断”既是写蝉,也是寄托自己的身世遭遇。就蝉说,责怪树的“无情”是无理;就寄托身世遭遇来说,责怪有力者本可以依托荫庇而却“无情”,是有理的。咏物诗既以抒情为主,所以这种无理在抒情上就成了有理了。
“薄宦梗犹泛,故园芜已平。”颈联是说,我官职卑下像桃梗漂流不定,家园长期荒芜杂草早已长平。
颈联来一个转折,抛开咏蝉,转到自己身上,这一转就打破了咏蝉的限制,扩大了诗的内容。作者在各地当幕僚,是个小官,所以称“薄宦”。经常在各地流转,好像大水中的木偶到处漂流。这种不安定的生活,使他怀念家乡,更何况家乡田园里的杂草和野地里的杂草已经连成一片了,作者思归就更加迫切。这两句好像和上文的咏蝉无关,暗中还是有联系的。“薄宦”同“高难饱”、“恨费声”联系,小官微禄,所以“难饱”、“费声”。经过这一转折,上文咏蝉的抒情意味就更明白了。
“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又回到咏蝉上来,用拟人法写蝉。“君”与“我”对举,把咏物和抒情密切结合,而又呼应开头,首尾圆合。蝉的难饱正与我也举家清贫相应;蝉的鸣叫声,又提醒我这个与蝉境遇相似的小官,想到“故园芜已平”,不免勾起赋归之念。钱钟书先生评论这首诗说:“蝉饥而哀鸣,树则漠然无动,油然自绿也(油然自绿是对“碧”字的很好说明)。树无情而人(‘我’)有情,遂起同感。蝉栖树上,却恝置(犹淡忘)之;蝉鸣非为‘我’发,‘我’却谓其‘相警’,是蝉于我亦‘无情’,而我与之为有情也。错综细腻。”钱先生指出不仅树无情而蝉亦无情,进一步说明咏蝉与抒情的错综关系。
咏物诗,贵在“体物为妙,功在密附”。这首咏蝉诗,“传神空际,超超玄著”,被朱彝尊誉为“咏物最上乘”。诗人借蝉栖高饮露的个性来表现自己高洁的品格,可谓借物咏怀的典型。
这首词以轻浅的色调、幽渺的意境,描绘一个女子在春阴的清晨里所生发的淡淡哀愁和轻轻寂寞。全词意境怅静悠闲,含蓄有味。
每一次春来,就是一次伤春的体验。词人之心,很早就发出了“为问新愁,何事年年有”的愁怨。然而他们的命运也往往是一年年地品尝春愁。此词抒写的是淡淡的春愁。它以轻淡的色笔、白描的手法,十分熨贴地写出了环境氛围,即把那一腔淡淡的哀怨变为具体可感的艺术形象渗透出来,表情深婉、幽缈。“一片自然风景就是一种心情”。索漠轻寒中袅袅而升的是主人公那轻轻的寂寞和百无聊赖的闲愁。即景生情,因情生景,情恰能称景,景也恰能传情,这便是词作的境界。
上片写天气与室内环境的凄清,通过写景渲染萧瑟的气氛,不言愁而愁自见。起首一句“漠漠轻寒上小楼”,笔意轻灵,如微风拂面,让人不自觉地融入其中,为全词奠定了一种清冷的基调。随后一句还是写天气,强调“轻寒”。初春之寒,昏晓最甚。更何况阴云遮日,寒意自然更深一步,难怪会让人误以为是深秋时节。“无赖”二字暗指女主人公因为天气变化而生出丝丝愁绪。“淡烟”一句视角从室外转到室内,画屏之上,淡烟流水,亦是一片凄清模样,让人不禁生出一丝淡淡的哀愁。
下片写倚窗所见,转入对春愁的正面描写。不期然而然中,他的视线移向了窗外:飞花袅袅,飘忽不定,迷离惝恍;细雨如丝,迷迷蒙蒙,迷漫无际。见飞花之飘缈,不禁忆起残梦之无凭,心中顿时悠起的是细雨蒙蒙般茫无边际的愁绪。本写春梦之无凭与愁绪之无际,却透过窗户摄景着笔于远处的飞花细雨,将情感距离故意推远,越发感生出一种飘缈朦胧、不即不离之美。亦景亦情而柔婉曲折,是“虽不识字人,亦知是天生好言语”(《人玉屑》卷二十一引晁无咎语)的佳例。词人将“梦”与“愁”这种抽象的情感编织在“飞花”、“丝雨”交织的自然画面之中。这种现象,约翰·鲁斯金称为“感情误置”,而这在中国诗词中则为司空见惯。“自在飞花”,无情无思,格外惹人恼恨,而反衬梦之有情有思。最后,词以“宝帘闲挂小银钩”作结,尤觉摇曳多姿。细推词脉,此句应为过片之倒装句。沉迷于一时之幻境,不经意中瞥向已经挂起的窗帘外面,飞花丝雨映入眼帘,这便引出“自在”二句之文。而在结构艺术上,词人作如是倒装,使得词之上、下片对称工整,显得精巧别致,极富回环变化的结构之美。同时,也进一步唤醒全篇,使帘外的种种愁境,帘内的愁人更为分明,不言愁而愁自现。句中“闲”字,本是形容物态,而读者返观全篇,知此正是全词感情基调──百无聊赖的情感意绪。作为红线贯串打通全词,一气运转,跌宕昭彰。
此词以柔婉曲折之笔,写一种淡淡的闲愁。在生活中,每个人都会拥有自己的一份闲愁。不知何时何处,它即从你心底无端地升起,说不清也拂不去,令人寂寞难耐。词人们又总是能更敏锐地感受到它,捕捉住它,并流诸笔底。而此时,又必然会渗透进他们对时世人生的独特感受。冯延巳的《鹊踏枝》写出了人人心中皆有的这般闲情,却也包蕴着一种由时代氛围所酿成的说不清、排不开的愁绪。“古之伤心人也”的秦观,年少丧父,仕途抑塞,于新旧党迭为消长之际,一再受到排抑,满腹满腔人生的遭际感慨,泛化为一种凄怨感伤的心境意绪而弥漫于词作之中,呈现出含蓄蕴藉、窈深幽约之美。此词曲折传情而凄清婉美,《词则大雅集》卷二称“宛转幽怨,温韦嫡派”。作为婉约派词人,他正是远祖温韦,近承晏柳,融各家所长为一体,成其细腻含蓄而又凄怨感伤之风格,吟唱出较“花间”、“尊前”更为绸缪凄婉的角声,别具一番魅力。
就思想内容来说,秦观的词多写艳情,与晏几道、柳永相似,但却能以语言的翻新、情致的幽趣历来受人激赏。这首词写的是春愁,一种细微幽渺的、不容易捉摸的感情,但作者以他非凡的功力,借具体的景物描写和形象的比喻,将它表现了出来。最具代表性的是它的“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它将细微的景物与幽渺的感情极为巧妙而和谐地结合在一起,使难以捕捉的抽象的梦与愁成为可以接触的具体形象。沈祖棻《宋词赏析》分析这两句时,说:“它的奇,可以分两层说。第一,‘飞花’和‘梦’, ‘丝雨’和‘愁’,本来不相类似,无从类比。但词人却发现了它们之间有‘轻’和‘细’这两个共同点,就将四样原来毫不相干的东西联成两组,构成了既恰当又新奇的比喻。第二,一般的比喻,都是以具体的事物去形容抽象的事物,或者说,以容易捉摸的事物去比譬难以捉摸的事物。但词人在这里却是反其道而行之。他不说梦似飞花,愁如丝雨,而说飞花似梦,丝雨如愁也同样很新奇。”这两句用语奇绝,特别具有一种音乐美、诗意美和画境美。
在文学大家的笔下,对情、意表达的处理常见“举重若轻”和“举轻若重”两种方式。它们都会有理想的表达效果,但秦观在这里的幽情轻吐却有如此的效果,依赖于其善于渲染、语言精美、比喻神奇,但更关键的是内中的那种情致。冯煦称赞说:“他人之词,词才也;少游,词心也。得之于内,不可以传。”秦观的个人气质与文体特征已经融而为一。这首词没有一处用重笔,没有痛苦的呐喊,没有深情的倾诉,没有放纵自我的豪兴,没有沉湎往事的不堪。只有对自然界“漠漠轻寒”的细微感受,对“晓阴无赖”的敏锐体察,对“淡烟流水”之画屏的无限感触。这春愁,既没有涉及政治,又没有涉及爱情、友谊,或者其他什么。它其实只是写了一种生活的空虚之感。在一个敏感文人的心里,这种空虚寂寞伴随生命的全程,它和愿望、和理想、和对生命的珍视成正比,无边无际,无计可除。
前人评陶,统归于平淡,又谓“凡作清淡古诗,须有沉至之语,朴实之理,以为文骨,乃可不朽”(施补华《岘佣说诗》)。陶渊明生于玄言诗盛行百年之久的东晋时代,“理过其辞,淡乎寡味”乃诗坛风尚,故以理为骨,臻于平淡皆不为难,其可贵处倒在淡而不枯,质而实绮,能在真率旷达的情意中化入渊深朴茂的哲理,从田园耕凿的忧勤里讨出人生天然的乐趣。读陶诗《移居二首》其二,即可知此意。
全诗以自在之笔写自得之乐,将日常生活中邻里过从的琐碎情事串成一片行云流水。首二句“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暗承第一首结尾“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而来,篇断意连,接得巧妙自然。此处以“春秋”二字发端,概括全篇,说明诗中所叙并非“发真趣于偶尔”(谢榛《四溟诗话》),而是一年四季生活中常有的乐趣。每遇风和日丽的春天或天高云淡的秋日,登高赋诗,一快胸襟,历来为文人引为风雅胜事。对陶渊明来说,在柴桑火灾之后,新迁南村,有此登临胜地,更觉欣慰自得。登高不仅是在春秋佳日,还必须是在农务暇日,春种秋获,正是大忙季节,忙里偷闲,登高赋诗,个中趣味决非整天悠哉游哉的士大夫所能领略,何况还有同村的“素心人”可与共赏新诗。所以士大夫常有的雅兴,在此诗中便有不同寻常的意义。这两句用意颇深却如不经意道出,虽无一字刻划景物,而风光之清靡高爽,足堪玩赏,诗人之神情超旷,也如在眼前。
移居南村除有登高赋诗之乐以外,更有与邻人过从招饮之乐:“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这两句与前事并不连属,但若作斟酒品诗理解,四句之间又似可承接。过门辄呼,无须士大夫之间拜会邀请的虚礼,态度村野,更觉来往的随便。大呼小叫,毫不顾忌言谈举止的风度,语气粗朴,反见情意的真率。“相呼”之意可能是指邻人有酒,特意过门招饮诗人;也可能是诗人有酒招饮邻人,或邻人时来串门,恰遇诗人有酒便一起斟酌,共赏新诗。杜甫说:“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客至》)“叫妇开大瓶,盆中为吾取。……指挥过无礼,未觉村野丑。”(《遭田父泥饮》)诸般境界,在陶诗这两句中皆可体味,所以愈觉含蓄不尽。
当然,人们也不是终日饮酒游乐,平时各自忙于农务,有闲时聚在一起才觉得兴味无穷:“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辄披衣,言笑无厌时。”有酒便互相招饮,有事则各自归去,在这个小小的南村,人与人的关系非常实在,非常真诚。“各自归”本来指农忙时各自在家耕作,但又与上句饮酒之事字面相连,句意相属,给人以酒后散去、自忙农务的印象。这就像前四句一样,利用句子之间若有若无的连贯,从时间的先后承续以及诗意的内在联系两方面,轻巧自如地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琐事融成了整体。这句既顶住上句招饮之事,又引出下句相思之情。忙时归去,闲时相思,相思复又聚首,似与过门相呼意义重复,造成一个回环,“相思则披衣”又有意用民歌常见的顶针格,强调了这一重复,使笔意由于音节的复沓而更加流畅自如。这种往复不已的章法在汉诗中较常见,如《苏武诗》、《古诗十九首·西北有高楼》、《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等,多因重叠回环、曲尽其情而具有一唱三叹的韵味。陶渊明不用章法的复叠,而仅凭意思的回环形成往复不已的情韵,正是其取法汉人而又富有独创之处。何况此处还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诗意的深化。过门招饮,仅见其情意的真率,闲时相思,才见其友情的深挚。披衣而起,可见即使已经睡下,也无碍于随时相招,相见之后,谈笑起来没完没了,又使诗意更进一层。如果说过门辄呼是从地邻关系表明诗人与村人的来往无须受虚礼的限制,那么披衣而起、言笑无厌则表明他们的相聚在时间上也不受俗态的拘束。所以,将诗人与邻人之间纯朴的情谊写到极至,也就将摒绝虚伪和矫饰的自然之乐倾泻无余。此际诗情已达高潮,再引出“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的感叹,便极其自然了。这两句扣住移居的题目,写出在此久居的愿望,也是对上文所述过从之乐的总结。不言“此乐”,而说“此理”,是因为乐中有理,由任情适意的乐趣中悟出了任自然的生活哲理比一切都高。从表面上看,这种快然自足的乐趣所体现的自然之理与东晋一般贵族士大夫的玄学自然观没有什么两样。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说:“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似乎也可以用来解释陶渊明《移居二首》其二中的真趣所在。但同是“人之相与”、“欣于所遇”之乐,其实质内容和表现方式大不相同。东晋士族自恃阀阅高贵,社会地位优越,每日服食养生,清谈玄理,宴集聚会所相与之人,都是贵族世家,一时名流;游山玩水所暂得之乐,亦不过是无所事事,自命风雅;他们所寄托的玄理,虽似高深莫测,其实只是空虚放浪的寄生哲学而已。陶渊明的自然观虽然仍以玄学为外壳,但他的自然之趣是脱离虚伪污浊的尘网,将田园当作返朴归真的乐土;他所相与之人是淳朴勤劳的农夫和志趣相投的邻里;他所寄托的玄理,朴实明快,是他在亲自参加农业劳动之后悟出的人生真谛。所以,此诗末二句“忽跟农务,以衣食当勤力耕收住,盖第耽相乐,本易务荒,乐何能久,以此自警,意始周匝无弊,而用笔则矫变异常”(张玉谷《古诗赏析》)。结尾点明自然之乐的根源在于勤力躬耕,这是陶渊明自然观的核心。“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诗人认为人生只有以生产劳动、自营衣食为根本,才能欣赏恬静的自然风光,享受纯真的人间情谊,并从中领悟最高的玄理——自然之道。这种主张力耕的“自然有为论”与东晋士族好逸恶劳的“自然无为论”是针锋相对的,它是陶渊明用小生产者朴素唯物的世界观批判改造士族玄学的产物。此诗以乐发端,以勤收尾,中间又穿插以农务,虽是以写乐为主,而终以勘为根本,章法与诗意相得益彰,但见笔力矫变而不见运斧之迹。全篇罗列日常交往的散漫情事,以任情适意的自然之乐贯串一气,言情切事,若离若合,起落无迹,断续无端,文气畅达自如而用意宛转深厚,所以看似平淡散缓而实极天然浑成。
由此可见,作诗以理为骨固佳,其尤贵者当善于在情中化理。晋宋之交,玄风大炽,一般诗人都能谈理。山水诗中的谈玄说理成份多为后人所訾议,而产生于同时的陶渊明田园诗中亦有不少谈理之作,却博得了盛誉。原因就在刚刚脱离玄言诗的山水诗多以自然证理,理赘于辞;而陶诗则能以情化理,理入于情,不言理亦自有理趣在笔墨之外,明言理而又有真情融于意象之中。这种从容自然的境界,为后人树立了很高的艺术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