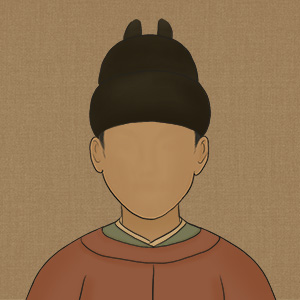这首词写游览所见所感。
上片写游湖时所见:风微微地吹,波轻轻地荡,圆荷上的露点如珍珠闪闪,绘出了初秋明丽的背景,“何处”二句,写出在画面中的人物,“吴娃越艳”,都是漂亮活泼的南国少女,“藕花红照脸”,这一句简洁俊秀,表现了姑娘们的青春的美丽。
下片写游客的心情,借用了乐府中《大堤曲》赞美少女的内容,来表示游客对吴娃越艳的倾慕。“烟波隔”,是说姑娘们渐渐远去。“渺渺湖光白”,他还留连不舍,目送舟行,直至再也看不见人影儿,只剩下湖光渺渺。“身已归,心不归”,出语直率,情真意切。结尾二句,景中有情,有温庭筠“斜晖脉脉水悠悠”之意。全词情意真挚,笔墨清丽明快,非凑数之作可比。
这首《伤春》诗写的是诗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感受。首句写诗人做的一个决定:对今春乐事早已安排好;次句用一个转折,推翻了之前的决定,也就辜负了好意送来春色的东风。第三句点明,不仅今年先做决定再推翻,而且年年如此;第四句指出年年辜负春光的原因。
春日可乐,而自己却非愁即病,年年都辜负了大好春光,这种主观与客观的矛盾对立使诗人禁不住感慨万端,发出一种无可奈何的叹息。读罢此诗,诗人愁病交加的面容、苦笑的表情和自嘲的意味,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不假雕饰,自然浑成,而诗意诗味即在其中,这正是“诚斋体”的成功之处。
杨万里在《荆溪集自序》中谈到自己写诗时,曾说:“步后园,登古城,采撷祀菊,攀翻花竹,万象毕来,献余诗材。盖麾之不去,前或未应,而后者己迫。”在他看来,平日所见所闻及所感似乎无不可以成为诗歌创作的材料,这和江西派“闭门觅句”,讲究“无一字无来处”,“虽只字半句不轻出”的苦吟自然是大不相同的了。但“诚斋体”也有其弊病:由于写作比较“随便”,有些诗艺术概括不够,境界不高,社会意义也不大。此首可以说是个典型。
这首诗第一句写养蚕的辛勤劳苦。诗人在这里没有过多地描写养蚕的过程,只是用“辛勤”与“得茧不盈筐”互相对照,突出了蚕事的艰辛。人们心中充满了怨恨,因此诗人在下句说这些养蚕人“灯下缥丝恨更长”。这句诗用茧丝来比喻蚕农的恨,既形象又贴切。劳动人民每天深夜都要抽丝织布,每一缕丝都是蚕农辛酸的记录,但是他们享受不到自己劳动的果实。劳动果实被统治者白白拿去,所以在他们心中充满了怨恨,那每一声织机的声响都是劳动人民的叹息,都是劳动人民的诉说。
第三句诗锋一转,写穿绫罗绸缎的贵人。他们穿着华美的衣服,然而他们哪里知道蚕农和织妇的辛酸,他们只知贪爱绣在绸缎上的鸳鸯图案。这样,这首诗的中心思想就更为明显,更清楚地点明封建社会贫富的对立,写出劳动人民对那些不劳而获的寄生虫的愤恨和鄙视,诗的社会意义就更深刻,社会作用更广泛了。
全诗语言通俗,明白如话,前两句同后两句构成对比,使诗意更加鲜明,加强了诗的表现力,使诗的主题揭示得更加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