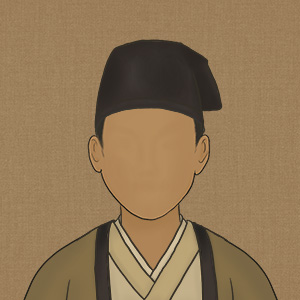从汉“柏梁体”开始,叹收六朝声律对仗,七言诗逐渐赶上五言诗;并从初唐开始分流,为新兴近体律绝,和乐府歌行。“初唐四杰”对七言古诗也作出巨大贡献。卢照邻的《长安古意》与《行路难》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行路难》是《乐府·杂曲歌辞》旧题,在卢照邻之前,鲍照就作过一首七言《行路难》,仄声促韵与长句宛转,充分表达悒郁不平之气。卢照邻这一首从容舒展,徐缓不迫,多次转韵;其声律、修辞、与对仗明显受六朝诗歌影响,从中也反映了诗风转变期的艺术特点。
全诗共四十句,分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从开头到“万古摧残君讵知?”“长安城北渭桥边”为虚指,即物起兴,从眼前横槎、枯木倒卧古田引起联想,“昔日”领起下文十六句,对“枯木”曾经拥有的枝繁叶茂,溢彩流芳的青春岁月,进行淋漓尽致的铺陈与渲染。围绕着它“千尺长条百尺枝”,有黄莺戏春,凤凰来巢,鸳鸯双栖,高贵的丹桂青榆也依附庇荫,更有香车宝马时常经过,马蹄声断续相闻;富有而轻薄的公子,妖冶的倡女,纷趋竞骛,攀龙附凤。诗人以工整的结构,华丽的语言,为我读者展现了初唐长安城内繁荣市井,骄奢生活的世态风情全卷,读者仿佛身临其境,却又清醒地感觉到诗人冷静的态度。从行文遣辞看,整齐的偶句与变换的角度,避免了呆滞散乱;层迭的词句增添了构图的对衬感与节奏感。末两句是全诗关键,也是主旨所在。从现实的“一朝零落无人问”,由此及彼提出“万古摧残君讵知”,已如桓温当年“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普遍人生感喟,将比兴之义进一步升华了。
第二部分从“人生贵贱无终始”到末句,由隐而显,喻体“枯木”显现为本体“人生”。“终始”指无限。转瞬即逝的人生与悠久无限的岁月,这对亘古不变的自然矛盾造成人们心灵的困惑,一系列抒情意象即由此展开。“谁家”以下(至“赤心会合在何时”)运用超时空框架,不断变换叙述角度,使生死枯荣的单一主题,形成多元层次与丰富内涵。先写时光流水,无人能阻,再写改朝换代,秦川汉陵,无可奈何;再写富贵公卿,顷刻归于青棘黄泉。由此进一步指出富贵不可骄,交情不足恃,都用复迭或对比手法。金貂换酒为李白《将进酒》所本;“玉尘”指玉骢马扬起的飞尘,狂饮与游冶似乎已解生死,其实正说明了无法排遣的苦闷。既然功名利禄都只是过眼云烟,就只好求友访仙以解心中积怨。因此,唐代盛行道教,许多官僚士大夫接受道教。诗人说:纵然平日有生死交情,但只要大限到来,你未抵“苍龙阙下”(苍龙,东方之神,二十八宿东七星总称),我则已羽化白鹤山前。至于云间海上的仙山,长生不死的仙丹,更是飘缈难觅。
道家与佛家都有转世说,即使退一步寻求“赤子”重生,要到什么时候呢?表面是消极、苦闷乃至放浪形骸,其实仍融注了对人生热烈执着的追求,因此结末两句“但愿尧年一百万,长作巢由也不辞!”尧年,代长寿;巢由,巢父与许由,古时隐士。“但愿”“长作”可见其辞情恳切。卢照邻因服丹中毒,手足痉挛,最终不堪恶疾所苦,自投颍水,这里似有忏悟,只祈求正常人的健康长寿,不奢求富贵荣华与长生不死。
初唐四杰对于诗体诗风的转变,最突出之贡献是扩大了时空境界,将目光由宫廷移向社会,转向丰富多彩的现实人生。他们对历史、对人生、对物质、对理想都常常有发人深省的理解与阐释,使诗歌气势宏远,哲理性强,有很深的社会意义。
这是一首仅三十三字的小令词。这首词采用神话传说故事作题材,描写刘、阮和仙女离别时的依依不舍之情,表达了别后对佳人的深深思念之情。
“曾宴桃源深洞,一曲清歌舞凤。”曾宴,点明往事。桃源深洞,“舞凤”,即凤舞,为叶韵,乃倒用,言伊人如凤之舞。词中写刘晨、阮肇天台遇仙女故事,省去全部细节,只将初会和离别时最深的印象加以形象化的概括,高度精炼。清歌凤舞,风光何等旖旎!
“长记欲别时,和泪出门相送。”“长记”二字是关键,记忆中的情景是那么的美好,可这一切已如梦幻,永无再现之期。小词没有多少篇幅,不容铺叙,要求写得很精粹,所以“长记”以下几句对整个宴别的过程便撷取了送别这一高潮时的场面来写。“长记”二字,上接“曾宴”二字,“和泪出门相送”写送别之悲痛,这是实写,下面旋又转入虚写。
“如梦!如梦!残月落花烟重。”“如梦!如梦!”诗有诗眼,词亦有词眼,这四个字实为本词之眼。如梦者,昔年之事如一场无凭的春梦,昔年之景只能在梦里再现,昔年之倡除非在梦里相逢。叠用两个“如梦”,显得更为惆怅,更为感伤。残月乃夜阑之景,落花烟重乃暮春之景,伤心人别有怀抱,才会有凄凉的感觉,更显萧瑟的气氛,言尽而意不尽。
这首小令,抒情细腻,婉丽多姿,辞语美,意境更美。词人描绘了曾和佳人在理想的世外桃源之地相聚时的情景,此为虚写梦中之景的美好,成为感情之流回旋奔涌而下之处,回忆如梦,因而显得特别含蕴丰富;梦醒时分,侧重于对眼前情景的刻画,眼前的半轮残月和簌簌坠落的花瓣,如烟一样的月色,给全词笼上了迷蒙孤寂的气氛,在这凄清的夜里,对她的思念绵绵不断,如此深沉。虚实两端互相补充,形成“以闲淡之景,寓浓丽之情”的特色,更显意味深长。
全诗十六章,前八章每章八句,刺厉王失政,好利而暴虐,以致民不聊生,故激起民怨;后八章每章六句,责同僚,然亦道出厉王用人不当,用人不当亦厉王之过失。故毛传总言为刺厉王。
首章以桑为比,桑本茂密,荫蔽甚广,因摘采至尽而剥落稀疏。比喻百姓下民,受剥夺之深,不胜其苦,故诗人哀民困已深,呼天而诉曰:“瘼彼昊天,宁不我矜。”意谓:高明在上的苍天啊,怎么不给我百姓以怜悯呢!诗意严肃,为全诗之主旨。
次章至第四章,述祸乱之本,乃是缘于征役不息,民无安居之所。“四牡骙骙,旟旐有翩”,谓下民已苦于征役,故见王室之车马旌旗,而痛心疾首曰:“乱生不夷,靡国不泯。民靡有黎,具祸以烬。”意思是说:乱子不平息国家就要灭亡,现 在民间黑发的丁壮已少,好比受了火灾很多人都成为灰烬了。国以民为本,民瘼深重,而国危矣。诗人对此情况,更大声疾呼云:“於乎有哀,国步斯频!”感叹国运危蹙,必无长久之理,必致蹈危亡之祸。三章感叹民穷财尽,而天不助我,人民无处可以安身,不知往何处为好,因而引起君子的深思。君子本无欲无求,扪心自问没有争权夺利之心,但念及国家前途,不免发出谁实为此祸根,至今仍为民之病害的浩叹。四章感慨“我生不辰,逢天僤怒”。“我生不辰”,谓生不逢时。诗人之言如此,可见内心殷忧之深。他从人民的角度出发,痛感人民想安居,而从西到东,没有能安居的处所。人民怀念故土故居,而故土故居都因征役不息不能免于祸乱。人民既受多种灾难的侵袭,更担心外患侵凌,御侮极为迫切。天怒民怨,而国王不恤民瘼,不思改变国家的政治,因此诗人忧心如捣,为盼国王一悟而不可得深怀忧愤。仅此四章,已可见暴政害民,深重到何等程度。
五章至八章,是诗人申述为国之道,再进忠言。五章首二句“为谋为毖,乱况斯削”,是说谋虑周到,做事慎重,祸乱的情况就可以削减。继言“告尔忧恤,诲尔序爵”;是以老臣的口气,诫教国王:必须忧恤国事,慎于授官拜爵,选用贤能。解救国家之急难,有如解救炎热。解救炎热,要用凉水,好比解救国家危难,必须任用贤良。诗人用“谁能执热,逝不以濯”等语,谆谆告诫,陈述利害,可谓语重心长,譬喻也很确当。六章七章,从爱护人民的观点出发,表明百姓都很善良,他们勤于稼穑,以耕种养活“力民代食”的人(“力民代食”指官府役使人民劳动,取其收获养活自己)。因此官府要体恤民情,爱护人民,是为政的首要大事。六章“如彼遡风,亦孔之僾”,是说国王为政,不得人心,人民就如向着逆风,感到窒息丧气。人民虽有进取之心,但征役过重,剥夺过多,他们必然会产生难于效力之感。七章叙天降灾害,祸乱频仍,执政者只知聚敛,没有顾念人民认真救灾。由于为政昏乱,所以人民倍感痛苦。在诗中,诗人用人民的口气,警示国王,一则曰:人怨则天怒,天降丧乱,将灭我所立之王;再则曰:降此蟊贼之虫,庄稼都受到虫害而失收,天灾正是天之惩戒。下曰“哀恫中国,具赘卒荒”,则是感念人民受灾痛苦,连缀的土地,都受灾荒芜,而执政者昏乱,没有领导人民合力救灾,因而也不能感念上天减轻灾难。
诗的第八章再从用人的角度出发,言人君有顺理有不顺理,用人有当有不当。贤明的国君明于治道,顺情达理能认真考虑选用他的辅相。不顺理的君王,则与之相反自以为是,把小人当作善良,因此使得人民迷惑而致发狂。
以上八章是诗的前半,也是诗的主体,总说国家产生祸乱的原因,是由于厉王好货暴政,不恤民瘼,不能用贤,不知纳谏,以致民怨沸腾,而诗人有“谁生厉阶,至今为梗”之悲慨。
后八章责同僚之执政者,不以善道规范自己,缺乏远见,只知逢迎君王,加速了国家的危亡,更引起人民的怨恨。诗人感慨小人当权,也是厉王的过失,因而作成此诗,希望引起鉴戒。
第九章以“瞻彼中林,甡甡其鹿”两句起兴。鹿之为物,性喜群居,相亲相善。今同僚朋友,反而相谮,不能以善道相助,是不如中林之鹿。故诗人感慨“上无明君,下有恶俗”(朱熹《诗集传》)而有“进退维谷”之叹。
第十章、十一章,用对比手法,指责执政者缺乏远见,他们阿谀取容,自鸣得意,他们存有畏忌之心,能进言而不进言,反覆瞻顾,于是贤者避退,不肖者进,于是人民惨遭荼毒而造成变乱。诗人指出执政者倘为圣明之人,必能高瞻远瞩,明见百里,倘若执政者是愚人,他们目光短浅,倒行逆施,做了坏事,反而狂妄欣喜。这是祸乱之由。诗人又说:“维此良人,弗求弗迪。维彼忍心,是顾是复。”表明贤者不求名不争位,忍心之不肖者,则与之相反,多方钻营,唯名利是图;国事如斯而国王不察,亲小人,远贤人,于是百姓难忍荼毒,祸乱生矣。
第十二章、十三章以“大风有隧”起兴,先言大风之行,必有其隧;君子与小人之行也是各有其道。大风行于空谷之中,君子所行的是善道,小人不顺于理,则行于污垢之中。次言大风之行,既有其隧;贪人之行,亦必败其类。征之事实,无有或爽。盖厉王此时,用贪人荣夷公为政,荣公好专利,厉王悦之。芮良夫谏不听,反遭忌恨。故诗中有“听言则对,诵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之语。可知厉王对于阿谀奉承他的话语,就听得进,进行对答,而听到忠谏之言就不予理睬。不用善良的人,反以进献忠言的人为狂悖,国家不能不危亡。
第十四章慨叹同僚朋友,专利敛财,虐民为政,不思翻然悔改,反而对尽忠的诗人进行威吓,所以诗人再作告诫。诗人说:“嗟尔朋友,予岂不知而作,如彼飞虫,时亦弋获。”意思是说:可叹你们这些同僚,我难道不知你们的所作所为?你们对国家有极大的危害,好比那些飞鸟,有时候也会被人捕获,国家动乱危亡,你们也不会有好的下场。诗人如此警诫,可渭声情俱历。可惜此辈小人,无动于衷,所以诗人在此章的结尾,以“既之阴女,反予来赫”作结,再次警告这些人说:我已熟悉你们的底细,你们对我也无所施其威吓了。
在第十五章中,诗人继第九至十四章指责执政臣僚诸种劣迹之后,更缕陈人民之所以激成暴乱的原因,实为执政者之咎,执政者贪利敛财,推行暴政,导致民怨沸腾,民无安居之所,痛苦无处诉说,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怨恨官府,走邪僻之路。此章诗云:“民之罔极,职凉善背。”指出人民之所以失去是非准则,是因为官府执政者推行苛政违背道理。“民之回遹,职竞用力”。指出人民之所以走向邪僻,是由于官府执政者尚力而不尚德。不仅如此,诗中还指出,执政者做对人民不利的事,唯恐不得其胜(意谓极其残酷)。谴责极为严正。诗人忧国之热忱,同情人民之深切,于此可见。《诗集传》所称此人此辈,即指助厉王为虐之荣夷公等,小人当权,加速国家之危亡,诚足引为鉴诫。
末章承前,言民之所以未得安定,是由于执政者以盗寇的手段,对他们进行掠夺,所以他们也不得不为盗为寇。上为盗寇之行,民心不能安定。诗人又以“凉曰不可,覆背善詈”两句,表示:我虽忠告你们,却又不被你们接受,反而在背后诅咒我。最后归结到作诗的缘由:“虽曰匪予,既作尔歌。”意谓:尽管你们诽谤我,我还是为你们作了这首歌,以促成你们的省悟。
此诗既叹百姓之困穷,又伤国事之昏乱;既探祸乱之根,又言救乱之道;既叹生不逢时,又伤救世无力;既指斥国君之昏庸,又斥群僚不敢进言;既斥责小人乱国之行,又指斥王之不能用贤。诗中显示出一种沉郁和忧伤的情调。
从诗的语言来看,全诗语言朴直而多变化,直陈己意,不事雕饰而寄意深长。其中许多用语,至今还被引用,还具有活力。如“瘼彼昊天,宁不我矜”,此呼天之词也。“乱生不夷,靡国不泯”,此忧时之词也。“谁生厉阶,至今为梗”,此愤世之词也。“谁能执热,逝不以濯”,此善譬之词也。“人亦有言,进退维谷”,此言处世之词也。古代语词,虽至西周,尚未发展到完美的程度,所以诗中多用通假字来满足表意的需要,有些词语,甚至解说纷纭,难有确意,但根据诗的主旨,仔细思考,还是可以顺理成章,得到合情合理的解说的,因为文字本是逐步发展起来的,从诗中可以看出诗人高度的操纵文字能力。
从表现手法来看,这首长诗,运用了比喻、反诘、衬托、夸张、对比等多种手法。
此诗前两句写梅花的品格和姿态,均紧扣倒枝梅画意;后两句是画外的话,引申为感慨世事,表现了作者愤世嫉俗、追求高品位人生的思想感情。此诗的讽喻意味很浓;风格峭丽,语言警拔。
诗的起句紧扣画来写:“皓态孤芳压俗姿”,“皓态孤芳”,可能画面上是一株白梅,这白梅的姿态却与众不同,大有压倒“俗姿”之势。诗人一落笔就对画上的梅花极力赞赏。
次句点题,“不堪复写拂云枝”,画上的梅花枝条是倒垂的,不是一般画上常见的那种向上伸展的姿态,“拂云枝”,在作者眼中是一种“俗姿”,他认为这种枝条“不堪复写”。
“从来万事嫌高格,莫怪梅花着地垂”就王冕梅花图再引申发表议论。联系当时社会生活里种种不公平的现象,作者愤恨地指出,从古以来,世上庸俗的人看待万般事情总厌恶高尚的风格。这话实际上从时间之久,到事情包罗之广,同情具有高尚风格的人,而对厌恶甚至迫害具有高尚风格的人恶劣世俗加以抨击。正因为世俗不公,所以最后又回到王冕的画上来,不能责怪王冕把梅花的枝头画成下垂到地面了。
在一般作品里,梅花傲然向上,不屈服于寒冷、冰雪之威;而“倒枝梅”在形态上正好相反,不论有否冰雪,王元章画的梅花没有“拂云”的伟岸,而是“着地垂”,这似乎意味着画家已心灰意颓,甚至失去了对“高洁”的向往,徐渭默认并且深深地感喟这种“倒枝梅”的姿态,似乎也已不复“脱俗”“超然” 的追求,但正在此,无论画家还是诗人,其匠心其实已跃然纸上,别出一格的曲折命意,写尽了他们不堪现实重压的窘迫与艰难;同时,即便世俗的肆虐可以让梅花垂地,亦无改其皓然的姿态、孤独的芳香、高迈的风格,作者对理想的执着信念、对世俗的鄙弃、厌恶,因此而更多一分真诚。
这首小诗虽只四句,但结构极为谨严。七言绝句四句中要求有起承转合,诗以赞梅起笔,次句承首句落实到所题的倒枝梅画上,三句转为慨叹世事,四句仍关合在倒枝梅画上,章法宛然。此诗以意胜,重议论而不重描摹。此诗则遗貌取神,可谓别具一格。
元宵佳节是历代词人经常吟咏的话题。不论是北宋,还是南宋,在所有的节日中,以元宵最为热闹,也以元宵最为人所重。而在国破家亡之时,这个节日又最容易引起人们对往昔繁盛的追忆,最易牵动人们的故国之思。
全词起笔“蕙花香也。雪睛池馆如画”,即沉入了对过去元夕的美好回忆:兰蕙花香,雪霁天晴,亭台楼阁之中池波荡漾,街市楼馆林立,宛若画图,尽是一派迷人景象。极度地渲染了元宵节日氛围。“春风飞到,宝钗楼上,一片笙箫,琉璃光射。”春风和煦,酒旗飘拂,笙箫齐奏,仙乐风飘。据载,宫中曾做五丈多高的琉璃灯,又地方进贡之灯“或以五色琉璃而成”。那令人陶醉的音乐,那壮观的灯市,使词人忆起如昨天一般。
“而今灯漫挂。不是暗尘明月,那时元夜。”“而今”二字是过渡,上写昔日情景,下写当日元夕景况。“灯漫挂”,指草草地挂着几盏灯,与“琉璃光射”形成鲜明的对照。“不是暗尘明月,那时元夜。”既写此夕的萧索,又带出昔日的繁华。“暗尘明月”用唐苏味道《上元》“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诗意。以上是从节日活动方面作今昔对比。“况年来、心懒意怯,羞与蛾儿争耍。”今昔不同心情的对比。蛾儿,即闹蛾儿,用纸剪成的玩具。写当日的元宵已令人兴味索然,心境之灰懒,更怕出去观灯了。这种暗淡的心情是近些年来才有的,是处境使然。
下阕“江城人悄初更打”,从灯市时间的短促写今宵的冷落,并点明词人度元宵所在地——江城。下面数句直至词末,一连用了“问”、“但”、“待把”、“笑”等几个领字,一气直下,写出了自己内心的悲恨酸楚。“问繁华谁解,再向天公借”,用倒装句法,提出有谁能再向天公借来繁华呢?“剔残红灺。但梦里隐隐,钿车罗帕。”怀着无可奈何的心情,词人剔除烛台上烧残的灰烬入睡了。梦中那辚辚滚动的钿车、佩戴香罗手帕的如云士女,隐隐出现。
“吴笺银粉砑。待把旧家风景,写成闲话。”以最精美的吴地的银粉纸,把“旧家风景”写成文字,以寄托自己的拳拳故国之思。银粉砑,碾压上银粉的纸。旧家风景,借指宋朝盛事。听到邻家的少女还在倚窗唱着南宋的元夕词。现在居然有人能唱这首词,而这歌词描绘的繁华景象和“琉璃光射”、“暗尘明月”正相一致。心之所触,心头不禁为之一动,略微感到一丝欣慰,故而以一“笑”字领起。但这“笑”中实在含有无限酸楚。,因为“繁华”毕竟是一去不返了。
这首词风格较为自然,词意始终在流动中,无一凝滞。但是在顿挫中显流动,于追琢中出自然。对过去元夕的铺叙作者不惜篇幅,不惜浓墨重彩,或直接描绘,或间接叙写,或通过梦境加以再现,着力处皆词人所钟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