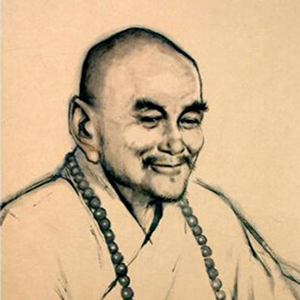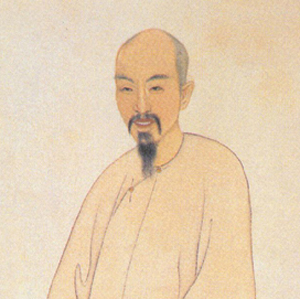“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提挈全篇,“万方多难”,是全诗写景抒情的出发点。在这样一个万方多难的时候,流离他乡的诗人愁思满腹,登上此楼,虽然繁花触目,诗人却为国家的灾难重重而忧愁,伤感,更加黯然心伤。花伤客心,以乐景写哀情,和“感时花溅泪”(《春望》)一样,同是反衬手法。在行文上,先写诗人见花伤心的反常现象,再说是由于万方多难的缘故,因果倒装,起势突兀;“登临”二字,则以高屋建瓴之势,领起下面的种种观感。
“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诗人从登楼看见的景色开始写起,描绘了一幅壮美的山河景观。锦江水夹带着朝气盎然的春色从天地间奔腾而来,玉垒山上的浮云飘忽不定,这使诗人联想到了动荡不安的国家,那浮云飘移就像是古今世势的更替变幻。上句从空间上扩展,下句从时间上蔓延,这样延展开来,顿然形成了一片宏阔悠远的意境,包括诗人对国家山河的热爱和民族历史的回忆。并且,登高望远,视野开阔,而诗人偏偏向西北方向望去,可见,诗人心怀国家,此时,他忧国忧民的高大形象跃然纸上。
“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主要写国家战事。诗人登楼远眺,由浮云想到了国家现时情况,虽然大唐朝廷风雨动荡,但代宗又回到了长安,可见“终不改”,这照应了上一句的“变古今”,语气中流露了诗人强烈的爱国之情。下句“寇盗”“相侵”,进一步说明第二句的“万方多难”,针对吐蕃的觊觎寄语相告:“莫再徒劳无益地前来侵扰!”词严义正,浩气凛然,在如焚的焦虑之中透着坚定的信念。
“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甫吟》。”后主,指蜀汉刘禅,宠信宦官,终于亡国;先主庙在成都锦官门外,西有武侯祠,东有后主祠;《梁甫吟》是诸葛亮遇刘备前喜欢诵读的乐府诗篇,用来比喻这首《登楼》,含有对诸葛武侯的仰慕之意。诗人伫立楼头,徘徊沉吟,很快日已西落,在苍茫的暮色中,城南先主庙、后主祠依稀可见。想到后主刘禅,诗人不禁喟然而叹:“可怜那亡国昏君,竟也配和诸葛武侯一样,专居祠庙,歆享后人香火!”这是以刘禅比喻唐代宗李豫。李豫重用宦官程元振、鱼朝恩,造成国事维艰、吐蕃入侵的局面,同刘禅信任黄皓而亡国极其相似。而诗人自己,空怀济世之心,苦无献身之路,万里他乡,高楼落日,忧虑满怀,却只能靠吟诗来聊以自遣。
全诗寄景抒情,将国家的动荡、自己的感怀和眼前之景融合在了一起,相互渗透,用字凝练,对仗工整,语势雄壮,意境宏阔深远,充分体现了诗人沉郁顿挫的诗风。
这首七律,格律严谨。中间两联,对仗工稳,颈联为流水对,有一种飞动流走的快感。在语言上,特别工于各句(末句例外)第五字的锤炼。首句的“伤”,为全诗点染一种悲怆气氛,而且突如其来,造成强烈的悬念。次句的“此”,兼有“此时”、“此地”、“此人”、“此行”等多重含义,也包含着“只能如此而已”的感慨。三句的“来”,烘托锦江春色逐人、气势浩大,令人有荡胸扑面的感受。四句的“变”,浮云如白云变苍狗,世事如沧海变桑田,一字双关,引发读者作联翩无穷的想象。五句的“终”,是“终于”,是“始终”,也是“终久”;有庆幸,有祝愿,也有信心,从而使六句的“莫”字充满令寇盗闻而却步的威力。七句的“还”,是“不当如此而居然如此”的语气,表示对古今误国昏君的极大轻蔑。只有末句,炼字的重点放在第三字上,“聊”是“不甘如此却只能如此”的意思,抒写诗人无可奈何的伤感,与第二句的“此”字遥相呼应。
尤其值得读者注意的是,首句的“近”字和末句的“暮”字在诗的构思方面起着突出的作用。全诗写登楼观感,俯仰瞻眺,山川古迹,都是从空间着眼;“日暮”,点明诗人徜徉时间已久。这样就兼顾了空间和时间,增强了意境的立体感。单就空间而论,无论西北的锦江、玉垒,或者城南的后主祠庙,都是远处的景物;开端的“花近高楼”却近在咫尺之间。远景近景互相配合,便使诗的境界阔大雄浑而无豁落空洞的遗憾。
历代诗家对于此诗评价极高。清人浦起龙评论说:“声宏势阔,自然杰作。”(《读杜心解》卷四)沈德潜更为推崇说:“气象雄伟,笼盖宇宙,此杜诗之最上者。”(《唐诗别裁》卷十三)
王廷相主要作为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哲学家著称于世。但是,他的《与郭价大学士论诗书》,乃是明代诗文批评中如同晨星一现的审美意象的专论。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夫诗贵意象透莹,不喜事实粘著,古谓水中之月,镜中之影,可以目睹,难以实求是也……言征实则寡余味,情直致而难动物也。故示以意象,使人思而明之,感而契之,邈哉深矣!此诗之大致也。”将化“直”为“曲”,虚实相同,透莹圆融,远神余味等,视为审美意象的重要特征,可谓觉得诗家三昧。然而,他的诗歌创作与他的意象理论相互矛盾,如钱谦益指出:“子衡五七言研讨,才情可观,而摹拟失真,与其论诗颇相反。今体诗殊无解会,七言尤为策浊,于以骖乘何(景明)、李(梦阳)、为之后劲,斯无愧矣。”(《列朝诗集小传》丙集《王宫保廷相》)钱氏的批评,未免过分苛刻。其实,王廷相的诗歌中,即使在被人称为多粗漫之作的七言古诗中,也可以披沙见金,间有意象和谐的篇章。令人有:“如游五都市中,动获奇宝”(陈田《明诗纪事》丁签卷三)之感。尤其是他的五言绝句颇有摩诘(王维)风致,下亦不失为裴十秀才(裴迪),崔五员外(崔宗之)(朱彝尊《明诗综》卷三十一引宋辕文语。)《古陵》就是其中颇有特色的一首。
《古陵》诗中的抒情主人公是那位独自惆怅的“行客”。行富的抒情并非是直说,而是以古今交错,虚实相间的手法曲曲道出。前两句以“蒿”为中心视点,上下流动,俯视古陵,仰视啼乌,这就构成了两个意象:蒿下之古陵,蒿上之啼乌。且说中心视点中“蒿”。蒿,野草。古代歌辞中言人死魂魄归于蒿里。“蒿”同于“槁”,人死则枯槁,所以说死人的居里名蒿里。相传齐国东部(今山东东部)流传《薤露》、《蒿里》谣讴。两曲都是挽歌,为出殡时挽柩人所唱。汉代以《薤露曲》送王公贵族出殡,以《蒿里行》送士大夫、平民出殡。显然,王廷相的“蒿下之古陵”中融入了《蒿里行》中某些传统的意象,哀悼的对象是“蒿下古陵”中的士大夫和平民。因为古陵深埋在蒿里,可望可不可即,所以诗人只以“古陵在蒿下”作粗线条的勾勒。如果说“古陵在蒿下”是俯视,是视觉形象,那么,“啼乌在蒿上”则是仰视,是视觉形象与听觉形象兼而有之。由“啼乌”,很自然地使人联想起唐代诗人张继《枫桥夜泊》中的名句:“月落乌啼霜满天”,在所见(月落、霜满天),所闻(乌啼)中呈现出一片幽寂清冷的景象。由“乌啼”,又很自然地使人联想到李白《乌夜啼》中的诗句:“黄云破边乌欲栖,归飞哑哑枝上啼。”感物应心,由乌鸦回巢引发起行客思归的愁绪。
然而,诗中没有由“啼乌欲栖”直接引出行客思归,而是突然插入一句“陵中人不闻”,由古陵之中的人(实际上指魂魄)“不闻”,反弹出行客闻声而动情。“不闻”,固然是由于“陵中人”丧失了“闻”的功能,也是诗人故作旷达之语,是用欲扬先抑的手法反衬出体察人生、饱尝辛酸的“行富”感物应心的敏感。对于诗人王廷想来说,“啼乌”不再是简单的物象,而是融注着威信人生之感的丰富的意象。所以,他闻乌啼之声而惊心动魄,而独自惆怅。而行客独自惆怅,固然有思归愁绪的侵袭,又融注了《古诗十九首·青青陵上柏》中的某些意蕴:“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感叹人生短促,犹如远行作客,匆匆走过。作者怀古伤今,感叹人生,凄婉之情油然而生。此种引发,往往可以举一反三。
这首五言绝句以“行客自惆怅”作结,言已尽而意无穷。由此可见,这首诗故作旷达而情倍凄婉,纯用白描而虚实相间,短小精悍而跌宕起伏,意象透莹而远神余味 ,是王廷想将自己的有关意象理论付诸创作实践的一次成功的尝试。
这是一首怀旧之作。本词追忆早年初见美人时的喜悦与欢欣及今日物是人非的惆怅,在对比中抒发好景不长的人生感慨。词中以往昔“歌韵琤琮”、“舞腰乱旋” 的欢乐场面与今日“点检无一半”的凄清境况对比,抒发了强烈的人生无常的伤感之情。词中所写景物:池塘、绿水、阑干、香阶,均兼关昔今。物是人非,更兼日斜时暮,遂使词人汕然而生故交零落、人生如梦之感。全词以极优美的文辞来流露出词人关于宇宙无穷,人生短暂,景物依然,物是人非的凄然感慨。
最折磨人的感觉,不是痛苦,而是惆怅的情绪;最令人伤感的,不是生离死别,而是景色依然,人已天涯云杳。“当时共我赏花人,点检如今无一半”——古典的诗意世界,已经远离现实的生活。只希望那些梦里飘飞的花瓣,洋洋洒洒地永远飘落在我的精神世界里。沉湎在回忆中,感觉人生是孤独的,人生其实就是一场寂寞的旅行,没有人可以陪你走到最后。所有的痛苦和美好,都终将随着岁月慢慢远去。云聚云散,潮起潮落。再回首,往事却已随风而去,了无痕迹,最后,还剩下些许淡淡的忧伤和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