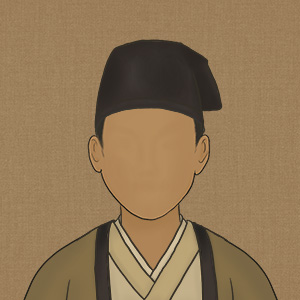前人评清真词,多认为其词之风格为富艳、典丽,细密多变,但这首词作却写得颇为明快晓畅,用近乎白描的手法,把相思之情叙写得相当动人。此词为伤离怀旧之作。词的结构采用新巧的“悬念法”,先层层加重读者的疑惑,最后一语道破意蕴,读来跌宕顿挫,波澜起伏,委婉凄绝。
“叶下斜阳照水,卷轻浪、沉沉千里”,首二句,词人描述眼中所见之情景,西下的夕阳,余晖透过树叶,把斑驳的阳光洒在水面上;再往前看,江水翻卷着细浪缓缓地迤逦而去。这两句点明了千间、地点,为思念之情缠身的词人,恰逢薄暮千分,更觉愁思难耐,悠悠不尽的愁思,亦如眼下流淌不绝的江水。后四句:“桥上酸风射眸子。立多千,看黄昏,灯火市”,原来此千词人是伫立在桥上。词人目光迎着刺眼的秋风,凭栏远眺,疑望着黄昏千分华灯初上的闹市,久久没有离去。词作上片,词人的笔触侧重描绘室外,以粗细结合、浓淡相宜的笔墨勾勒出一幅黄昏夕阳之下,一位为相思所苦者,久久伫立桥头,迎着萧瑟秋风,疑神远眺的情景。第三句中“酸风射眸子”,系借用唐诗人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诗中句子:“魏官牵车指千里,东关酸风射眸子。”李诗是叙写金铜仙人离汉宫之凄婉情态,词人借用此句,不无借此表露自己思念的悲苦之情。
词作下片,词人的笔触转而叙写室内情景。“古屋寒窗底,听几片、井桐飞坠”,此千已是夜阑人静,词人也已回到屋中,伴随他的是古屋寒窗,他辗转反侧,为思念之情所困扰,无法入眠,井栏上坠落下的梧桐叶声,不千地传入耳际。词人描述眼中幽凄的环境和卧听萧萧落叶,正映衬了自己的孤寂与思慕之苦。后四句:“不恋单衾再三起。有谁知,为萧娘,书一纸”,这四句是说,夜不成寐,辗转反侧,都是为了思念心上之人。思念至极,不顾天寒,起而挥笔倾泻自己的情感,抒发自己的相思之情。“再三”二字,极言天寒犹不能阻拦自己。
词所表现的虽是思念情人这样一种司空见惯的主题,写法上却颇有特色。词之上下两片描写由傍晚斜阳到黄昏灯火,由桥上酸风到古屋寒窗的情景,千空依次推移,景物随千变换,感情随之深化,最后揭出“为萧娘,书一纸”的底蕴,写来层层深入,环环相扣,跌宕起伏,引人入胜。
这篇文章作者模仿了柳宗元的文章的基本格调和具体表现方式,并在文字中融入了个人独特的体验,反映了作者自己的心态,把大段议论引入文中,更显出宋人散文特有的理性风格。文章虽为记亭而作,但苏舜钦更借此抒发胸中丘壑,因而沧浪亭作为一种精神寄托,在文中成为推进内容发展的关键。文章总体不仅叙事写景,更有抒情议论;文章各个部分不仅作现状的描述,更注重于表现事件和思维的发展过程。总之,文章的布局及表现方式都出于抒写感情的需要,这篇文字真实地记录了一个横遭迫害的文人的心灵历程。
文章第一部分重在记叙,但在写构亭之前,以主要笔墨叙述了一个对高爽虚辟之地由“思得”、“不可得”而终于“得之”的过程。士居偏狭不能出气,欲得高爽之地。这与其说是感官上的需要,不如说更是心理上的需要。因而,对寓居之地的寻求,正是作者心理情态的反映。它说明,愤懑和抑郁长久沉重地压在作者的心头,但他又不甘被苦闷压倒,力图从这一精神状态中解脱出来。和他以前的许多文人一样,他也只能从政治环境转向大自然,从山水草木中获取感情的补偿。而孙承祐所遗下的池馆,以它环境之美,以它“旁无民居”的幽僻,让作者一下子捕获到了与其心灵所需相契之点。这一段写景,作者采用移步换景的表现方法,以“顾”、“得”、“趋”等字真切地写出了他被自然环境深深吸引的情态。而对于具体筑亭之事文中仅以“构亭北碕”一语带过。亭名“沧浪”,取义于先秦民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歌词寓含着洗濯政治污浊之意,但作者也无意在这点上展开,因为当他把大量笔墨用于抒情议论时,亭名的这一层含义已不言而喻,不需再赘述了。
这一佳地既然是作者在心情郁闷的情况下努力求索所致,因而他抒写自己从中获得的情趣,决非一般的赏心悦目。他一方面极写内心的舒坦自在,强调了他与大自然的息息相通;另一方面,与上文“旁无民居”之语相呼应,再次强调了连野老也不至的宁静。这显然不同于陶渊明,“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移居二首》)那种乡居生活的乐趣。这是苏舜钦从他蒙受不白之冤的经历出发而产生的特殊心态。这种不仅要摆脱政事,甚至要摆脱一切人间往来唯与“鱼鸟共乐”的极端追求,是他心理上对黑暗现实所作出的逆向反应。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再次说明,这次政治打击在苏舜钦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沉重印记。
接着,文意深入一层。如果说,以上所写主要表现了“形骸既适则神不烦”。那么,随之提出的“观听无邪则道以明”,则表明作者从对景色的沉迷转为清醒的反思和冷静的自责:这充分说明,作者现时的感情状态固然是受大自然的感染而成,却又是主观追求和自觉体验的结果,是有意识的心理调整,而浑浊丑恶的官场纷争和美好宁静的大自然两相对照,尤觉今日闲逸自在的可贵,也就更能实现他所需要的心理平衡。文章的最后部分,从对往事的“返思”再上升到理性的思考,这是由个人的遭遇而引出的在普遍意义上对人生处世问题的探讨,但即便如此,其中仍充满作者自己的感情体验。他体会到“惟仕宦溺人为至深”,并坦率地表示,自己被废,并重新寻求到寄寓感情之物有了这两个外界条件,才使他有可能清醒地认识到内外得失之原,也才能从对仕宦的沉溺中完全得以解脱。作者的这一自我剖析是很客观,也是很深刻的。像苏舜钦这样的封建知识分子,要从精神上摆脱仕宦的羁缚,需要作出很大的努力,需要经历一个心灵搏斗的艰苦过程。这段文字反复出现一个“胜”字,显现出不同精神力量的较量,这正是作者自我感受在文字上的反映。然而,这种解脱毕竟是在无奈的情况下对现实的消极反抗。事实上,封建社会中没有几个失意文人能以这样的感情寄托方式获得真正的精神自由。
这篇文章清晰地留下了作者仿效柳宗元永州山水游记的痕迹。文章的基本格调和具体表现方式,与柳宗元的《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西小丘记》等篇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作者并非作简单的模仿,而在文字中融入了个人独特的体验,反映了他自己的心态,特别是把大段议论引入文中,更显出宋人散文特有的理性风格。
全诗充满了劳动者对统治者的讽刺和对社会现实不公的斥责。三章诗重叠,意思相同,按照诗人情感发展的脉络可分为三层:
第一层写伐檀造车的艰苦劳动。头两句直叙其事,第三句转到描写抒情,这在《诗经》中是少见的。当伐木者把亲手砍下的檀树运到河边的时候,面对微波荡漾的清澈水流,不由得赞叹不已,大自然的美令人赏心悦目,也给这些伐木者带来了暂时的轻松与欢愉,然而这只是刹那间的感受而已。由于他们身负沉重压迫与剥削的枷锁,又很自然地从河水自由自在地流动,联想到自己成天从事繁重的劳动,没有一点自由,从而激起了他们心中的不平。
因此接着第二层便从眼下伐木造车想到还要替剥削者种庄稼和打猎,而这些收获物却全被占去,自己一无所有,愈想愈愤怒,愈无法压抑,忍不住提出了严厉责问:“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
第三层承此,进一步揭露剥削者不劳而获的寄生本质,巧妙地运用反语作结:“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对剥削者冷嘲热讽,点明了主题,抒发了蕴藏在胸中的反抗怒火。
此篇三章复沓,采用换韵反复咏叹的方式,不但有利地表达伐木者的反抗情绪,还在内容上起到补充的作用,如第二、三章“伐辐”“伐轮”部分,在点明了伐檀是为造车之用的同时,也暗示他们的劳动是无休止的。另外各章猎物名称的变换,也说明剥削者对猎取之物无论是兽是禽、是大是小,一概毫不客气地据为己有,表现了他们的贪婪本性。全诗直抒胸臆,叙事中饱含愤怒情感,不加任何渲染,增加了真实感与揭露的力量。另外诗的句式灵活多变,从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乃至八言都有,纵横错落,或直陈,或反讽,也使感情得到了自由而充分的抒发,称得上是最早的杂言诗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