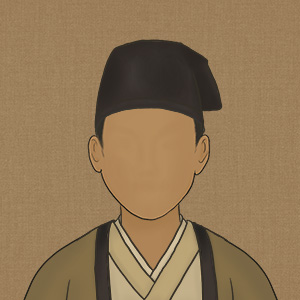此词上片写对友人别墅的赞美,其向往之情毫无掩饰。下片写世间的功名利禄之事不过过眼云烟,表达出对官场斗争、人海沉浮的厌倦。全词借景抒情,看似套语,却露真情。
上片写词人平日身在繁华都市之中,见惯了车水马龙,如今来到友人幽屑的山间,实在心生羡慕。对友人的别墅毫无掩饰地赞美,到处都是车马如龙,羡慕友人能寻到一个如此清幽的住处。在这里,眼见的是满山柿叶殷红,听闻的是四面萧萧清风,多么美丽。但是,容若出身钟鸣鼎食之家,享尽荣华,什么优美的住所他未曾见过,何需对友人的别墅艳羡不已。
下片说世间的功名利禄之事,只不过是镜中之月、河中之影而已。看镜中自己的容颜渐老,越发感慨功业无成。结尾两句“安得此山间,与君高卧闲”则直接地表达了纳兰也渴望归隐山林的愿望:真想和友人一道隐居在此,以明月和银河为伴,何等逍遥自在。至此,终于明白容若的真意,对见阳山庄的向往是假,对官场斗争、人海沉浮的厌倦才是真。容若真正想对友人说的,乃是结伴从红尘喧嚣中逃走吧,躲开这肮脏的一切。
小词有景有情,借景抒情,看似套语,却露真情。纳兰性德虽身在高门广厦,内心深处“其于世味也甚淡,直视勋名如糟粕,势利如尘埃”。一位承平时代的贵公子,能够作如此之想,古今难得。
这是一首写周宣王忧旱祈雨的诗。是所谓“宣王变《大雅》”的第一篇(其他五篇是《大雅·崧高》、《大雅·烝民》、《大雅·韩奕》、《大雅·江汉》和《大雅·常武》)。
全诗八章,每章十句。一、二两章写祭神祈雨。正是需雨的时节,然而日日骄阳似火,禾稼死亡,田地龟裂,人畜缺水。这当儿,人们是多么盼望老天降落一场甘霖啊!可是仰望苍穹。毫无雨征(古人常夜间观天象以察云雨)。“倬彼云汉,昭回于天”,星河灿烂,晴空万里,夕夕如此。内心焦灼的诗人于是发出了“何辜今之人!天降丧乱,饥馑荐何”的慨叹。无神不祭。无牲不用,礼神的玉器也用尽了,然而神灵们却不闻不问,毫无佑助之意。这苍天啊,好像真的是把降雨的事儿抛在脑后,彻底忘掉了;或许人们得罪了他,他在有意地惩罚人们。三、四两章写大旱的不可解除,主要表达了畏旱之情。“旱既大甚,则不可推”,“旱既大甚,则不可沮”,凶暴狂猛的旱灾如洪水猛兽,无法推开,无法阻拦,使“周余黎民,靡有孑遗”,造成了无法收拾的严重局面。再继续下去,将国祚难永。然而“群公先正,则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宁忍予!”意谓:群公先正,我常雩祭以祈谷实,现在却不助我以兴云雨;至于父母先祖,尤一体之所亲,一气之所感,为什么也忍心看我遭此祸而不救呢?五章写旱魃继续肆虐。山原秃而河湖干,这里已经变成了一块让人无法生存下去的土地。“昊天上帝,宁俾我逐”,老天似乎是要迫使人们离开此地,他是不想让人安居了。六章述失望痛苦之余的反思。也不是祭神不及,也不是对众神不恭敬,细细思量,确实没有什么罪愆,那又为何降灾加害呢?七章叙君臣上下因忧旱而困窘憔悴。末章周王著力鞭策,希望臣子们“无弃尔成”,继续祈祷上苍。最后仰天长号,以亟求天赐安宁作结。
统观全诗,作者对这次持久难弭的灾祸从旱象、旱情、造成的惨重损失及所引起的心理恐慌等方面作了充分的描写。这场大旱就是死亡之神的降临,可以摧毁一切,消灭人类。在那个生产力水平还很低的时代,它会造成怎样的人间灾难,是不难想像的。这首诗在写宣王忧旱的同时,也写了他的事天之敬及事神之诚。在人们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还极其有限的西周末期,面对无法战胜的灾害,对虚无飘渺的天帝和神灵产生敬畏乞求心理,也是不难理解的。今人自然不能以现代科学主义的观念和标准来苛责古人。
这首诗兼叙事抒情于一体,在艺术上值得称道的有两点:一是摹景生动;二是夸饰手法的运用。“倬彼云汉,昭回于天”,夜晴则天河明,此方旱之象。“昭回于天”又暗示出仰望之久。久旱而望甘霖者,己所渴望见者无,己所不愿见者现,其心情的痛苦无奈可想而知。毫无雨征,还得继续受此大旱之苦,于是又顺理成章地推出“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丧乱,饥馑荐何”四句。所以开篇这摹景之句不仅写出了方旱之象,同时也表达了诗人的心情,并生发出下文,是独具匠心、富有艺术魅力的诗句,因而孙鑛称赞这首诗的起首“最有风味”(陈子展《诗经直解》引)。“旱既大甚,涤涤山川。旱魃为虐,如惔如焚。”这场大旱使周地变成了不毛之地,无水之区。山空川涸,禾焦草枯,畜毙人死,大地就像用火烧燎过一样,没一点生气,没一点活力。“涤涤山川”、“如惔如焚”可谓写尽旱魔肆虐之情状,同时也传达出诗人面对这种毁灭性灾害的痛苦、焦灼之情。王夫之《姜斋诗话》云:“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情中景,景中情。”这几句诗虽然称不上“妙合无垠”,但做到景中含情、景中寓情却是很明显的。
诗中“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二句早在战国时代就被孟子认为是夸饰之辞的典范,备受后世批评家的关注。这两句是用夸张的艺术手法,以突出遭旱损失的惨重。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指出夸张的修辞虽然言过其实,但因为能通过形象的夸张来传难写之意、达难显之情,所以在文学作品中有它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确实,“靡有孑遗”四字,所述虽非事实,但却突出了旱情的严重,是反映真实,并且凸现了真实的传神之笔。
这是一首秋夜不眠夜行的小词。
起句“不寐倦长更”中“不寐”二字异常醒目,耐人寻床,是全词的根。“倦”字借“不寐”自然生发出来,揭示出因无眠而生倦怠的逻辑关系,可以想见词人心绪的烦闷了。第二句又从时序上因承上句,貌似平谈,却是承上启下不可或缺的过渡。第三、四两句,笔锋一顿,停留在出门所见所感上面。“月寒”句在点明季节之余,更以“寒”、“冷”二字借物传心,将心中抑郁愁闷之情隐隐带出,是这首词重心所在。最后一句着笔于月寒竹冷,被疾风拍打的窗户在深夜回想,以景结情,自然收束,是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妙笔。
此词是典型的即景即情之作。全诗尽透作者的愁苦之情,夜不能寐更添几番寂寥之意,风呼啸体现了作者的一路坎坷,寒月凄凄,心中的苦闷只有随秋竹落落归寂罢了。
《驹支不屈于晋》在晋与诸侯“会于向”这一历史事件中,只不过是一段小插曲,然而它却有不同寻常的认识价值。这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上一段耐人寻味的故事。它不仅看到了当时少数民族在霸权制度下所受压迫的深重,也从驹支与范宣子的冲突与和解中看到了古代各民族既斗争又融合的复杂关系的缩影。通过个性化的语言表现人物性格是《驹支不屈于晋》的一大特点。
文章开头范宣子一上来就是:“来,姜戎氏!”像怒气冲冲的主人呼唤惹了祸的奴隶,凶神恶煞,怒目而视,语气咄咄逼人,态度粗鲁生硬。接着居高临下,夸示晋先君对诸戎的大德大恩,而后毫无根据地把“今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子者”的罪责一股脑推给驹支。“盖言语漏泄”,分明是推测、怀疑,“职女之由”,则是武断定罪,“与,将执女!”恐吓之声,令人不寒而栗!范宣子颐指气使、不可一世的神态纤毫毕见。
驹支面对气势汹汹的指斥,面对即将遭受拘捕的厄运,则临危不惧,据理力争。针对范宣子强加于己的不实之词,逐层辩驳,洗刷被泼在身上的污水,维护自己和部落的清白。从答话可以看出,驹支虽为戎族首领,但其语言艺术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他的语言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把握分寸,恰到好处。他对范宣子的无端指责,既针锋相对又没有过激言辞,既不掩惠公之德,也不蒙不白之冤。
其次是逻辑严密,形象生动。先感惠公之德,再表戎对晋之功,以事实为据,证明自己对晋“不侵不叛”,忠心“不贰”。最后以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的事实驳斥范宣子强加的罪名,环环相扣,天衣无缝。尤其是关于“捕鹿”的比喻,极为确切生动,且符合人物的身份。
最后是赋诗言志,颇具策略。《青蝇》所赋:“恺悌君子,无信谗言”,驹支将范宣子恶意相加的罪名解释为“听信谗言”,给了范宣子一个下台的台阶,把范宣子说成“恺悌君子”,也让这位盛气凌人的大人物感觉舒服。其实驹支似乎设了一个看不见的圈套:是“恺悌君子”就不要听信谗言,否则就不是“恺悌君子”。春秋时代,诸侯外交,讲究赋诗言志。范宣子没有赋诗言志,反不如驹支,说明驹支胜过范宣子,夷狄胜过华夏。这一点,恐怕不是《左传》作者的初衷吧。
《左传》除了对各国战争描述精彩之外,对一些谋臣说客的辞令艺术的记录,也极具艺术性,尤其是那些谋臣们在外交中实话实话,以真取胜的史实,令人叹为观止。《驹支不屈于晋》就是戎子驹支以事实说话,驳倒范宣子的责难的事:范宣子仗着晋国的强大,仗着自己的先君曾有恩于羌戎,对驹支气势汹汹,把晋国霸主地位的动摇归咎于驹支。戎子驹支则据理力争,逐层辩驳。首先说晋国所赏赐的土地是荒芜不毛之地,不足以称大恩大德。其次说羌戎帮助晋国在肴地全歼秦军,可以说已经报恩了,之后更是鞍前马后,毫无二心。最后暗示晋国所以众叛亲离,乃是其自己一手造成的,与羌戎无关。全部辩辞语气委婉而正气凛然,使范宣子不得不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