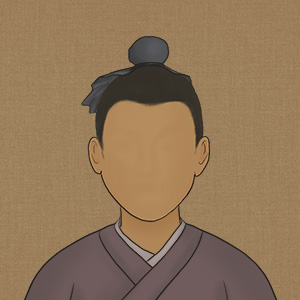此诗语言清浅,讽旨颇深。诗人仅仅抓住富室女子首饰之华美珍贵这样一个典型事物进行渲染,深刻地揭露出贵戚显宦、地主富室生活的奢靡浮华。
不仅如此,含蓄也当是此诗的一个艺术特色。诗写一个富室女子的两片云髻就花费了“数乡”农民所缴纳的赋税,这就说明,她们所挥霍的并非他物,而是广大农民的血汗钱,从而以诗的语言形象地揭示了封建社会赋税的剥削本质,对农民的苦难寄寓了深刻的同情。
韩偓的七言律诗《三月》主要表达了诗人对时光易逝,盛景不再的感慨,其中也寄寓了诗人壮志难酬的无奈。这与诗人所处的时代不无关系。晚唐早已没有了盛唐的雄壮和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剩下的仅有颓废和衰弱,作为始终坚持反对朱全忠篡唐的有气节的士人,身处这种时代,面对危乱的时局,却只能无奈叹息,这首《三月》正是诗人无奈的哀叹,一方面是借哀叹美好的初春三月来哀叹国势颓危的晚唐王朝,另一方面也在为自己盛年易逝,无可挽留,功业未就的现实感慨万分,诗的结尾 “新愁旧恨真无奈,须就邻家瓮底眠”万般无奈的心情表露纸上,借酒消愁却愁更愁。
辛夷花是一月开花的,它才刚刚谢了,桃花却早早的开了。笫一句就说明写诗时是早春时节,这样的时节是充满生气的,绿地草涨莺飞,万物渐欣渐荣。在这样的日子出去踏青是再好不过的了,在南方,寒食时节,总是细雨飘飘,滋润着千树力‘花,也带给人清新舒服的感觉。第一句的前半句“四时最好是三月”,正好说明“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就好比一个人的少年时期,一个精力充沛、活力无限的时期,然而少年也像春天的三月那样,晃一晃就过去了。时间总是这样,在你的指缝隙间流失,而你却全然不知。韩偓在这里就借用短暂的三月来感叹少年时期的一去不复返,让人不禁的感伤了起来。“吴国地遥江接海”,吴国即吴地,是长江及其支流哺乳的地域,长江经过吴地最后流入浩翰的东海,故诗人说“江接海”。汉陵是汉朝天子陵墓,“汉陵魂断草连天”,汉朝天子建立的辉煌大业早已成为历史,今也只剩陵墓断碑伴着杂草丛生。“新愁旧恨真无奈”,新增添的忧烦苦闷和旧有的遗憾悔恨,让诗人也无可奈何,如今的他除了借酒醉酣睡在瓮底,还以做什么来扭转故国火亡的乾坤呢?
整首诗由春天短暂的三月写到人生的少年,又寄寓着家国灭亡的哀痛。春天的三月快的让人无奈,少年的大好光阴逝去让人无奈,国家变迁更让人无奈。这首诗倾注着诗人对国家的眷恋,环境的变化往往会让诗人的诗作风格有着质的改变,和李煜一样,社会动荡、王室颠覆给予韩偓诗歌创作以重大影响。他的诗常有以不写而写来传达窈妙之情,一句“一去不回唯少年”,无伤而让人感伤;一句“新愁旧恨真无奈”,不明言其愁,而愁巳不言而喻。
卢僎这一首有名的五排,其妙处在于,诗人以雄劲的笔触,描写主人十月咏梅的艺术概括。他通过对于时间和空间的意匠经营,以及把写景、叙事、抒情与议论紧密结合,在诗里熔铸了丰富复杂的思想感情,使诗的意境雄浑深远,既激动人心,又耐人寻味。
诗的起始两句:“花寒懒发鸟慵啼,信马闲行到日西。”写冬去春来,但仍春寒料峭,那种百花争艳、莺声燕语的春日繁华景象还远未出现。看不到一点可以驻足观赏的春天景象,诗人也只好在长堤上信马闲行,颇为无奈地消磨时光。但春天
《魏王堤》诗意图 不可能没有一点踪影,细心而敏感的诗人突然发现了春已到来的迹象,那就是长堤两旁的弱柳,已嫩枝轻拂,给人间带来了一丝春意。
从全篇诗意来看,这首小诗可以说是一首寻春、觅春诗;在春天来临之前,诗人已动春思,来到魏王堤觅春、寻春。这时虽仍然寒锁大地,不见花影,未闻鸟声,但从已变得柔嫩的柳枝上,看到了春的踪影。诗中用“懒发”、“慵啼”来形容花、鸟,以“无力”描写柳条,都给人一种娇不胜寒的感觉,但春既已萌动,毕竟是锁不住的,“何处未春先有思?”“先有思”,就是说,春天已在不易察觉中迈出了她的脚步,一个姹紫千红的繁华春日,就要来临了。凭着诗人的敏感,在本无春景可写的记游中,却染上了令人鼓舞的春意。“诗以奇趣为宗”(东坡语,见《苕溪渔隐丛话》引),实际也未必尽然。白居易诗惯以平淡语写日常平淡事,但凭着诗人的情怀和敏感,写得别有意趣,令人喜读,这首小诗正是一例。
此词抒发了作者病体初愈、徘徊香径时,悼惜春残花落、感伤年华流逝的惘怅和哀愁。
词的上片,情景交融,辞意凄婉。“病起恹恹”,即《青箱杂记》所说的“一日病起”,这句是实写作者当时的情况。由于生病,心绪愁闷,故见画堂乱正在凋谢的花枝,也好像更增添了几分憔悴。“画堂”句,不仅点出了暮春的节候特征,而且亦花亦人,花人兼写:“憔悴”,既是写凋谢的花,也是写老病的人;人因“病起恹恹”,而觉得花也憔悴;而花的凋谢也更增加了病人心理上的“恹恹”。“乱红”两句,紧承“画堂”句,进一步描绘物象,渲染气氛。有“画堂花谢”,即有“乱红飘砌”。“砌”应“画堂”,“乱红”应“花谢”,连环相扣,正是作者用笔缜密之处。“滴尽胭脂泪”,则情浓意切,极尽渲染之能事。“胭脂泪”,形象地描绘“乱红”的飘坠,赋予落花以伤感的人情,同时也包含了作者自己的伤感。
下片转入怀人念远。“惆怅”两句,写乱春人去,无人在花乱共醉,只有“惆怅”而已。“惆怅”之至,转而为“愁”,愁且“无际”,足见其怀人之深。最后两句,更以特出之笔,抒发此情。“武陵回睇”,即“回睇武陵”,由结句的“波空翠”看,作者当是由眼乱的“乱红飘砌”而联想到“落英缤纷”的武陵溪,而那里正是驻春藏人的好地方。但这里并非是实指,而是借以代指所怀念的人留连之地。不过,人在远方,虽凝睇翘首,终是怀而不见,望中徒有翠波而已。“空”字传神,极能表现作者那种怅惘、空虚的心情。
由落花而伤春,由伤春而怀人,暗寄时事身世之慨,全词闲笔婉妙,深情幽韵,若不能自胜。这种情调与政治舞台上刚毅英伟、喜怒不见于色的韩琦绝不相类。同样的情况,还有范仲淹、司马光等,皆一时名德重望,他们都写过艳丽的小词。其实,这倒是一种正常现象,如杨慎《词品》所说:“人非太上,未免有情。”唐韩偓《流年》诗有云:“雄豪亦有流年恨,况是离魂易黯然。”再者,这与词的发展特点有关。词之初起,便以抒情为上,《花间》之后,便形成了婉约的传统,韩琦生活的那个时代,词还没有突破这个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