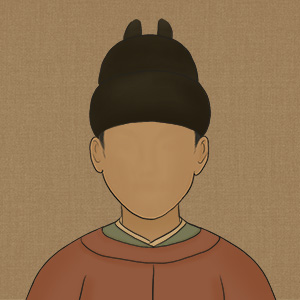兰花没有牡丹、海棠的妖冶富丽,也没有寒梅、霜菊的傲峭冷艳。它清秀雅洁,芳香馥郁,如淑女婷婷,似君子彬彬,别有一种幽淡孤清的风韵。历来富贵者爱牡丹,隐逸者爱菊梅,而清雅孤高、弱而不阿的文士就偏爱幽兰了。
崔涂这首诗通过咏写兰的贞芳幽独,寄托自己孤高而又哀伤的抑郁情怀,在咏兰诗中是偏于感伤的一类。诗篇兴寄鲜明,旨在抒情,所以诗人对兰不作描绘,而是集中笔墨,诉说兰花自持芬芳却遭风雨侵凌又被弃如路草的悲惨命运,以自伤不遇。诗篇写得质实、深婉,恰如一株飘零的幽兰,质而芳,柔而韧,顾盼自哀,低回不已。
诗人代兰自诉,娓娓说道。开篇先自剖高洁:“幽植众能知,芬芳只暗持。”幽兰常常生于山野、谷畔,但不因清寒而不开,不因无人而不芳。这两句写兰的芳质,又突出了兰幽植孤生,芬芳不被人识的客观处境。宋刘克庄咏兰诗中写它“深林不语抱幽贞,赖有微风递远馨”,意与此相近。但“幽植”二句除自剖之外,还暗责世俗不识芳洁,一笔两开,诗意半含半露,奠定了全篇顾盼、低回的韵调。
“自无君子佩”承首句,“未是国香衰”承次句。兰被推为“花草四雅”之首,有“花中君子”的美称,又因其幽香浓郁,有国香之誉。我国古人常以佩兰表示芳洁,屈赋中有“纫秋兰以为佩”的诗句,唐太宗李世民有《芳兰》诗:“会须君子折,佩里作芬芳。”与此相关,古来也把贤人遭弃比作芳兰无人采折。屈原内美而好修,却反遭斥逐,他慨叹“户服艾以盈要兮,谓幽兰其不可佩。”为统治者所不容的李白也发出“若无清风吹,香气为谁发”(《古风·秋兰》)的悲慨。秉性耿介,后被罢相的张九龄也咏兰为寄:“幽林芳意在,非是为人论。”(《悲秋兰》)“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感遇》)。这些诗或发抒不平,或自赏孤花,但都掩盖不住遭受冷遇的孤寂。而崔涂这两句,从主体客体两面着笔:兰花芳节香质不稍减,可君子却置之不顾。这是期待后的失望,内省后的自伤,更充满无可奈何的感伤情调。
“白露霑长早,青春每到迟。”因生于山林,寒露早至,使之先期零落;春光晚顾,又晚得佳期。这一迟一早,写出境遇之惨凄,显出芳魂玉质难得久持的无限悲苦,作吞吐哽咽之声。
诗篇已三层递进,愈转愈悲,但诗人仍情不能已。由于以上种种遭遇,兰对自己的生存意义产生了疑虑:“不知当路草,芳馥欲何为?”芳质高格,无人赏识,被弃掷路侧,形同荒草,那么自己独抱贞节,自开自芳,又有何用?步步退逼,终归于凄绝,把不遇之情,推至顶点。至此诗篇的抒情形象完成了。我们好象看到了一株生于草野当风离披的芳兰,又似看到了一个落拓不偶,抑郁难伸的贤士。
此诗运用传统的芳草美人的比兴手法。由于作者对兰的禀赋特征体察入微,自己的思想情调又与之相契,物性与人情,各自昭然,又妙合如一。诗中所言皆为兰,又无一不是作者的自道。王士祯说:“咏物之作,须如禅家所谓不粘不脱,不即不离,乃为上乘。”这正可用以评价此篇。
作为借物抒情的作品,它体物幽微表现细腻。诗情如一根不绝的丝缕,柔细绵长,欲断又续。既写出幽兰几遭侵凌,生机欲断,却期待不已、春心不死的柔韧之质;又表现了作者虽郁塞难伸,却执着人生追求不舍的深挚沉郁、无限凄苦之情,哀婉幽怨缠绵不尽。
此诗表现细腻,感情深微,诗境却并不狭小,诗的内涵十分丰富,有很高的典型意义。这不能不归之于作者对诗意的提炼和表达的灵活、准确。诗篇不仅咏物抒情相融相映,一笔两到,在具体表达中,用笔又始终是一语双关,言己言他,叹恨如一。使人一面感到幽兰的悲诉、哀凄,一面又感到世人的冷漠、霜露之无情,在鲜明的对比中,揭露了现实的严酷,使人不禁想起李商隐《咏蝉》的名句:“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在哀伤的感情中,又含有几分冷峻。这样,诗篇在自叹自伤之外,深刻地揭示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使这首取材平常的咏物诗表现了广泛的社会内容和深刻的思想意义。
戴复古的诗中同情劳动人民之作不乏其例。著名的如《庚子荐饥》等。可以看出,尽管戴复古名列江湖诗人之榜,但他并非一味地逍遥江湖。社会时事、人民生活时常撞击他的心灵,使我们更加了解了作者“身在江湖之上,心存魏阙之下”的良苦用心。
本诗在表达“农夫夏耘”而“吾安坐”这样一个主旨时,大胆地运用比喻和想象。虽然《庄子》中就是“今以天地为大炉”的说法,贾谊《鵩鸟赋》中也说:“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土;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但是,他们所要表述的思想实质是人在自然面前的无可奈何,而戴诗在运用这些比喻和想象的同时,又强调了农人于酷暑中的辛勤劳作,以致秋日百谷才能有收获。这样,就把暑热与农人生活紧密联系起来,而诗的主题也在暑热与农人劳作的交汇中得以升华。他用对生活深刻体验所描写的内容,实际上已经由“悯农”上升到“敬农”。较之唐代诗人李绅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思想境界更高一筹。
这是一首咏物诗。古人咏菊之作很多,但此诗为作者一念触发,灵感倏至而作。
头二句写作诗缘起,乡居野处的百姓出于对隐居的英雄的敬佩,相赠菊花。首句“战罢秋风笑物华”,起势不凡,一个“战”字,一个“笑”字,使横戈疆场而又乐观坚贞的民族英雄形象跃然纸上。次句“乡人偏自献菊花”,是对抗清英雄的崇高礼赞。诗的一、二句创造了赏菊的感情环境。
后两句则笔势急转,“已看铁骨经霜老,莫遣金心带雨斜”是全诗最铿锵有力、动人心魄的诗句。诗人由对自身的抒写转入对菊花的描绘。野菊挺秀的枝茎和灿然如火的黄花激发许多联想。花茎虽已经霜,仍不失挺拨咄咄之势;“铁骨”一词拟化出不畏风霜的菊花的伟岸不群的品格。诗人以怜惜的笔调写出对不畏风雨的菊花的爱护。后二句虽然字面上全为咏叹菊花的字句,但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野菊经霜不老的傲岸实为诗人自身凛凛正气的象征。无疑,后两句仍是在抒写诗人自己的豪情气概。
前两句是叙述,叙述中充满诗情,后两句借景抒情。“骨”与“心”都将菊花拟人化,赋予菊以人的性格。“骨”用“铁”字修饰,“心”用“金”字限定,既写出了菊花的凌霜贞姿,又写出了诗人的英雄品格。全诗写菊,又是写人,是写景,又是抒情,菊与人,景与情,洽合无间,融为一体。
此诗严格说来,不是纯粹的咏物诗,因为诗人的感情、精神时时介入其间,不过借菊花象征而已。但野菊的自然情态处处与涌荡于诗人胸中的奔逸之情相合,所以诗人才得以借菊花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就实质而言.作者描绘菊花的诗句已创造出一种艺术形式,从而将主体感情固着其中,菊花成为诗人情感的一个对等物。
开篇趣起,打趣自己,说只要清溪对岸有美酒,就可以招致自己这个难致的“幽人”前来。接韵以“更觉”的措辞,将自己与赵国兴暗中对照,以突出赵的“湖海豪气”。意谓因自己这样容易被招致,就更觉得赵这个有四方之志的湖海之士气度不凡、当卧百尺楼头了。“自叹”以下,直到结韵,全都是自我抒情。“自叹”一韵,伤惋自己年老才凋,作诗赋词,难以称意。上片末韵,明承起韵沽酒之辞,写自己得酒即醉、醉归于东风中的情态。暗接“不如人意”的句意,表达他欲因酒而排遣此愁的意思。有趣的是,这里写词人的醉态,不出以正笔,而以“松竹如醉”的曲笔来写,这就写透了他醉态朦胧的情态。而诗意正在“松竹如醉”的形容中。下片似写清醒时的思绪,其实是所谓“酒醉心灵”的思考产物。过片接上片末韵“东风”一词,写他对此春日美景若有所不足的遗憾感。此韵以“怎得”领起,表明所思所须实属不可得的用意。他所希望自己成为的,是庄周梦中那只栩栩然的物我浑一的蝴蝶,他希望作这一只蝴蝶,来纵情邀游于花丛间,把花底当成是整个的“人间世”即整个的世界。这就泄露了他希望忘世兼忘我的心意。而具有这种忘我兼忘世之想的人,显然是因为所承受的过于沉重痛苦之故,他在寻找着一个不可得的解脱。“记取”一韵,表明了他之所以想做庄周梦中的蝴蝶的部分原因。是因为暮春的江上,总是风狂雨骤,横暴的风雨从来不爱惜春天的美景,而要将它匆匆送走。“记取”一词,表明这种时光之忧,是他一直萦结在胸的旧伤痛。在“风雨”一句中,词人的悲凉、无奈之情可感。在这两韵里,花与春天的意象具有隐喻的色彩,它们隐指美好无憾的时光。同样,风雨也具有隐喻的色彩,它是作为破坏春天的对立面出现的,它是生命所不能把握的横暴力量的隐指。因为以上的隐喻色彩,所以尽管是写的自然春天的过程,也令词人产生了不能承受的“万斛愁”。这样无法称量的沉重愁恨,只有杯中酒才可以解除,因为它可以使人沉醉忘忧。而象征了富贵极盛的头上金貂,在此时光之优面前,则显得毫无意义———流逝的时光把金貂象征的富贵、把一切存在甩在自己的后面化为虚无。结韵关合全篇,以此词不过是一种《宾戏》的解释,把一切打空,用来回复赵知录。这样的结尾,固然表明了他的游戏态度,同时也更有深意。这深意就是,当词人反照自己的内心,发现了巨大的空虚和难以承受的痛苦时,他所去做的,不仅是以酒来沉醉忘情,更是要以排空一切的方式,来获得解脱。所以,这样的结尾,不是无聊的游戏,不是无意义的闲话,而是包容着一种压力和反压力的精神对抗的。
本词在章法上,打破上下片分段的词体常用格式,从上片第三韵就开始转为单纯写自己,是为变格;但变中有不变,如下片全为上片末韵引起,写自己春日归途上醉酒后的忧思与解脱。在表意上,全词似散而聚。所谓散,是指它头绪众多;既赞友人,又自叹衰老才枯;既写耽酒情状,又写耽酒的原因;既抒发好景不常的生命幽恨,又写忘世遣愁的心理需要。所谓聚,是指这么丰富的情意,曲曲折折地都可以用酒来收结:衰老才凋的闲愁可以用酒来打发,好景不常的生命大悲可以凭酒来遗忘,想做庄周梦中的那只蝴蝶而不可得的苦恼可以借酒来平息,乃至功名富贵终归无用的虚无之悲可以以酒来消除。
此诗是作者诀别故乡之作。起笔叙艰苦卓绝的飘零生涯,承笔发故土沦丧、山河破碎之悲愤慨叹,转笔抒眷念故土、怀恋亲人之深情,结笔盟誓志恢复之决心。既表达了此去誓死不屈的决心,又对行将永别的故乡流露出无限的依恋和深切的感叹。 全诗思路流畅清晰,感情跌宕豪壮。格调慷慨豪壮,读来令人荡气回肠。
“三年羁旅客,今日又南冠。”叙事。其中“羁旅”一词将诗人从父允彝、师陈子龙起兵抗清到身落敌手这三年辗转飘零、艰苦卓绝的抗清斗争生活作了高度简洁的概括。诗人起笔自叙抗清斗争经历,似乎平静出之,然细细咀嚼,自可读出诗人激越翻滚的情感波澜,自可读出平静的叙事之中深含着诗人满腔辛酸与无限沉痛。
“无限山河泪,谁言天地宽!”抒写诗人按捺不住的满腔悲愤。身落敌手被囚禁的结局,使诗人恢复壮志难酬,复国理想终成泡影,于是诗人悲愤了:“无限山河泪,谁言天地宽?”大明江山支离破碎,满目疮痍,衰颓破败,面对这一切,诗人禁不住“立尽黄昏泪几行”,流不尽“无限山河泪”。诗人一直冀盼明王朝东山再起,可最终时运不济,命途多舛,恢复故土、重整河山的爱国宏愿一次次落空,他禁不住深深地失望与哀恸,忍不住向上苍发出“谁言天地宽”的质问与诘责。
“已知泉路近,欲别故乡难。”坦露对故乡、亲人的依恋不舍之情。无论怎样失望、悲愤与哀恸,诗人终究对自己的人生结局非常清醒:“已知泉路近”。生命行将终结,诗人该会想些什么呢?“欲别故乡难”,诗人缘何难别故乡呢?原来,涌上他心头的不仅有国恨,更兼有家仇。父起义兵败,为国捐躯了。而自己是家中唯一的男孩,此次身落敌手,自是凶多吉少,难免一死,这样,家运不幸,恐无后嗣。念及自己长年奔波在外,未能尽孝于母,致使嫡母“托迹于空门”,生母“寄生于别姓”,自己一家“生不得相依,死不得相问”,念及让新婚妻子在家孤守两年,自己未能尽为夫之责任与义务,妻子是否已有身孕尚不得而知。想起这一切的一切,诗人内心自然涌起对家人深深的愧疚与无限依恋。
“毅魄归来日,灵旗空际看。”盟恢复之志。尽管故乡牵魂难别,但诗人终将恢复大志放在儿女私情之上,不以家运后嗣为念。正如诗人在《狱中上母书》中所表示的“二十年后,淳且与先文忠为北塞之举矣”。“已知泉路近”的诗人坦然作出“毅魄归来日”的打算,抱定誓死不屈、坚决复明的决心,生前未能完成大业,死后也要亲自看到后继者率部起义,恢复大明江山。诗作以落地有声的铮铮誓言作结,鲜明地昭示出诗人坚贞不屈的战斗精神、精忠报国的赤子情怀,给后继者以深情的勉励,给读者树立起一座国家与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不朽丰碑。
全诗思路流畅清晰,感情跌宕豪壮。起笔叙艰苦卓绝的飘零生涯,承笔发故土沦丧、山河破碎之悲愤慨叹,转笔抒眷念故土、怀恋亲人之深情,结笔盟誓志恢复之决心。诗作格调慷慨豪壮,令人读来荡气回肠,禁不住对这位富有强烈民族意识的少年英雄充满深深的敬意。
这首诗表达的不是对生命苦短的感慨,而是对山河沦丧的极度悲愤,对家乡亲人的无限依恋和对抗清斗争的坚定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