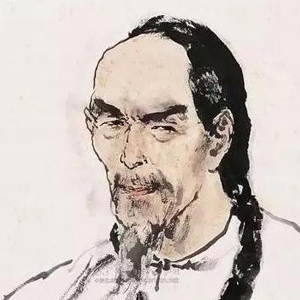《小雅·节南山》所指责的对象则是幽王及其权臣。前人屡辩诗旨是“刺王”还是“刺尹”,甚为无谓。总因古代君臣名分颇严,论者又往往横亘一“诗可以怨”或一“《小雅》怨诽而不乱”之念于胸中,因之便有不同的“先入为主”之念在作怪。今就诗论诗,直刺师尹,颇为鲜明;而一再怨望“昊天”,又借以指责天子。
关于师尹,自毛传以来皆解作“大师尹氏”,至王国维始辨析其为二人,即首掌军职的大师和首掌文职的史尹。观《大雅·常武》中大师“整六师”、尹氏及其属“戒师旅”,则大师统军而尹氏监军,对照《小雅·节南山》诗首章,“忧心如惔,不敢戏谈”正合于军国主义背景,偏于责师;而“国既卒斩,何用不监”。乃监察司之失职,偏于斥尹。
全诗十章,共分三部分。首二章以南山起兴,以象征二权臣。以山之险要象征其权之枢要,又以山之不平联系到二臣秉政不平。结合篇末“昊天不平,我王不宁”的呼应来看,天怒人怨,总由师尹秉政不平使然,故“不平”二字为全篇眼目。只是第二部分却一再将不平(不夷)与不己(不自为政)并提而责难,推思其义,全诗是指斥师尹失政在不能持平(夷),而要持平则又须事必躬亲(己),因而全诗结构是起于夷(平)终于夷(平)而介于己。
首章点出“不敢戏谈”以致“国既卒斩”;二章点出昊天再降饥疫以致“丧乱弘多”,民众无法存活,从而“不敢戏谈”之高压失控,遂而“民言无嘉”。一章言人祸,二章言天灾,由时间及顺序暗示天灾实人祸所致,人间暴戾上干天怒所致,此即第一部分的要害。
从第三到第六共四章为第二部分。在上两章铺垫的基础上,三章进一步点明师尹之害人害天,天再施报于人,人民双重遭殃。“诗可以怨”,怨而至天,亦已极矣!
四、五两章句式排比,结构整齐而又不乏疏宕之美。四章围绕“夷”“己”二字正反展开,既为师尹说法,更为一切秉政者说法,三十二字可铭于座右,可镌于通衢。五章“昊天不佣(融)”“昊天不惠(慧)”二解是“刺”,“君子如届(临、己)”“君子如夷(平)”二解是“美”,也是对师尹说法。两章排比、对比之势,酣畅淋漓,一气呵成,诗人的责怨之情也推到了高潮。
六章承上启下,由怒转叹。
统观第二部分四个章节,结构颇为讲究:五、六章既以“昊天不佣”“昊天不惠”和“不吊昊天”以上应第三章的“不吊昊天”,又以“君子如届(临、己)”、“君子如夷”和“谁秉国成(平、夷)”、“不自为政(不己)”以上应第四章的“式夷式已”,可见此部分是以怨天和尤人双向展开而又并拢合承,甚耐玩味。
第七、八、九、十章为第三部分。变每章八句为四句,于音乐为变奏。于诗情为由怨怒转悲叹。唯七、八两章疑有错简而当易位:前“方茂尔恶”章言师党与尹党既相倾轧又相勾结,以见朝政难革;后“驾彼四牡”章言无奈之下只有往奔四国避乱(或求诸侯勤王),然而四方亦不可往,“蹙蹙靡所骋”。诗人说:既然宗周与四国皆被师尹扰乱,国已不国,今日上干天怒,下危人主,尽管师尹不自责己而反怨怒匡正,我身为大夫,也只有勇作诗“诵”,“以究王讻”,成此一篇檄文,为来者垂诫了!
《无家别》和“三别”中的其他两篇一样,叙事诗的“叙述人”不是作者,而是诗中的主人公。这个主人公是又一次被征去当兵的独身汉,既无人为他送别,又无人可以告别,然而在踏上征途之际,依然情不自禁地自言自语,仿佛是对老天爷诉说他无家可别的悲哀。
从开头至“一二老寡妻”共十四句,总写乱后回乡所见,而以“贱子因阵败,归来寻旧蹊”两句插在中间,将这一大段隔成两个小段。前一小段,以追叙发端,写那个自称“贱子”的军人回乡之后,看见自己的家乡面目全非,一片荒凉,于是抚今忆昔,概括地诉说了家乡的今昔变化。“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这两句正面写今,但背后已藏着昔。“天宝后”如此,那么就会想到天宝前的情况。于是自然地引出下两句。那时候“我里百余家”,应是园庐相望,鸡犬相闻,当然并不寂寞:“天宝后”则遭逢世乱,居人各自东西,园庐荒废,蒿藜(野草)丛生,自然就寂寞了。一起头就用“寂寞”二字,渲染满目萧条的景象,表现出主人公触目伤怀的悲凉心情,为全诗定了基调。“世乱”二字与“天宝后”呼应,写出了今昔变化的原因,也点明了“无家”可“别”的根源。“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两句,紧承“世乱各东西”而来,如闻“我”的叹息之声,强烈地表现了主人公的悲伤情绪。
前一小段概括全貌,后一小段则描写细节,而以“贱子因阵败,归来寻旧蹊”承前启后,作为过渡。“寻”字刻画入微,“旧”字含意深广。家乡的“旧蹊”走过千百趟,闭着眼都不会迷路,如今却要“寻”,见得已非旧时面貌,早被蒿藜淹没了。“旧”字追昔,应“我里百余家”:“寻”字抚今,应“园庐但蒿藜”。“久行见空巷,日瘦气惨凄。但对狐与狸,竖毛怒我啼。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写“贱子”由接近村庄到进入村巷,访问四邻。“久行”承“寻旧蹊”来,传“寻”字之神。距离不远而需久行,见得旧蹊极难辨认,寻来寻去,绕了许多弯路。“空巷”言其无人,应“世乱各东西”。“日瘦气惨凄”一句,用拟人化手法融景入情,烘托出主人公“见空巷”时的凄惨心境。“但对狐与狸”的“但”字,与前面的“空”字照应。当年“百余家”聚居,村巷中人来人往,笑语喧阗;如今却只与狐狸相对。而那些“狐与狸”竟反客为主,一见“我”就脊毛直竖,冲着“我”怒叫,好像责怪“我”不该闯入它们的家园。遍访四邻,发现只有“一二老寡妻”还活着!见到她们,自然有许多话要问要说,但杜甫却把这些全省略了,给读者留下了驰骋想象的空间。而当读到后面的“永痛长病母,五年委沟溪”时,就不难想见与“老寡妻”问答的内容和彼此激动的表情。
“宿鸟恋本枝,安辞且穷栖。方春独荷锄,日暮还灌畦。”──这在结构上自成一段,写主人公回乡后的生活。前两句,以宿鸟为喻,表现了留恋乡土的感情。后两句,写主人公怀着悲哀的感情又开始了披星戴月的辛勤劳动,希望能在家乡活下去,不管多么贫困和孤独!
最后一段,写无家而又别离。“县吏知我至,召令习鼓鞞”,波澜忽起。以下六句,层层转折。“虽从本州役,内顾无所携”,这是第一层转折;上句自幸,下句自伤。这次虽然在本州服役,但内顾一无所有,既无人为“我”送行,又无东西可携带,怎能不令“我”伤心!“近行止一身,远去终转迷”,这是第二层转折。“近行”孑然一身,已令人伤感;但既然当兵,将来终归要远去前线的,真是前途迷茫,未知葬身何处!“家乡既荡尽,远近理亦齐”,这是第三层转折。回头一想,家乡已经荡然一空,“近行”、“远去”,又有什么差别!六句诗抑扬顿挫,层层深入,细致入微地描写了主人公听到召令之后的心理变化。如刘辰翁所说:“写至此,可以泣鬼神矣!”(见杨伦《杜诗镜铨》引)沈德潜在讲到杜甫“独开生面”的表现手法时指出:“……又有透过一层法。如《无家别》篇中云:‘县吏知我至,召令习鼓鞞。’无家客而遣之从征,极不堪事也;然明说不堪,其味便浅。此云‘家乡既荡尽,远近理亦齐’,转作旷达,弥见沉痛矣。”
“永痛长病母,五年委沟溪。生我不得力,终身两酸嘶。”尽管强作达观,自宽自解,而最悲痛的事终于涌上心头:前次应征之前就已长期卧病的老娘在“我”五年从军期间死去了!死后又得不到“我”的埋葬,以致委骨沟溪!这使“我”一辈子都难过。这几句,极写母亡之痛、家破之惨。于是紧扣题目,以反诘语作结:“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意思是:已经没有家,还要抓走,叫人怎样做老百姓呢?
诗题“无家别”,第一大段写乱后回乡所见,以主人公行近村庄、进入村巷划分层次,由远及近,有条不紊。远景只概括全貌,近景则描写细节。第三大段写主人公心理活动,又分几层转折,愈转愈深,刻画入微。层次清晰,结构谨严。诗人还善用简练、形象的语言,写富有特征性的事物。诗中“园庐但蒿藜”、“但对狐与狸”,概括性更强。“蒿藜”、“狐狸”,在这里是富有特征性的事物。谁也不能容忍在自己的房院田园中长满蒿藜。在人烟稠密的村庄里,狐狸也不敢横行无忌。“园庐但蒿藜”、“但对狐与狸”,仅仅十个字,就把人烟灭绝、田庐荒废的惨象活画了出来。其他如“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也是富有特征性的。正因为是“老寡妻”,所以还能在那里苟延残喘。稍能派上用场的,如果不是事前逃走,就必然被官府抓走。诗中的主人公就是刚一回村,就又被抓走了的。诗用第一人称,让主人公直接出面,对读者诉说他的所见、所遇、所感,因而不仅通过人物的主观抒情表现了人物的心理状态,而且通过环境描写也反映了人物的思想感情。几年前被官府抓去当兵的“我”死里逃生,好容易回到故乡,满以为可以和骨肉邻里相聚了;然而事与愿违,看见的是一片“蒿藜”,走进的是一条“空巷”,遇到的是竖毛怒叫的狐狸,真是满目凄凉,百感交集!于是连日头看上去也消瘦了。“日”无所谓肥瘦,由于自己心情悲凉,因而看见日光黯淡,景象凄惨。正因为情景交融,人物塑造与环境描写结合,所以能在短短的篇幅里塑造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反映出当时战区人民的共同遭遇,对统治者的残暴、腐朽,进行了有力的鞭挞。
民歌中,情歌一类数量很多。它不仅有较高的审美娱乐价值,而且也起到实际的爱情桥梁的作用。在我国西南民间,对歌的风俗自古很盛。刘禹锡谪居巴楚间的诗作中就有这种民俗的描写,这首《踏歌词》就是。踏歌是不用伴奏、踏地以为节拍的徒歌,是民歌的一种唱法。刘禹锡居夔州时创作了《踏歌词四首》,这是第一首。
开篇以景起兴。春江水涨,几乎平堤。尤其在月下,堤面和江面都明晃晃连成一片,更给人水与堤平的感觉。“大堤平”三字,不仅写出江水上涨,大堤平宽,还写出月色的皎洁。就在这样的春江花月夜,堤上走着成队的“女郎”。她们都是生在村野的民间姑娘,是趁月圆之夜“踏歌”来的。她们初来的情态是彼此偎靠连袂而行,既兴奋,又含几分娇羞。一二句写“春江月出”,是暮色;三四句写到“红霞映树”,是拂晓,其间有较长的时间跨度,省略了一些情事。从三句的“唱尽新词”和“欢”等字样看,省去的正是“新词宛转递相传”的对歌的情景。民间对歌,词儿大多是即兴新编,言为心声,所以是“新词”。“欢”则是女方所悦的男子,即对歌的另一方。歌声一起,姑娘们最初的娇羞立即被赶跑了,到后来,新词唱尽,便与所欢相就。所以同组第三首《踏歌词·新词宛转递相传》就写道:“月落乌啼云雨(指男女私情)散,游童陌上拾花钿。”在这样美丽的夜晚并非十全十美,有人找到情侣,同时也有人找不到。三四句正是这样一个特写的镜头。它表现的并不是全部的女郎而是其中的某一个。在别人都凭歌声为媒介而会到自己所“欢”的时候,她却是“唱尽新词欢不见”,尝到了失望的滋味。但她仍旧怀着希望,一直等到“红霞映树”的早晨。小伙子最后是否来了,“鹧鸪鸣”声似乎有所暗示。然而终究是个谜,有两种猜法。鹧鸪雄雌和鸣,也许暗示姑娘终于等到了自己的心上人。但也可以是相反,这双双鸟儿和鸣之声反衬出她的烦恼。不光这结尾有些扑朔迷离,第三句省略的主词也有解作女郎全体的。从而这就成了一个很离奇的夜晚——小伙子们都没有来,姑娘们都有些不堪。总之,由于使用了省略和暗示的语言,使得此诗意境灵活,不易确指。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诗写出了妙龄中的女郎对爱情失望而有所期待的心情。
咏物词发展到南宋已进入成熟期,不仅作品数量众多,而且更重视写作技巧和形式类。与北宋的咏物词相比较,南宋咏物词更具有一种幽微细腻的特色,虽然不容易看出其寄托所在,但更富有朦胧美。张鎡的这首词就能够将作者内心的情思同作品外化的意象融合无间,使读者若有所悟又难以名状。
词的上片集中刻画了芭蕉独特的风姿和品格。起句从芭蕉跟别的花卉草木的对比中写出它同中有异的特点。在人们眼光中,“风流”、“多情”、“潇洒”是许多花卉草木所共有的,然而词人之所以特别欣赏芭蕉,却是由于它那独特的清逸绝俗风姿。芭蕉并不以色彩斑斓、绚丽多姿的花朵来显示它的“风流”,它也不在丽日和风中与群芳争妍,只有到了烟雨空濛和雨滴拍打的时刻,芭蕉,这才以一身潇洒的绿衣,显示出它那特有的风韵和情致,吸引人们观赏,撩拨人们的情思。一切繁喧炽热跟芭蕉无缘,它浑身上下透出的是无限清凉。不仅使人想起吴文英的名句“纵芭蕉不雨也飕飕”(《唐多令》),这样,我们从芭蕉独具的潇洒、清凉,依稀感受到词人的心灵,现出了一个风流、多情、而又潇洒雅洁的文人形象。
下片顺着“绿衣长”、“满身凉”的拟人化的描写发展,逐渐从外形深入到心灵。词人观赏芭蕉风情万种,情为之动;芭蕉得遇知音,也动起感情来了。看,那一片片开张伸展的硕大绿叶,就像是在我面前铺开的文笺,要请我在上面题写生动的诗句呢!但我又能写什么呢?这时,明月已升到中天,清辉泻在芭蕉那略披白粉的绿叶上,好象生出了一层薄薄的寒霜,袭来一阵又一阵寒气。唉,别再倚着阑干痴看了,还是回屋去吧!“莫凭小阑干,月明生夜寒”两句,淡淡地透露出词人在此情此景下若有所思、若有所悟的感触。这种感触是什么呢?是芭蕉的清高与索句的催迫使他感到自愧弗如、无辞以对?是眼前的清冷促使他想到了趋炎附势的炎凉世态?还是“以其境过清”(柳宗元《小石潭记》),“凛乎其不可久留”(苏轼《后赤壁赋》),而只得消然离去呢?词人没有明白说出,却留下了让读者充分联想、回味的余地,言有尽而意无穷。
在诗词中,芭蕉常常同孤独忧愁特别是离情别绪相联系。李清照曾写过:“窗前谁种芭蕉树?阴满中庭。阴满中庭,叶叶心心舒卷有余情。伤心枕上三更雨,点滴霖霪。点滴霖霪,愁损北人不惯起来听。”(《添字丑奴儿》)把伤心、愁闷情绪一古脑儿倾吐出来,对芭蕉甚至还颇为怨悱。张鎡这首词的感情抒发却相当空灵含蓄。他的哀愁和悲凉并没有直接倾吐,而是在雨丝烟雾里,在寒夜月色中,朦胧而自然地流露出来。一缕淡淡的哀愁回肠九曲,大有欲吐又吞、欲说还休的况味。
张鎡的这首词与唐代钱珝的《未展芭蕉》诗(冷烛无烟绿惜干,芳心犹卷怯春寒。一缄书札藏何事,会被车风暗拆看。),虽然暗示性有所不及,但在总体意境上更富有象征意蕴,表达上也越显得曲折幽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