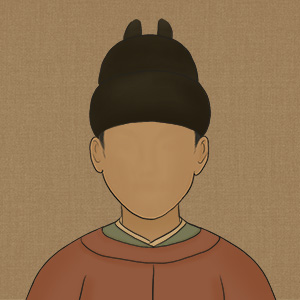黄庭坚于途中过访徐积,畅叙之后又匆匆分别,诗即写在黄庭坚别去之后,从未见故人写到既见故人,再写到分手后的思念之意。前二句的意境与《诗经·草虫》中“未见君子,忧心惙惙,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说”的描写相类似。通过未见时与已见后的对照,真实地表达了朋友间心心相印、情投意合的感情。
后两句极言故人去后,诗人梦萦魂绕的思念之情。这里用了极度夸张的手法,而造意新奇,想落天外。梦本是无意识的,但诗人却说梦魂有意地去追寻友人的踪迹,已是神奇绝妙;追寻而不得,其原因竟在忘了问其船泊的停靠处,所以梦绕西城,不忍心马上离开。这两句同时也婉转地表现了诗人对黄庭坚的情意之笃,留恋之深。这里忘却问船泊处是现实中之事,而清梦绕西城是梦幻中之情,诗人故意将梦与真交织在一起,造成了一种亦真亦幻、亦实亦虚的艺术境界。两句诗感情诚挚、意味深长,写积想成梦,梦中寻友之情正与杜甫《梦李白》中“魂来枫林青,魂返关塞黑”诸语异曲同工。而因此诗是绝句,故更为凝炼。
全诗纯以时间为次,章法井然有序,语言质朴,全篇几乎没有一个修饰的词语,如同随手书写一样,然而其中表现的感情却是深沉笃实,皆自肺腑中流出。
“琼姿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处处栽?”琼姿,这是古诗词中的常用词了,谓瑰丽的姿容,通常只用于梅花。不过,诗的首联,却一点也不因这措辞的常见而显得平凡:神话中的昆仑山,上有瑶台十二座,皆以五色彩玉筑成;梅花既有瑰丽的风姿,那么就本该(合,应该)充任瑶台上的琼玉,至于它们为何不留居在飘渺的仙山,却被不知哪位仙家之手,栽向了江南的处处山林,这,可真是个令人大惑不解的疑问!这二句,给凡间的梅花,赋予了谪仙的身份,使它们纵然已降生到地上,却终究是超凡出尘、气质异于俗中众花。若不是诗人对梅的品行理解至深,安能作此奇想、出此奇语、发此奇问?至于为何只说栽于江南,而不说栽于天下,这,也可算得个疑问:大概,诗人一生足迹不出江南,在他的心目中,只有这片山川钟秀、人杰地灵的广土,才最适宜迎接梅的降临?
“雪满山中高士卧”,梅花到底还是来到了人间,不过,它们既然是夙具仙骨,当然也不屑在尘埃之中生长;远离人迹的烦嚣,栖住到大雪铺满的深山,这,才是这位孤高拔俗的隐士的愿望。常人说到梅花,总不免提什么“傲霜斗雪”,其实,梅花又何尝逞勇好斗?雪满山中,它们却稳稳地酣卧,何尝把大雪放在心上?大雪又怎配做它们的对头?“月明林下美人来”,梅花到底是花的一种,是世人愿意亲近的美人,不过,这美人既然是仙子下凡,俗人当然不能轻易窥到,若去闹市中寻觅,无异于水中捞月。你须得摒弃一切俗念,退身到清风明月的林泉之下,那时,你才能见到她款款而来,神情是那么超朗闲雅,容貌是那么清秀动人,一如《世说新语》中的咏絮才女谢道蕴,“神情散朗”,有“林下风气”。
“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请反复吟诵这千古名句,请反复体味其中的含义:独立而无惊、无憾的高士,秀雅而不艳、不俗的美人,梅花的高洁精神,不正化身于这二者而得到了最生动的显现了吗?
“寒依疏影萧萧竹,春掩残香漠漠苔。”这二句是分承上二句,再作进一步的申说,其原来的含义,应该是如下:山间的苍苍秀竹,自不会放过与高士交结的机会,它们把自己萧萧竹声中的清寒,奉献给梅花的身影,好让那疏朗的梅影得了清寒的依附,更显得仪态高峻;山间最不起眼的漠漠青苔(漠漠,密布之貌),也知道爱怜美人,当她完成了报春的使命,零落的花瓣半蚀于春泥之时,它们也会把自己身携的微微春意,轻轻遮掩在她残留的清香之上,好让无意争春的美人,也多少领受点春的回报。这二句的正常顺序,本来也该是“萧萧寒竹依疏影,漠漠春苔掩残香”,殊不料,诗人却把“寒”与“春”提炼到醒目的句首,显得这二者才是依托于“疏影”、“残香”的梅之魂魄,而遗于句尾的“竹”、“苔”,倒成了这二者蜕下的躯壳。次序一变,诗的境界顿异,诗人的笔法,真是老到。
“自去何郎无好咏,东风愁寂几回开?”何郎,指南朝的诗人何逊,作有《扬州法曹梅花盛开》等诗,虽然他不是第一个咏梅者,但诗人大概认为梅花的“好咏”(佳作)自他而始。在何逊之后,诗坛上当然也不乏“好咏”,但诗人在这里说梅花自从何逊去了便不逢知己,使自己不禁要问它们在漫漫的岁月里,寂寞愁苦地在东风中开落了多少回,似乎近千年来只生出自己一个梅花的知音——这,说他目无古人、过于自负,也未尝不是;但若没这份空前的自信,又如何有胆量抛开古人的陈规所限,别创出这千古佳作?况且,佳作既已咏成,就算他真的笑傲古人,古人到底也指摘他不得!
具体的梅易写,抽象的梅难说;梅之形态易赋,梅之精魂难摄。何也?诗人若不先禀有梅的灵性,又安能窥到梅的灵魂深处?因此,由此意义上说,读者最该佩服的,倒不在诗人手笔的高妙,而应是诗人襟怀的高洁;读者在梅的“疏影”之上,也更该细看是否有诗人自己的身影在“依”着。
临末还有一点说明。注家谓:“雪满山中”句,出自东汉袁安卧雪之典;“月明林下”句,出自隋朝赵师雄在月夜林中逢美人饮酒、醒来在大梅树下之典。(见清人金坛《高青丘诗集注》)其实,袁安卧雪在城中,而不在山上;赵师雄所遇的美人,与赵在酒肆中狎饮,岂可算梅花的化身?清人寻出的典故,多有胶柱鼓瑟之病,今悉不取。
在一个秋晚,道途仆仆的诗中主人停车阴山脚下,对着苍茫景色,顿生思古之幽情。
这首《玉楼春》抒写闺怨,所创设的意境是:暮春时节,梁燕双飞,落红满地。女主人公愁倚锦屏,感到“春色恼人”,好天良夜而玉郎不见,不禁泪滴绣衫。全词意境优美,婉丽多姿。
上片写卷帘所见,怨情油然而生。首句用梁间燕语,表现“画堂”“寂寂”,以动写静,人物情感也寓于其中;“高卷”句在结构上是过渡;后两句是触景伤情:帘外“一庭春色”,本人公感到并不为己所有,故有“恼人”之感;而“满地落花”则又使她想到青春难再!
下片首二句用“愁倚”、“泪滴”写她触景伤精时的容态;结尾二句,点出原由。对月怀人,深为“四美”(良辰、美景、赏心、乐事)难全而伤心。
在艺术上,此词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意象的装饰性特征。词中的“画堂”、“落花”、“锦屏”等都是较为典型的装饰性意象,在颜色、形状等方面都是有着鲜明的图案性质的。这些具有图案性质的意象构织出整体的图案。这些意象,并非是词人的兴会所得,而是具有审美抽象性质的意象构织而成的,也就是说,它们没有个体化的、殊相的特征,都是一种具有抽象意义的意象。它们缺少随机感兴的鲜活感,但却具有一些可以相互诠释的意味。文学语言的图案化,在晚唐五代词中是最为典型的。因此可以说,此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晚唐五代词的共同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