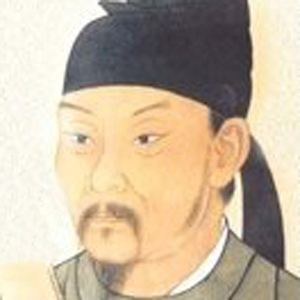这首写风雪渡江的诗,用极古简的笔法,绘出一幅饶有情致的图画。首句点出地点,诗人正“渡”的是汉江环绕襄阳、岘山的一段,这同时也是写景,淡淡勾勒出岘山的轮廓,在灰色的冬晚天空背景衬托下,岘亭的影子显得特别惹眼和好看。次句点节令(“岁阑”),兼写江上景色。由于岁暮天寒逆旅主人,故“古道少行人”。然而“渡口只宜寂寂,人行须是疏疏”,反而增添了一种诗情画意。三句是寄语备酒,借此引起末句“夜来风雪过江寒”:江间风雪弥漫,岘山渐渐隐没在雪幕之中,一叶扁舟正冲风冒雪过江而来。末二句用“为报”的寄语方式喝起,在读者面前展示了一幅天生的图画,而且仿佛人在画图中。
说它如画,似乎还远不能穷尽此诗的好处。虽然诗人无一语道及自己的身份、经历和心情,但诗中有一股郁结之气入人很深。
襄阳这地方,不仅具有山水形胜之美,历来更有多少令人神往的风流人物,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晋代的羊祜。史载他镇守襄阳,务修德政,身后当地百姓为他在岘山置碑,即有名的“堕泪碑”。诗的首句说“襄阳好向岘亭看”,绝不仅仅是就风光“好”而言的,那尽人皆知的羊公碑,诗人是不会不想到的。而且,诗的后面,越来越深蕴了一种怀古之情。前面提到岘山“岘亭”,紧接就说“人物萧条”,也不仅仅是就江上少人行而言的,还有一种“时无英雄”的感喟盘旋句中。
“习家池”乃襄阳名胜之一。在那注重名士风度的晋代,“习家”曾是襄阳的望族,出过像习凿齿那样的大名士。在重冠冕(官阶爵禄)压倒重门阀的唐代,诸习氏自然是今不如昔了。第三句不言“主人”或“酒家”,而言“习家”,是十分有味的。它不仅使诗中情事具有特殊地方色彩,而且包含浓厚的怀古情绪,引人产生一种“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的感慨。怀着这样的心情,所以诗人“初渡汉江”就能像老相识一样“为报习家多置酒”了。不光“置酒”而且要“多”,除因“夜来风雪过江寒”的缘故,而联系前文,还有更深一层涵义,这就是要借酒杯一浇胸中块垒,不明说尤含蓄有味。这两句写得颇有情致,开口就要主人“多置酒”,于不客气中表现出豪爽不羁的情怀。
于是,在那风雪汉江渡头如画的背景之上,一个人物形象(抒情主人公形象)越来越鲜明地凸现出来。就像电影镜头的“迭印”,他先是隐然于画面中的,随着人们对画面的凝神玩赏而渐渐显影。这个人似乎心事重重而举措落落大方,尽管他有一肚皮不合时宜,却没有儒生的酸气,倒有几分豪侠味儿。这大约是一个落魄的有志之士吧。他别有怀抱,却将一腔感慨愤疾,以淡语出之,诗的风格十分沉郁。而这种风格,在绝句中是不多见的。
令人觉得奇怪的是,用散文的形式写作喜雨的,在文学史上却并不多见。因此,苏轼的这篇散文《喜雨亭记》就显得十分突出了。当然,如果仅仅是因为前人未写而自己写了这一题材,对文学史有所贡献尚不足为奇。一旦后人接手写作,超越了前人的作品,那么前者就只能有一点文学史的价值而谈不到什么艺术的永恒价值了。苏轼的《喜雨亭记》却不是这样,因为它自身就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有许多令人品味的地方。也许正是这一点,使得后来的作家裹足不前,心甘情愿地让苏轼一枝独秀了吧。
文章开始即点明了用“雨”命名的缘由,与“喜”字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一共援引了历史上的三件事作铺垫,说明古人有了喜事,常常受用这件喜事来命名,以纪念喜事,或者也有预示将来喜事连连的意思。这三件事都很有趣。因为它们与国家的政治都有关系,其中并多少含有天人的关系。第一件事,相传周成王的同母弟堂叔得一异禾,献给了成王。成王将禾转送了周公。周公于是作了《嘉禾》一篇。第二件事,汉武帝于公元前116年5月,在汾水上得一宝鼎,于是改年号为元鼎元年。第三件事,鲁文公十一年,北狄鄋瞒国伐鲁,鲁文公派叔孙得臣抗敌,获胜,并俘获了国君侨如,于是特自己的儿子命名为侨如。最后这件事,对今人来说,几乎困惑不解了。为什么将敌人的名称用作自己儿子的名字?这是颇为值得研究的事情。无论如何,这是作者为要以雨志亭所作的铺垫,有了这一铺垫,再说事和雨就有记述的道理了。这就像逻辑学中大前提、小前提的三段论一样,有了大前提,后面的话即好说许多,也容易让人接受。
苏轼到风翔府任职的第二年,建官舍,行政事,凿池引流,美化环境,但不巧的是当地整整一个月没有下雨,旱情显现,灾情就会是必然的结果了。大旱望云霓,百姓的忧愁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恰好显示了苏轼笔墨的巧妙。我们知道,苏轼在写《后赤壁赋》的时候,曾经说到自己孤独闲寂,正好有两个朋友来了;霜露既降、明月诱人,想酒而樽空,贤妻正好献上了珍藏多时的美酒;没有下酒之物,正好客人笑哈哈地拿出了出水时鲜。一切就是那么巧,又那么惬人心意。这里也同样如此。百姓们盼望下雨,望眼欲穿,结果是“乙卯乃雨,甲子又雨”,这种句子,轻淡、简单,但不寡味,很像甲骨卜辞中的语言,但甲骨卜辞中是占问、预测,这里则是如实提供了,所以这种句子读来是令人心醉的。够不够?“百姓以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按,乙卯是四月初二日,甲子是四月十一日,丁卯是四月十四日。半月之内连降了三场雨,前两次不足,第三次一连下了三天。下得透,下得足,下得实在。要说好雨,喜雨,这才真正称得上是好雨,喜雨!杜甫的“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总令人有细小入微不够大气的感觉。这里我们要注意“民以为未足”一句的作用,这一抑、一落,然后产生后面的三日大雨,效果才能够显示出来。没有这么一句,当然也可以成立,但是读起来就平软的多了。
这场大雨产生的欢快气氛是可观的:“官吏相与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农夫相与忭于野,忧者以喜,病者以愈……”。这是一幅万民同乐官民同欢的喜庆图,较之欧阳修的太守和民的欢乐,真不可同日而语,因为欧阳修的乐并没有落到实处,架空,浮廓,是在造文、造情,而苏轼这里却是在如实地写作了。我们仿佛也同苏轼一起融入了喜雨的场景之中。唯其如此,苏轼为新落成的亭子命名“喜雨”才是顺理成章之事,才真正具有意义。
亭名由来有自,讲清楚之后也就等于曲终奏雅,逐善可陈了。但是苏轼又在这里做出了好文章,说他善于翻空出奇也好,说他敢于寻根溯源也好,无论如何,作者在这里表现出了惊人的艺术技巧。作者把笔锋一转,以设问的方式,从反面人手来探讨喜雨。曲径通幽,我们试想,也许这是继续写此雨的唯一途径,但苏轼找到了,并不一定是妙手偶得,可能是苏轼的真正功力所在。文中说道:“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则无麦。……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则无禾。”无麦无禾,饿鸿遍野,盗贼蜂起,百姓遭殃。但是不到五日,不到十日,就喜雨骤至,泽惠我民,又怎么能说不是上天厚待苍生?加上这么一段,文章就显得十分充实,丰满,在对比中更觉得雨之可喜。
写到这里,苏轼开始笔歌墨舞了,但是也曲尽其妙。“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为襦;使天而雨玉,饥者不得以为粟,一雨三日,伊谁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归之天子,天子曰不然;归之造物,造物不以为功;归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你看,他还是落在亭上,层层递进,把天降喜雨的大功劳像画饼一样,在太守、天子、造物和太空面前虚晃一二,并忙里偷闲找出了一句,让这些人都一一默然,谦虚地拒绝这一荣耀,多漂亮的话,各路诸侯都奉到了,然后再实实在在地放到主题上去。既然如此,就让我们以喜雨来为亭子命名吧。一虚一实,一推一进,总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作者紧扣一个“雨”字.一个“喜”字。在不到五百字的文章中,“雨”字出现了十五次,有两次作动词使用,“喜”、“乐”共出现六次。通篇都贯穿着为雨而喜的喜气洋洋的气氛。
中国古代,自孟子开始,创天子、官员要有与民同乐,乐民之乐的思想。写这种作品的人很多,但真正写得好的不多。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是其一,苏轼的此篇文章则表现得更好,好就好在落实、不空。
这篇文章在用词上也有值得注意之处。一、排比句多。比如第一段,作者为了说明古人有喜事则名物以示不忘,举了三个例子,三个例子就是三个排比句,借助这种句法,使读者在文意方面有一种说理透彻,充实满足的感觉。第二段写大雨之后,百姓的欢乐场面以及第四段的“雨珠”“雨玉”说,也同样用的是排比形式。在人们喜之不尽,手舞足蹈之时,文字上必须有所变化,一味的松散不可能有文字的整饬条理来得惹眼引人。二、结尾的用韵。《喜雨亭记》的结尾很有意思,它既照应了开头,又给人许多的联想,值得我们注意。苏轼的哲学思想是儒释道三家合一的。在他的诗文中,经常出现对大自然发问的句子,以表达他的人生观和他旷达乐天的情怀。这次大雨之后,感谢谁为好?这里他展开的想象,是从太守到天子,从天子到上天,从上天到造物,其中“玉”、“粟”押韵,“日”“力”押韵,“功“空”押韵,“冥”“名”押韵,读之有循环不尽,均成系统的感觉,神完气足,优雅俊美,然而是虚笔,真正目的则是要归之其小小的亭宇,这样也就把造物、上天、天子、太守、百姓、借助“喜”之“雨”用一个亭子联系了起来,有歌唱的味道,所唱者依然是喜雨,一篇文章的主题所在。
为什么古代关中富甲天下,而近代却默默无闻,特别是唐以后人文凋敝。是不是我们的人种退化了,我近来翻阅(唐代移民史),似乎找到了部分答案。在唐末到宋初的移民浪潮中,关中地区首当其冲,人口大量向东迁移,先经洛阳,然后到苏州扬州等运河地区。大家熟知的大文学家范仲淹,祖籍陕西彬县,但却是苏州人。但我们从其文学作品中仍能感受到其陕人后裔的豪迈文风,范仲淹后来也多年在陕从官,报效桑梓。其实在唐末吴县(今天的苏州地区)已有1/3的北方移民。其实不管是从西周之镐京到东周之洛邑;还是西汉之长安到东汉之洛阳;从隋炀帝迁都洛阳到武则天时期42年居住洛阳,关中地区到洛阳的人口迁移一直是单向的,并又有一次向东南方向迁居。还有明代昆山人顾炎武,曾在华山滞留多年,写下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佳句。写到这里,不得不提到大文豪苏东坡,苏东坡初仕凤翔府签书判官,也就是我的家乡陕西凤翔,凤翔是唐王朝的西京,曾经是晚唐人才和贵族的聚居地。苏东坡初仕凤翔府签书判官三年,可以说对他的人生价值关影响至重,正是由于家乡的纯朴民风,和周秦文化发祥故里文化的熏陶,对其文风产生影响。如果说一个人最难忘记的是自己的初恋,那苏东坡同样也忘不了在凤翔的美好时光,以致后来被贬黄州时,碰到当年的凤翔游侠少年陈季常,两人还忆起当年在凤翔北山纵马驰骋的场景;还有当年在凤翔之任上修的“引凤池”(凤翔东湖),居然后来在杭州西湖和广东惠州西湖二次克隆成功。那篇著名的《喜雨亭记》更是体现了其与民同乐的大同思想。
此诗“巴东”这一地理概念的具体所指,历来有所争议。一些旧注认为诗题上的“巴东”即是唐代归州的巴东(今湖北巴东),如比较权威的清代学者王琦所注的《李太白全集》在此诗题下解释说:“巴东,即归州也,唐时隶山南东道。”(《李太白全集》中册1021页,中华书局出版)若仅凭字面意义,此说无错。但按照诗意,则不可通。诗题曰“自巴东舟行经瞿唐峡登巫山”云云,可知诗人的行进路线是从巴东出发,然后穿过瞿唐峡,接着才登上巫山的。若此,巴东的位置一定在瞿唐峡之前,或者说,瞿唐峡一定在巴东和巫山的中间。然而,归州的巴东却在巫山的下游,若自这里登巫山,则必须溯江而上,但无论如何又无法经过瞿唐峡。如果顺流,那就要先过瞿唐峡,登巫山之后要再行走相当一段水路方可到归州的“巴东”,与诗题大相牴牾。于此可知,“归州巴东”的说法是错误的。其实此诗中的“巴东”是指夔州(今重庆奉节)。《新唐书》地理志卷四十载:“夔州,云安郡下都督府,本信州巴东郡。武德二年(619)更州名,天宝元年(642)更郡名。”据此可知夔州原来是信州的巴东郡,至“天宝元年”始“更郡名”。李白此行当在开元十三年(725),此时的夔州尚未改名,仍叫巴东郡,所以诗人才有此称。又据《方舆胜览》:“瞿塘峡在夔州东一里”。若把与此有关的地名按长江流向自上而下的地理位置排列一下的话,其顺序则是夔州、瞿唐峡、巫山、巴东,况且前三处所距不远,完全可能是在一天中所经过的三个地方。诗人自夔州(时称巴东郡)出发,很快即经过瞿唐峡而到达巫山(参见《中国历史地图册》第五册47-48页,中华地图学社出版)。这样解则全诗疑窦顿开,语意甚明。
诗的开头概述自己登巫山前的情景。“江行几千里,海月十五圆”两句是说自己从家乡出发以来,沿江已走了几千里水路。这天正逢望日,明月皎洁,圆如银盘。诗人接着说,刚刚经过瞿唐峡之后便徒步登上巫山的最高峰。在山巅之上,诗人极目千里,饱览巫山的雄姿。“巫山高不穷,巴国尽所历”紧承前句,写巫山的高危与广阔。“不穷”是无穷无尽之意,这显然是夸张的说法,但又可说是诗人所目见。因为诗人视野之内皆是耸山峻岭,都是巫山之境,故谓之“无穷”,所以下句说整个巴国境内都被巫山占据了。当然此句只是形容巫山面积之大,与杜甫名句“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句意相同,不必拘泥考证巴国的辖境。“日边攀垂萝,霞外依穹石。飞步凌绝顶,极目无纤烟”四句写登山时的主观感受。山路高危陡峭,诗人要凭借垂下的藤条萝蔓才可向上攀援,有时只好倚偎在突出的大石头上喘息一会儿。诗人登得太高了,他觉得好像在日边霞外一般,云气在脚下缭绕,太阳在身边高悬。诗人心情愉悦,急不可待地快步登上绝顶,向远处眺望。啊!太美了。天清日朗,万里澄鲜,一点遮挡视线的东西也没有。他心旷神怡,浮想联翩,以下六句便写其在顶峰上的感受。
“却顾”两句是说,山顶真是高极了,回头向下一看,只见万里深渊神秘莫测,令人面容失色,心惊肉跳;抬头向上一望,头上即是青天。登临高绝之处,惊愕中又有几分自豪感,这是所有登山人都会产生的普遍心理。于是诗人展开了想象的翅膀,竟觉得青天仿佛可以用手就能摸到一样,但夜间所常见的银河此时却不知哪里去了。远望云彩的升起之处,便可知道苍梧山所在的地方;观看那奔腾的大江的流逝,便可辨别大海所在的方向。“苍梧”语出《归藏·启筮》:“有白云出自苍梧,入于大梁”。“瀛海”一词出白于《史记》。其实这两句诗是诗人由眼前所见的云气和江水发想而来,江流的方向当然应该是大海,无须详考。“周游孤光晚,历览幽意多”两句是过渡句,承上启下,下文便转写归途中的景色。
“积雪照空谷”以下八句大意是说,高山背阴处的积雪映照着空荡荡的深谷,风吹树木发出呜呜的悲凄之声。踏上归途时天色已晚,只剩夕阳的余晖了,但诗人游意未艾,兴致颇高。江上寒冷,故早早就听到了猿的啼叫之声,天色朦朦胧胧,远处的松林已隐隐约约,一轮明月从那里缓缓升起,宛如松林吐出的一般。月光皎洁明媚,猿声清幽凄厉。此情此景给人一种空寂静穆的感觉。这既是眼前的实景,又有诗人不忍离去的主观情感寓于其间,因此有一种惆怅惋惜的情味。最后两句说虽然自己还有游兴。但不愿再听到猿的啼叫声,这才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辞别了巫山,拄着登山杖回到了船上。
全诗记叙登巫山的经过,写得相当完整。从开始上山写起,继写登山时的感受与登上顶峰时所见到的景色,最后写下山及回船的过程,一气呵成,完全按时间顺序和所经历的过程来写,脉络清晰,层次分明。诗中借助夸张手法和大胆的想象渲染巫山之高峻宏伟,“日边”、“霞外”等诗句给人以飘飘欲仙之感“青天若可扪,银汉去安在?”两句更是异想天开的惊人之语,令人耳目一新,充分体现出诗人的浪漫气质。此诗是太白初离家乡时所作,他第一次接触到如此雄伟壮阔的山川景色,又因未接世事,所以诗中洋溢着欣喜之情,虽然在后半部分略含凄寂之味,但那恰恰充分地表现了游兴未尽的遗憾与惋惜,并没有什么感伤的情味。全诗的基调是明朗乐观,积极向上的,与其后来的一些山水诗的扑朔迷离,晦暗感伤是大不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