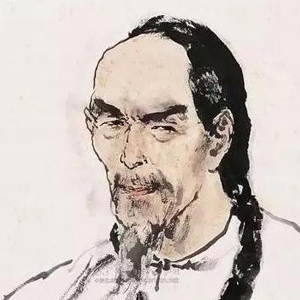这组诗作于清道光十九年己亥(1839年)。这年龚自珍辞官,由北京南返杭州,后又北上接取家属,在南北往返的途中,他看着祖国的大好河山,目睹生活在苦难中的人民,不禁触景生情,思绪万千,即兴写下了一首又一首诗,于是诞生了《己亥杂诗》。
第一段(篇首十二句)陈述被放的遭遇,抒发救国的忠愤。李白讨逆爱国,无辜被刑,实为冤屈。只因时机乖违,怨谁难辨。此诗开头四句即言其得罪并不怨天,他以黄口小雀易为罗者所得、白龙化鱼偶为渔者所刺的典故为喻,说明自身被祸当归咎自身,这里以一“愚”字自责不明智、不识时务。其实当时永王东巡至李白获释这一过程事态之翻覆,非人所能预料。但他对安史作乱是非常痛恨的,直以“鲸鲵”“豺狼”呼之,谴责其多行不义,一“屡”字谓其作恶多端。正是因为安史之乱,使他又在肃宋朝坐累远流,“去国愁夜郎,投身窜荒谷”二句,可见其遭逐仓皇之状。但李白虽一再遭逐并不沉溺于个人的不幸之中,“悲作楚地囚,何由秦目哭!”襟怀非常广阔。他痛哭的是,身为楚地的囚徒,多么可悲,不能像申包胥为救楚国而赴秦目大哭七天七夜。他自比申包胥,愿效一片救国之忠心。
第二段(篇中从“半道雪屯蒙”到“剑玺传无穷”)叙述光复两京的经过,抒发诗人的欣喜之情。前四句承上段写他在艰难的流放途中欣闻收复两京。他举出汉代的光武中兴,意谓光武尚须东迁,如今李唐王朝大势颇好,不须迁都,理当光复长安,非光武可比,字里行间已含喜悦之感,一“欣”字为此段的基调。这二十句一气贯下,历数光复长安的事迹,先言明皇幸蜀之时,有太子(储皇)驻兵扶风,支撑局面,继承帝位,延揽群雄。郭子仪率官军与回纥军共讨叛贼,前后夹攻,几经鏖战,平息国难,收洛阳,入咸京,席卷天下,成就大功。谓“扬袂正北辰,开襟揽群雄”,“叱咤开帝业,手成天地功”,是对肃宗的溢美之辞。后言肃宗迎明皇还长安,明皇亲授传国玺与肃宗,以“两日忽再中”盛称与皇儿于乱后团聚之喜庆。“大驾”四句皆祝愿之辞。这一段,李白当时据传闻写成,考之《旧唐书》中《郭子仪传》与《肃宗纪》,事与史正相吻合。诗中不仅切实地反映了这段历史,而于对平息安史之乱的赞颂与对唐王朝复兴的祝愿之中,又表现出李白关心国事的热情。这里,李白并未为区区一己得救而自喜,却为社稷“中兴”而欢欣。
第三段(篇末八句)感叹为时所弃,并以归隐的幻想表示对现实的不满。这一段扣住诗题的第三层意思:“书怀示息秀才”。李白肯与息秀才言承恩放还的身世和光复两京之大事,剖心相告,无疑其人亦为李白的志同道合者。他所表白的心迹是极为复杂的。前二句“愧无秋毫力,谁念矍铄翁?”显然由前段对社稷“中兴”的热烈赞美陡然跌落为自伤身世的浩叹。李白已年近六旬,当此国家复兴之际,自愧不能效秋毫之力,一“愧”字便含积极用世之念。他并以矍铄翁自比。《后汉书》载:“武威将军刘尚击武陵五溪蛮夷,深入军没,援因复请行,时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许之。援自请曰:“臣尚能被甲上马。帝令试之。援据鞍顾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铄哉是翁也。’”(卷五四《马援传》)李白欲效马援,颇怀老骥伏枥之志,是何等勇气。一年之后,李白有作《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还,留别金陵崔侍御十九韵》,亦见其“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谁念”二字,意谓不为时所重,无由鼓力,是怨愤之言。这二句分量很重,既有济世的热望,又有失意的苦闷。“积蓄万古愤,向谁得开豁?”(《赠别从甥高五》)亦同此意。欲进不能,无可奈何,由对执政者的失望与不满,进而产生弃剑学道、避祸远游的幻想,言如鸿高飞冥冥薄天,令弋者无以取之。“弋者何所慕?高飞仰冥鸿”二句,照应篇首“以愚陷网目”之意,记取隐身网罗之教训,遁迹方篷,高飞远祸。这里不是表示退隐的决心,而是以退隐的呜咽写其慷慨进取之志,力透纸背,感人至深。关于李白的隐退,历来被人误解,《旧唐书》说他“飘然有超世之心”,这种超世说一直成为论者的话题,他的游仙好道之作向为人所重视,他的仙风道骨向为人所赞赏。但这位“诗仙”的毕生经历与全部作品却表明他积极面世的人生态度,始终一贯。他曾明白地表示:“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送蔡山人》)这两句诗正可以作为“愧无秋毫力,谁念矍铄翁”二句的注脚。
这是一首以史笔写成的政治抒情诗。诗的主旨在于表明诗人怀有坚贞的报国之志,年虽老而志未衰,并为大志未酬深感不满。他能够做到:刚遇赦得释,便议论国家政治,可见李白面向社会现实的人生态度是十分积极的。李白在晚年,由于安史之乱把他推入现实矛盾的旋涡,他投笔从戎,对平息边将的叛乱,恢复社会的安定、消除苍生的灾难,寄予极大的关注,使他的诗歌创作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时期的作品,不同于安史乱前那些从个人出发的抒怀之作,而更多是从社会出发直接反映社会现实的矛盾,因而他晚年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和丰富的社会内容。而艺术风格也不似青壮年时期诗歌那样“壮浪纵恣”(元稹语),而表现为沉着顿宕。这首咏怀之作,恰好体现了其后期诗歌的特点与风格,无疑是其一篇代表之作。
李白晚年这类诗歌可以与杜甫同期作品媲美。惜乎长期以来论者与史家未予应有的重视,人们主观地以为:杜甫的主要活动时期为安史之乱后,而李白的主要活动时期为安史之乱前。因而李白与杜甫虽同经历过安史之乱,于杜甫为其中年,故以为重要:于李白为其晚年,则不予重视。这种重中年轻晚年的意识,掩没了李白晚年不朽诗篇的光辉。李白晚年的坎坷身世与光辉诗篇当与杜甫等同视之。
“人道横江好,侬道横江恶。”开首两句,语言自然流畅,朴实无华,充满地方色彩。“侬”为吴人自称。“人道”、“侬道”,纯用口语,生活气息浓烈。一抑一扬,感情真率,语言对称,富有民间文学本色。横江,即横江浦,在今安徽和县东南,位于长江西北岸,与东南岸的采石矶相对,形势险要。从横江浦观看长江江面,有时风平浪静,景色宜人,所谓“人道横江好”;然而,有时则风急浪高,“横江欲渡风波恶”,“如此风波不可行”,惊险可怖,所以“侬道横江恶”,引出下面两句奇语。
“猛风吹倒天门山”,“吹倒山”,这是民歌惯用的夸张手法。天门山由东、西两梁山组成。西梁山位于和县以南,东梁山又名博望山,位于当涂县西南,“两山石状飚岩,东西相向,横夹大江,对峙如门”(《江南通志》),形势十分险要。“猛风吹倒”,诗人描摹大风吹得凶猛:狂飚怒吼,呼啸而过,仿佛要刮倒天门山。
紧接一句,顺水推舟,形容猛风掀起洪涛巨浪的雄奇情景:“白浪高于瓦官阁。”猛烈的暴风掀起洪涛巨浪,激起雪白的浪花,从高处远远望去,“白浪如山那可渡?”“涛似连山喷雪来”。沿着天门山长江江面,排山倒海般奔腾而去,洪流浪峰,一浪高一浪,仿佛高过南京城外江边上的瓦官阁。诗中以“瓦官阁”收束结句,是画龙点睛的传神之笔。瓦官阁即瓦棺寺,又名升元阁,故址“在建康府城西隅。前瞰江面,后据重冈……乃梁朝故物,高二百四十尺”(《方舆胜览》)。它在诗中好比一座航标,指示方向、位置、高度,诗人在想象中站在高处,从天门山这一角度纵目遥望,仿佛隐约可见。巨浪滔滔,一泻千里,向着瓦官阁铺天盖地奔去,那汹涌雄奇的白浪高高腾起,似乎比瓦官阁还要高,真是蔚为壮观。诗人描绘大风大浪的夸张手法,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猛风吹倒天门山”,显然是大胆夸张,然而,从摹状山势的险峻与风力的猛烈情景看,可以说是写得活龙活现,令人感到可信而不觉得虚妄离奇。“白浪高于瓦官阁”,粗看仿佛不似,但从近大远小的透视规律上看,站在高处远望,白浪好象高过远处的瓦官阁了。这样的夸张,合乎情理而不显得生硬造作。
“海潮南去过浔阳,牛渚由来险马当。”长江在安徽地界变为南北走向,所以“海潮”不是西去,而是南去。浔阳,即江西九江市,“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白居易的《琵琶行》所写的,就是这里。牛渚,即采石,历来以地势险峻而闻名,可以用一人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来形容,其险峻远远胜过马当这个地方。马当,江西彭泽县西北四十里,山形似马横枕大江而得名。“横江欲渡风波恶,一水牵愁万里长。”这两句看似写渡江之险,实则写北上报国之路难行,“风波恶”,是指世事险恶,人心难测,所以才会有一个“愁”字了得。当时诗人避祸江南,也可以说报国无门,这里还没有以酒浇愁,这愁中还存在某种幻想,不似《月下独酌》其四所写的那样“穷愁千万端,美酒三百杯。愁多酒虽少,酒倾愁不来。”二十个字中用了三个“愁”字,而且愁到最后,连愁都不来了。
“横江西望阻西秦,汉水东连一作楚水东流扬子津。”长江天堑阻隔了李白北上的路途,只能在站在横江向西望了,长江由东西走向变为南北走向,所以用西望,而不是北望。西秦,指唐朝长安所在的地方,李白念念不忘报君恩。汉水,即长江水,东流到扬子津,古地名,实际上是扬子江畔的渡口。长江到江苏地界,俗称扬子江。李白想由此北上,但“白浪如山那可渡”,正赶上那天狂风大浪,白浪如山,根本无法渡船过江。古代人过江可没有现在方便,无论坐火车或汽车,从长江大桥几分钟就可以完全过江,古代长江上没有一座桥,过江主要是船,那时的船一般都是木头做的,根本架不住淘天的白浪,可以说一不小心就可能船翻人亡。所以在风大的日子,船一般是不过江的。“狂风愁杀峭帆人。”从这句来看,当时的船不仅有橹,还有帆,开船的也不只一个人,至少有两个人。一个摇橹,一个挂帆。从诗句来看,狂风让人愁不是李白,而是开船的人,因为不能开船渡人,他们的生活费也没有着落了,那一家人大小日子也没法过。这里实写开船人愁,而真正愁的是李白。他要北上,究竟为何事,六首词都没有交待,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李白不想久居江南,远离唐朝政治中心——长安。
“海神来过恶风回,浪打天门石壁开”,“海神”,指海潮,这里刚刚涨潮,潮还没退,狂风又来了,浪打在天门石壁上,似乎打开了天门的大门。天门,即天门山。“浙江八月何如此?涛似连山喷雪来!”“浙江八月”一词很令人费解,诗写的是江东,写到浙江去的原因,实际上不过是用浙江潮来说明横江浪涛之大。宋代的苏轼苏这样写浙江潮:“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红旗青盖互明灭,黑沙白浪相吞屠。”农历八月是浙江潮最为壮观的时候,那凶险的程度非比寻常,而横江潮后之浪可与浙江潮相匹敌。可见李白是见过浙江潮的,随手捡来,不着痕迹。最后一句“涛似连山喷雪来”来形容风起涛涌的凶险。
“横江馆前津吏迎,向余东指海云生。”横江驿馆面前渡口的官吏来送,可见那时的津渡是公家渡口,津吏长期生活在当地的渡口,对这里的气候变化了如指掌,他遇到李白后,伸出手臂,用手指一指东边,说:“你看,海云出现了。”意思说,马上海潮就要来了,渡船不能渡人了。接着问到“郎今欲渡缘何事?”,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大人您今天渡船北方有什么事呀?”有人根据“郎”这个字,认为李白在横江渡时还是一个年轻人,因为年轻的男子才叫“郎”,但实际上,这“郎”显然不是指人的年纪。“郎”在古代有五种含义:一是地名,春秋鲁邑;二是官名,战国开始设置,秦汉以后遂为朝廷官吏通称;三是指少年男子之通称;四是指女子对情人的昵称;五是姓氏。诗中的“郎”可以用解释为第二种,即郎官之意,比如《史记·司马相如传》:“赋奏,天子以为郎”,又比如《汉书·明帝纪》:“馆陶公主为子求郎”。李白曾在宫中呆了三年,大大小小也算一个官,但这儿离京城有好几千公里,一个渡口的小吏能够知道他在京城做官,可能是因为李白身上穿着唐玄宗赠给他的宫锦袍,人家一看,当然知道他就是一个官了。还没等李白回答,那人就说:“如此风波不可行!”意思是:不管有什么事,是大事或小事,反正今天是行不得了,因为很快就要风起浪涌了。
“月晕天风雾不开,海鲸东蹙百一作众川回。惊波一起三山动,公无渡河归去来。”这四句诗不仅写长江浪涛之大,“海鲸”是形容浪涛的,而且江面上起了大雾,那就更不能行了。
六首诗中处处流露出李白北上的急切和恶劣天气下不可渡口北上的惆怅与焦虑。诗人以浪漫主义的彩笔,驰骋丰富奇伟的想象,创造出雄伟壮阔的境界,读来使人精神振奋,胸襟开阔。语言也像民歌般自然流畅,明白如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