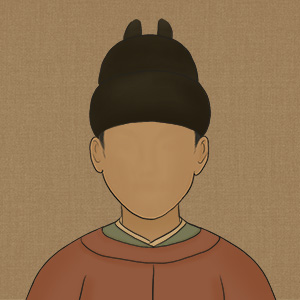这首词写春游的情景。上片写在叶嫩花明的春光里,画船轻荡,鸳鸯戏浴,渔歌声声,给人以轻快明畅之感。下片“春水无风无浪,春天半雨半晴”二句,连用两个“春”字,两个“无”字,两个“半”字,写尽春光骀荡之状。后两句写人情,与上片“鸳鸯”呼应,突出"红粉相随”。少女们相互媳戏追随,在南浦游玩,各得其乐。这首词写得明快,有生活气息,摆脱了浓厚的富贵味,堪称佳词。
此诗首字“至”字在诗中反复出现八次,故题名“八至”。从内容上说,全诗四句,说的都是浅显而至真的道理,具有深刻的辩证法,富有哲理意味。从结构上说,作者设置了层云叠嶂,前三句只是个过场,主要是为了引出最后一句“至亲至疏夫妻”,专在针砭世情,极为冷峻。
首句“至近至远东西”,写的是一个浅显而至真的道理。东、西是两个相对的方位,地球上除南北极,任何地点都具有这两个方向。两个物体如果不是南北走向就必然有东西区别。所以“东西”说近就近,可以间隔为零,“至近”之谓也。如果东西向的两个物体方向相反,甚至无穷远,仍不外乎一东一西,可见“东西”说远也远,乃至“至远”。这“至近至远”统一于“东西”,是常识,却具有深刻的辩证法。
“至深至浅清溪”,清溪不比江河湖海,一目了然能看到水底,“浅”是实情,是其所以为溪的特征之一。然而,它又有“深”的假象,特别是水流缓慢近于清池的溪流,可以倒映云鸟、涵泳星月,形成上下天光,令人莫测浅深,因此也可以说是深的。如果说前一句讲的是事物的远近相对性道理,这一句所说的就是现象与本质的矛盾统一,属于辩证法的不同范畴。同时这一句在道理上更容易使人联想到世态人情。总此两句对全诗结穴的末句都具有兴的意味。
“至高至明日月”,因为旁观者清,站得高望得自然就远看得自然明朗。日月高不可测;遥不可及,这个道理很浅显。这第三句,也许是最肤浅的。“高”是取决于天体与地球的相对距离,而太阳与月亮本不一样。“明”指天体发光的强度,月亮借太阳的光,二者更不一样。但是日月同光是人们的感觉,日月并举是向有的惯例,以此入诗,也无可挑剔。这个随口吟出的句子,在全诗的结构上还有其妙处。警句太多容易使读者因理解而费劲,不见得就好。而警句之间穿插一个平凡的句子,恰有松弛心力,以便再度使之集中的调节功能,能为全诗生色。诗人作此句,应当是意在引出下句。
前三句虽属三个范畴,而它们偏于物理的辩证法,唯有末句专指人情言之,是全诗结穴所在——“至亲至疏夫妻”。因为夫妻是没有血缘的亲人,在一起就是一个人,分开则形同陌路,甚至老死不相往来有之。当代某些学者试图以人的空间需求来划分亲疏关系。而“夫妻关系”是属于“密切空间”的,特别是谈情说爱之际。从肉体和利益关系看,夫妻是世界上相互距离最近的,因此的确是“至亲”莫若夫妻。然而世间的事情往往是复杂的,伉俪情深固然有之,貌合神离而同床异梦者也大有人在。夫妻间也有隐私,也有冲突,也有反目成仇的案例,正所谓“爱有多深,恨有多深”,不相爱的夫妻的心理距离又是最难以弥合的,因此为“至疏”。在封建社会中由于夫为妻纲,男女不平等的地位造成了夫妻不和谐的关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造成了没有爱情的婚姻,而女子的命运往往悲苦。这些都是所谓“至疏”的社会根源。如果说诗的前两句妙在饶有哲理和兴义,则末句之妙,专在针砭世情,极为冷峻。
这首诗和一般讲究起承转合的诗不同,这诗语言淡致,和唐代诗僧王梵志的诗一样平白如话,但平中见奇绝。
诗的前三句是个过场,其存在是为了衬托最后一句。层云叠嶂,前三句过后,才显出最后一句峰峦。“至亲至疏夫妻”这话满是饱经人事的感觉,比一般的情诗情词要深刻得多,可算是情爱中的至理名言。夫妻间可以誓同生死,也可以不共戴天。这当中爱恨微妙,感慨良多,寻常年轻小姑娘想说也说不出来,必得要曾经沧海,才能指点归帆。 或许正是看透了这些,李冶才宁愿放纵情怀。因此,即使隔了千年,也依然能引起人们的共鸣。
《吕氏春秋》说:“禹年三十未娶。行涂山,恐时暮失嗣,辞曰:‘吾之娶,必有应也。’乃有白狐九尾而造于禹。禹曰:‘白者,吾服也;九尾者,其证也。’于是涂山人歌曰:‘绥绥白狐,九尾庞庞。成于家室,我都攸昌。’于是娶涂山女。”此段引文系据《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太平御览》转引,今本《吕氏春秋》失载。又《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亦有《涂山歌》,全诗为:“绥绥白狐,九尾痝痝。我家嘉夷,来宾为王。成家成室,我造彼昌。天人之际,于兹则行。”《乐府诗集·杂歌谣辞一》亦有《涂山歌》,全诗为:“绥绥白狐,九尾庞庞。我家嘉夷,来宾为王。成于家室,我都攸昌。天人之际,於兹则行。”这两个版本文字较繁,是据《吕氏春秋》又加增补而成。《吴越春秋》中并说到涂山女的名字叫女娇。(《吴越春秋》:“乃有白狐九尾造于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九尾者,王之证也。’于是涂山之人歌之。禹因娶涂山,谓之女娇。”)
夏禹娶亲之事,发生在治水过程中。《史记·河渠书》说:“禹抑洪水十三年。”《汉书·沟洫志》说:“禹湮洪水十三年。”关于这十三年中的情况,《史记·夏本纪》中有概括的介绍:“(大禹)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但《尚书·益稷》记大禹的自述为:“娶于涂山,辛、壬、癸、甲。启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又《吕氏春秋》说:“禹娶涂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复往治水。”这两则材料都是说大禹只告了四天“婚假”,即“复往治水”。可见其婚娶是在治水期间。《史记》所说“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是不包括回家结婚这一次的。《孟子·滕文公上》说大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或许此“八年”是从新婚离家时算起;这样,大禹“三十未娶”,于三十岁这一年结婚时,在外治水已有五年的历史。古代男子二十岁行冠礼(见《礼记·曲礼上》,但《仪礼·士冠礼》等说十九而冠),表示已成年,可以娶妻了。大禹至三十岁而未娶,已是晚婚的“大男”。《吕氏春秋》说他急于结婚是“恐时暮失嗣”,即担心年纪大了不能生育,无法传宗接代。他对女色并不贪恋,所以新婚才四天便重又离家去治水了。
大禹的婚姻,据开头所引《吕氏春秋》中的资料,可见是很带有传奇性的。在走到涂山时,他预感到自己的婚事将会一帆风顺,所以说:“我娶亲,一定会有想嫁我的人。”正当其时,有一只长着九条尾巴的白色狐狸来到他面前。古代一般认为狐狸是瑞兽,是吉祥的征兆,因而他说“白者,吾服也;九尾者,其证也”,意思是出现白狐,也就是象征衣裳也是白色的自己将迎来吉利的事。涂山当地的人,也从白色九尾狐的出现预感到把涂山的一位少女嫁给大禹,将会降福给涂山,于是便编了这首短歌吟唱。首句中的“绥绥”是描述狐狸的样子。前人对《诗经·卫风·有狐》的“有狐绥绥”之“绥绥”,有两种不同的解释——雌雄并行貌或独行求匹貌。《涂山歌》中之白狐既然有一定的象征性,当以独行寻求配偶的后一解释较为近是。次句以表示厚实、粗大的“庞庞”形容白狐的“九尾”。以上两句,是用具有象征和比喻意味的瑞兽白狐独行求匹的意象起兴,接着的后两句即转向关于大禹求偶的正题。古人所谓“女有家,男有室”(《左传·桓公十八年》),指男女的结婚成家。故“成于家室”,即指大禹同涂山当地的女子成婚。涂山人认为这件婚事意义深远,故结尾一句说“我都攸昌”。“都”,原指城邑,这里具体指涂山当地;后两句合起来的大意就是:大禹与涂山女子成亲会使当地繁荣昌盛。
这首《涂山歌》的传奇性,从另一角度来审视,便具有一定的天人感应的神秘色彩。《吴越春秋》中的《涂山歌》所增补的句子中有“天人之际,于兹则行”二句,更是直接站出来表明九尾白狐与大禹婚事二者之间正是一种天人感应的关系。从科学的观点看,将社会人事同自然现象作简单的比附,这当然是荒唐的;但从人类社会的演进史来看,诸如此类的天人感应,正好反映了人类童年时代的思维幼稚的一面。读这样的诗,除了令人感受到时代的进步之外,也使读者如同成年人面对幼稚天真的儿童一般,可以领略到一份意想不到的轻松与喜悦。
“阆州城东灵山白,阆州城北玉台碧。”“阆州”是说明“地名”,当时阆中人已在被唐玄宗赐为“仙穴山”的灵山祭祖祭神,用大量的白花、白幡挂放于满山、满坡、满树枝,映衬得此山一片片白色而象征“灵山白”。“城东”“城北”,是在介绍相关的地理位置;“灵山、玉台”,是专指具体的地方;“白、碧”,是在以景喻事。这两句叙述了阆中当地的清明祭祀活动之事。
“松浮欲尽不尽云,江动将崩未崩石”两句是针对第一联从现实性出发所记载的阆中当地清明节祭祖活动之盛况。“松浮欲尽”,是指松枝在摇动中“想”把本不属于松树的什么东西摇开。可能把一些由唐代阆中人在清明节有人先挂在松树上的白花(诗中喻为白云)、挂在松树上的青纱(诗中喻为乌云)摇散、摇落,但又有后来人在清明时节陆续再在树枝上挂上白花或青纱,让阆中的灵山与玉台山的松树上在这段时间内,能较长期存在着可拟为白云或乌云的白花和青纱,故而能“不尽云”。接着以唱叹的语气写出江面的盛况。唐代阆州盛大持久的祭祖、祭天、祭神、祭亡灵的活动,因不少仪式是官民共同参与,来自陆路与水路的敬拜者络绎不绝:在山祭山神,在水祭水神,在庙祭祖宗,在宇祭上天;这一因船只在江面涌动、陆上又有吹打弹唱而震得岩体欲崩的群体性民俗活动,能震撼目击者的心灵。
第三联上句“那知根无鬼神会”中“根”与“鬼神”均与清明节的活动有直接关系,与《杜臆》所释“阆中山多仙圣游迹”相符合。下句“已觉气与嵩华敌”的诗意不是在讲阆山的山势能与嵩山和华山的高度相似而可“敌”,而仍然是描写阆山清明祭祖活动的空前盛况与磅礴气势。上句中“那知根”正好与下句“已觉气”成为一问一答的对应;而“无鬼神会”和“与嵩华敌”的描写,也是对应式的自问自答。这就是杜甫以《阆山歌》来记叙阆中清明祭祖盛况之诗歌中所表现来的睿智。
最后,“中原格斗且未归”是表达诗人在参加阆中清明节的祭祖活动中,仍不忘记国家的大事。杜甫一直关注着国家大事,即使他在参加阆中的清明祭祖活动以及写其《阆山歌》之际,仍在牵挂着不稳定的中原局势。此时身在阆州,耳闻目睹阆中人民爱祖爱国的民俗与热情,诗人表明自己也要与阆中人民同忧同思同作同为——“应结茅斋著青壁”。这个结句有几层大意:第一,在叙述与感叹中认为自己不能只是一个清明活动的记录者,也同时应当以行动来表示爱祖爱国;能在自己所居茅屋的墙壁著上表示哀愁的青纱,也是一番衷肠的诉说。第二,诗人从阆中清明祭祀活动中所领会“爱祖爱国民俗”的画境,和他要求一首诗所应达到“篇终接混茫”的诗境是近似的、相通的。第三,篇首的“灵山白”与篇末的“著青壁”,一“白”一“青”,又呈现出“白花与青纱”的对仗。这般前呼后应的诗歌结构,强烈地显现出《阆山歌》写作于清明时节的祭祀文化的风格。
杜甫在阆中的时间虽然不长,创作的诗篇却不少。就创作的速度而言,可以说是一个小小的高产期。这首《阆山歌》专咏阆山之胜,它与《阆水歌》一起成为杜甫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